
在中国近现代化历程中,很多领域受到外来侵略和战争的影响,出现了“断层”。从民国时期开始,传统工艺受到舶来品的冲击,随着腐朽的封建主义一起土崩瓦解,这不仅和政治运动、文化运动有关,更深层次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人类走向机械化和数字化,家庭的电器化,女性获得了完全的解放,服装从形制到工艺彻头彻尾的面向“全球化”。
其实“断层”何止近现代的中国,西方女装发展也曾一度出现断层。处于非社会性生产地位女子,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处于被支配地位。服装发端于女红文化,其传承和流变都依赖于女性,离不开男性的审美表达。服装,作为附属品,无法改变被支配的地位。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女装的紧身胸衣和中国女性的缠足一样,成为一种刑具极为残酷的延续了近四百年,是女性心甘情愿的“被驯化”的过程。而拖地的长裙和不方便的尖鞋头更使得女性获得了优雅美名的同时,失去了参与社会正常劳动的能力。服装极具文化性。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军需生产和支援后方,女性被迫进入社会生产领域,这种转变是历史必然。挡眼的长刘海,拖地的长裙,华丽的阳伞和高耸的帽子无法适应社会需要。女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自觉地从自己的亲戚和丈夫那里寻找变装的“救兵”——短发、军服、吸烟装,那时的“缓兵之计”带来了战后设计风潮。放松了曲线的香奈儿,用珍珠项链搭配直身黑礼服成为服装设计界的经典,迪奥则选择用“新面孔”来重新恢复女性的优雅,无论什么理念,女装近代化大步流星地阔步前进。 女装似乎在一夜之间让女性从花瓶一样的装饰品,变成了生产线边的技术工,女人以一个社会生产者的身份站在了男人旁边,女人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了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穿起了简易实用的制服。
处于民国时期的中国民众,对旧社会失去信心,接受了新思维,尚无法辨明该何去何从,没有新派,只能“借来”,西方的变服运动是从男装上寻找借鉴,而中国当时的服装更多的从西方形制着手。一切外来的都带着侵略,也带着“洋味儿”。租界的洋房、汽车、铁轨,洋房里面的照明灯、电话、厨具,舞厅里的洋酒、香烟,奢华的裘皮大衣,黑白肃穆的西装,怀表等舶来品伴随着百货商场驻扎在上海。从洋务运动开始陆续的留洋学习的“先生小姐”们处处洋气,买雨衣、胶鞋是多么难得的事情。随着消费观念、审美观念、设计观念、时尚观念的传入,生活在一些被迫“开放”城市中的太太小姐们,审视延续了千年的服装形制——扁平“二维”的上衣下裳,开始走上街头的裁缝店追求“新派”来。旗袍开始注重省道,表现女性的曲线,裙摆长长短短,亦步亦趋地仍然改不了骨子里的矜持,国画似的人物,绣鸟似的做派。这种清丽的“海派”成为胶卷和录影带中永远不可磨灭、一去不复返的辉煌。建国、肃反、文革……动荡年代又让变服之路变成一条“断了的弦”。
中西方服装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深深浅浅的断层,而回顾起来,意味深长的是西方断层之后是时装界辉煌的“新世纪”,在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循环往复间一次次的将人本主义发挥到极致,利用本民族的特色大胆突破,服装设计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很多当时的品牌成为如今的“百年老店”,而且当代最富盛名的设计师还在一年两季在四大时装周上发布他们的“新品”,多少时尚界人士带着一颗朝圣心,不远万里奔赴巴黎,熏陶时尚情怀。如今,中国国际服装周上不断产生新力量,包括模特和时装表演策划团队也逐渐走上国际化,在历史的断断续续中,是不是可以找到些许灵感 。(此文中的断层有一种称法为文化真空)
(作者 李晓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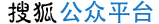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