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夏凉之
大唐盛世
人人自有一种不输不畏的底气
他们爱作诗
下笔如流水过皆真性情
他们爱做梦
真真假假皆为趣味而生

神笔飞来的传奇
他们爱作诗。
所有的理想或生活,都是诗词的题材。
所有的诗词,都是他们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载体。
他们写爱情: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爱了就是爱了,热烈而果敢,绝不惺惺作态瞻前顾后。
他们求前途: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干谒诗理直气壮,毫无求人办事的低姿态。
他们说相思: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缠绵悱恻又扣人心弦,由不得你不感怀相思入骨。

他们谈理想: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完全摒弃了书生意气,满纸皆是浩浩然的男儿志气。
他们写生活: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山村的旖旎风光和村民的淳朴扑面而来,自在随意。
他们控诉社会: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陰雨湿声啾啾。
字字珠玑字字血泪,将那个时代的苦难尽诉笔端,让人不忍卒读。
他们写离别: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
分明无限的愁绪,却不过分沉重。
这是专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块自留地。自唐以后,宋词清婉,元曲缠绵。
再也没有哪一个朝代诗人,能如唐朝诗人一般把诗词写的肆无忌惮,写的无比生动,写的那么真实。

自我娱乐的乌托邦
生活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场享乐。
他们爱做梦。那对想象和梦的狂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会玩,也敢玩,即便做一个梦,也要梦出新的高度。
无论真或假,他们都愿意付诸认真的态度。梦想,是他们对美好的追求,对趣味的追求。
正是如此,才会有白居易的飞云履,鱼朝恩的鱼藻洞……
飞云履:
唐·冯贽《云仙杂记·飞云履》:白乐天烧丹于庐山草堂,作飞云履,玄绫为质,四面以素绡作云朶,染以四选香,振履则如烟雾。乐天着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云,计不久上升朱府矣。”
在江州的日子,白居易虽然不得志,但是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
这幻想中的仙鞋,自然不能带着白乐天踩着飘飘云彩登上仙界。然而,当鞋子上的云朵在芬芳的香气中若隐若现,无论是否可以飞天已不重要。对于诗人而言,这超越现实的浪漫,或以鞋为飞行器的梦想,都已在飞云履上得以实现。

鱼藻洞:
《南康记》曰:鱼朝恩有洞房,四壁安夹琉璃板,中贮江水及萍藻、诸色虾,号“鱼藻洞”。
对于人类来说,水晶宫是属于神话中的建筑。然而早在唐朝,大宦官鱼朝恩就兴建过明净剔透的“水晶宫”。
再以玻璃做成夹层内灌满江水,种植水草、浮萍。当藻草与萍叶漂浮,鱼虾轻灵游动时,仿佛置身水底的洞穴内。在还没有轧制大块玻璃技术的唐朝,这“鱼藻洞”实在是难能可贵。
幽人笔:
《云仙杂记·汗漫录》:司空图陷于中条山,芟松枝为笔管,人问之,曰:“幽人笔当如是。”
休休休,莫莫莫。
休休亭里,于年迈的司空图而言,一枝幽人笔,大概已是乱世之中唯有的安宁与寄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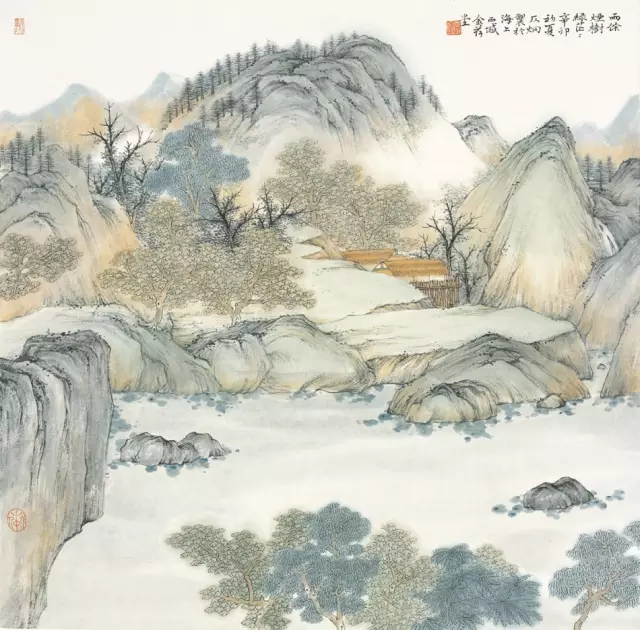
洞天瓶:
唐·冯贽《云仙杂记·酒中玄》:虢国夫人就屋梁上悬鹿肠于半空,筵宴则使人从屋上注酒于肠中,结其端,欲饮则解开,注于杯中。号“洞天圣酒将军”,又曰“洞天瓶”。
洞天瓶这名字虽好听,不过鹿肠中流出的酒,不知会不会染上什么味道呢?
不过美酒从半空流入杯中,在视觉上,已是一种享受。
同样是喝酒,汝阳王李琎的方法,可就温柔太多了。
泛舟于注上酒的云梦石长渠中,随手可取的酒器,其自在形态,与曲水流觞的雅集,倒颇有相似之处。

雪莱说:“在我们人生中替我们创造另一种人生。”
我想,这是对唐人的想象与行动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