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止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传记随笔作家,是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
我们不知道的是,青年时代的止庵也曾醉心于小说创作——虽然大多都被他烧毁。今年年头,止庵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喜剧作家》。
如今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小说?这个问题,止庵曾问过自己很多次,他甚至一度怀疑小说这一形式本身:小说本质上是个阴谋,编个故事把读者诱骗其中。但这么多年来,包括止庵在内,人们阅读小说的脚步却从没有停止。
你如今还阅读小说吗?对你来说,小说的魅力在哪儿?今天我们来听止庵聊聊跟小说有关的那些事儿。也欢迎你留言给书评君,与大家分享你对小说的看法。

止庵,原名王进文,1959年出生于北京。传记随笔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自由撰稿人。代表作品有《惜别》、《周作人传》、《神拳考》等,《喜剧作家》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作品。
止庵:小说是个阴谋,但我们需要它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婷
《喜剧作家》是止庵的第一部小说作品,收录《姐儿俩》、《走向》、《墨西哥城之夜》、《喜剧作家》与《世上的盐》五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创作于1985年到1987年之间,于是它们自然带着年轻的止庵——一个二十多岁小伙的荷尔蒙及滚烫的热血。同时,它们还带着80年代的诸多烙印。
80年代,在我们当下的讲述中,是一个文学与艺术的黄金年代,充满不灭的理想与荣光。但在止庵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的八十年代。它似曾相识,却又全然新生。
止庵写道“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寻找不到;这些动着的人和车,这些不动的房子和墙——那个怀抱,那种安慰,他寻找不到了。”这部小说集写的,是这样一些与他们的世纪失之交臂的人:那些求而不得的愿望,爱而不得的人,以及未能实现的理想、激情与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喜剧作家》不仅属于80年代,更属于30年后的今天。因为人类的困境,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有时候,小说比历史更真实
《喜剧作家》如同它的作者止庵一样,简单素净。翻开书,不见一篇前言与推荐,打头就开宗明义,一篇篇小说接踵而来。读罢所有小说,你才能在书的末尾看到止庵写的一篇小小《后记》,七八百字,大略记述了这本小说集出版的缘由。
我们熟知的止庵,是个传记随笔作家,也是个专业的读书人。如果说起周作人,说起张爱玲,说起“义和团”,乃至说起读书、出版、写文章,我们都会想到止庵。但说起写小说,我们会觉得止庵的名字多少有些突兀。
实际上,止庵在少年至青年时代,曾写过大量小说。但最早写的几十万字小说习作,止庵在25年前都烧掉了。对此,止庵说是“幸未谬种流传”。直到母亲帮他编“三十年集”(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三十年集”系列丛书,其中包括止庵的《河东辑》),某日提起,“你不是写过不少小说吗”,止庵这才从寄放在友人地下室的纸箱中,翻腾出年轻时留下的小说手稿。
“幸存”下来的小说共有十多篇,有些曾在80年代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有些则没有。《喜剧作家》收录的五篇短篇小说,自然是止庵精挑细选的。选出来的这几篇,用止庵的话说,“还不坏”。

《喜剧作家》
作者: 止庵
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7年2月
这些小说创作于止庵26岁——28岁之间,那时候的止庵,对人生有着强烈的焦灼感。他渴望找到自己的路,也渴望外界给予自己的寻找一些支撑与回应。少年时止庵曾经对小说创作怀有满满的热望,但小说发表后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关注与评论。“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有时候,一个人一件事的确都有自己的‘际遇’。”如今回头看,止庵觉得这些小说与80年代的时代情绪是错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小说也跟它的世纪失之交臂了。
这些如打了一记空拳般的小说,令止庵疑心,自己大概并不适合小说创作这条路。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地,是止庵当时对小说这一文体本身也产生了怀疑。当时他已经开始大量阅读周作人。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与废名的通信内容,两人在信中谈及一个观点:小说,尤其是“好莱坞式”的小说写作,实际上是个阴谋,写作者人为设计一个“套”,设置好一套固定的程式,将读者“诱捕”到其中。言下之意,小说不过是一套骗人的把戏。“唉?当时读完,我觉得这话说得有道理啊。”此言对当时将小说创作奉为志业的止庵来说,多少有些根本上的观念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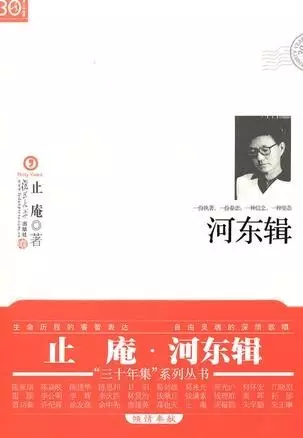
《河东辑》
作者: 止庵
版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8月
差不多同时期,止庵曾花了一年时间大量阅读研究庄子的著作及思想。受庄子影响,止庵那种焦虑地期望受到社会认可的心情也变得动摇了。“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变得不着急了。”对一个年轻人来讲,这可能是种“负面”影响。
无论如何,90年之后,止庵逐渐远离了小说创作。但此后的三十多年间,小说一直在止庵的阅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向谦卑的止庵,唯独在提到自己的读者身份时,颇为志得意满。这么些年来,他虽然没有继续小说创作,但他读遍了最好的小说。“我知道好小说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小说是怎么回事儿。看小说的眼光,我有。”
如今回头再看,止庵认为,很多时候,小说比历史还要更真实。“文学给我的震撼、教给我的关于人生的事情,不比任何一个思想家、哲学家少。甚至很多东西,我在文学里找得到,在哲学里却找不到”。
是啊,小说可能是个阴谋,但我们却如此需要它。
他要的,是“自适其适”
如同许多有志于写作的前辈一样,止庵是“弃医从文”。他学医出身,198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止庵调侃自己道,小时候,他想上北大,但家里想让他学医,没上成北大。后来,北京医学院并入北大,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院,他倒变成了北大毕业生。前几年,北大还颁发给他一项“优秀校友”的荣誉。“所以啊,好多事儿根本没法儿说。”止庵知道,命运是控制不来的,对于人生在世的许多事情,他都有顺其自然的态度。
从医学院毕业后,止庵去了积水潭医院口腔科做医生。按理说,医生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但干了一段时间,止庵就动了转行的念头。因为,做医生的日子,一眼就能看到头。“一人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坐下。看病人。评职称。我能看到我五年后,十年后的样子”,这令止庵感觉恐惧。
在小说《走向》中,男主角是个牙医,其中有段对牙医日常工作的描述:“患者从嘴里掏出一副假牙,带出来的唾液粘粘糊糊的,拉成了长长的丝。他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不是厌恶,不是蔑视,也不是愤懑,只是有些担忧,觉得应该再把一切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它们——那些动作,那些器械,那些声音,将他孤零零地抛在这儿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什么都不属于他,什么都与他无关。那么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牙医止庵,最终还是转行了。

青年时代的止庵
他去了报社做记者。在报社的几年,是他创作小说最集中的一段。再后来,他去了外企做销售,做得风生水起,收入比之前多了很多。也是从去外企工作之后,他停止了小说与诗歌的创作。
但有一点,从他二十多岁起,就没有变过。那就是他看待世界与人生的方式,或许在这一点上,止庵受庄子的影响很明显。他很赞同庄子所主张的,人要“自适其适”。所谓“自适其适”,当然是要自得其乐。其实它说的,就是人的自由:不勉强自己与别人一样,也反对别人把意愿强加给自己。人通往自由的路,说到底只有这一途。
在这样的“自适其适”中,止庵读书写作至今。这种“自适其适”并非是简单的自得其乐,它是早早认清了生活的无意义、荒诞、绝望之后,又安然接纳了这种绝望,并且与这种绝望和平共处之后的选择。如同书名《喜剧作家》所提示的,这并不是一种软弱的悲观,而恰恰是一种有力的勇敢,甚至是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英雄。
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喜剧作家》正与此呼应。对此,止庵自己有过恰如其分的解释:悲剧是以“人生有价值”为前提,喜剧是以“人生无价值”为前提。人生本是一个东西,悲剧和喜剧都是对它的看法。悲剧是正的,喜剧是负的;悲剧是向上的,喜剧是向下的;悲剧最终张扬人生的价值,喜剧最终消解人生的价值。
那么,《喜剧作家》,正是这样一部负的、向下的作品,描写了这样一群负的、向下的人。然而它的珍贵之处,或者说小说的珍贵之处,却正在于此。它揭示了人类最深的绝望与困境,而这种揭示本身,正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大真实。
对话止庵:
“应当讲讲翻译文学的影响,文学史里缺这章”
新京报:您挑选这几篇小说时,有什么“标准”吗?
止庵:这批小说一共有十来篇。对我来说,不必一定要再出版这些小说。所以出版社找我的时候,我说得给我点儿时间,把这些小说全都重读一遍,看看到底写得怎么样。
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来看,我觉得这些小说中有几篇还不坏。我又拿给几个平时也喜欢读书的朋友看,他们也觉得不坏。那就出吧。找出来的十多篇小说,有的离八十年代太“近”了。比如讲退休之后的老人去剧场看戏的快乐;还有写当时的一个高考落榜女青年如何通过穿着打扮而建立自信……这些故事因为太靠近那个时代,现在读就觉得“过时”了。选出来的几篇,离八十年代的具体生活相对“远”一些,拿到当下来读,仍然有很多情绪上的相通之处。
新京报:对,小说中对生存状态的描述,过了三十年来看,我们当下的人还是如此存在着,这种对存在的感受是相通的。我们看到书封上用“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来概括这部小说集的主题。你自己会如何描述这部小说的调子,有更精确的概括吗?
止庵:如果要给这部小说挑几个关键词,我觉得是绝望、挣扎、徒劳、无意义。听起来是很灰暗,但我到现在读小说,能接受的、好的文学其实说的都是这个东西。
这几篇小说写的都是一个人开头进入了一种尴尬、困难的状态,到结尾也没有变得更好。人生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有提出解决方案的人可能都是自以为是的。我不想给出虚伪的解决,虚妄的希望。文学是揭示一种状态,不是给出一种解决。

创作《喜剧作家》时的止庵。
新京报:整部小说集给我感觉是非常现代派,非常先锋的,从中能够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你,里面充满的是个血气方刚、暗流涌动的写作者。这样的写作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受过哪些作家的影响?
止庵:这些小说都保留着我当时写它们的样子,没有改动过。我也没法去改它。我已经不是当时创作这些小说的那个年轻人了,他跟我是不一样的人。小说里的主体都是很年轻的人,同时他是很多愁善感、很孤独的,对生活有强烈的焦灼感。这种东西是我现在没有的。比如《走向》,从头到尾贯穿着这种焦灼感。有了这个焦灼,这个小说才成立。
给我影响最大的,应当是卡夫卡。实际上,这五篇小说我都能读到对应的源头,这也无庸讳言。但这种影响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把它搬过来,还有一种是要把它“化”掉。我觉得我这些小说还是消化了很多东西的,没有那么直接。
《姐儿俩》这篇很明显是有毛姆、日本作家井伏鳟二的影响。《世上的盐》我觉得是比较像法国的青春文学,可能还有点川端康成的影响,写得比较唯美。《走向》受莫里亚克的影响。《墨西哥城之夜》注重客观描述,这是受福楼拜影响。《喜剧作家》应该是受过伍尔夫《墙上的斑点》的影响,那时候还没读过《尤利西斯》全本,但看得出来也受了它意识流写法的影响。

《卡夫卡文集》
作者: [奥]卡夫卡
译者: 高年生
版本: 作家出版社 2011年3月
新京报:《喜剧作家》这一篇写法非常特别,令人印象很深刻,有各种人物意识上的穿插描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用了非常多省略号。看得出这篇小说创作时是很费心的,能讲讲这篇小说的创作吗?
止庵:当时我对话剧这个形式特别感兴趣,只要有话剧就去看。写这篇小说就有意识地要写一个戏仿剧本的东西,想让小说有舞台感。这个小说里每句话都是内心的台词,它看起来是个小说,其实里面是个话剧。省略号都是内心各种想法、心理、意识的交替。
我写小说甚至比我后来写文章耗费的精力还要多,我记得当时住在一个很小的小房子里,特别冷,写得脚都生冻疮了。写小说是很耗费人心的,写文章相对比较平静,情绪上不会有那么多拉扯。我自己身上有非常敏感的一面,神经非常细,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就知道他开不开心。写小说其实是要把这一面不停地放大。
新京报:我们现在看80年代,觉得那是一个文学与艺术的黄金年代。你们那时候都读什么书?整个时代的文学氛围是怎么样的?
止庵:这种氛围其实从文革后期就开始了。大家都很爱读,但找不着书。后来过来一批西方的思想、文学作品,大家都是如饥似渴。
影响最大的是萨特,那时候还没有他成本的书,都是这儿一篇,那儿一篇,大家到处搜罗来读。他有本小册子叫《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流行读物。他说人能确定自我,这现在听起来好像很浅薄的道理,但当时特别鼓舞人。还有尼采,他讲“上帝死了”,否定旧价值,打破旧权威。还有就是弗洛伊德,让人认识到人心理的无限复杂。文学方面,当时有大量的海明威的作品引介,还有契诃夫、毛姆,当然还有卡夫卡……
那个时候的作家,几乎每个人你都能找到一个对应的源头。咱们的文学史缺这么一章,应当好好写写翻译文学的影响。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作者: (法)让-保罗·萨特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年9月
新京报:你后来停止了小说跟诗歌的创作,但是文学阅读一直在你的阅读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你如何看待小说创作跟阅读的关系?
止庵:对我来说,阅读也是一种写作。你的脑子是紧紧地跟着作家走,看他走到哪儿想到哪儿,看你自己能不能跟得上。
拿卡夫卡举例,他写的《城堡》、《审判》我都能跟得上,但是《地洞》里面对焦虑、恐惧的描写有好几个层次,那个最深的层次,是我没想到的。到最后那个动物的恐惧到什么程度呢?它要在自己本来的地洞口再挖一个小洞,藏在那个小洞里看着原来的地洞,防备着被侵害。焦虑的情绪大家都有,但他最后把它写到是,我等着看我如何被这个焦虑侵害,是对焦虑的焦虑。写到这一层我就觉得人家写的太好了,已经把焦虑这个情绪写到极致了。
挑最好的小说读,跟着它一步步走,那如果把出名这些事情放下,阅读跟写作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要去自己写一个拙劣的版本?作家分两种,有一种是特别知道自己哪儿好哪儿不好,比如张爱玲,非常清醒;还有一种是凭本能,凭冲动写作,比如萧红,所以她的小说有的很好有的很差,全集是不能看的。这个可能也是“旁观者清”,但一旦太清醒了,那也就没法下笔了。

《豹》
作者: (意)兰佩杜萨
译者: 费慧茹 艾敏 等译
版本: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年5月
新京报:没有一直保持小说写作,你会觉得可惜吗?
止庵:不会。意大利作家兰佩杜萨,原来是个亲王。59岁开始写小说,一直没有发表,到62岁死了。后来《豹》发表后,被誉为是终结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时代的作品。所以好多事儿真的没法儿说,做的事儿就做了,没做的事儿那就是没做。
我对自己的写作跟阅读是很知足,很感恩的。写作、出书这么些年,一直都很顺利,碰到的人也都很好,没有遇到过大的波折。这几十年是好好读书、写作过来的,的确是认认真真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现在没有说一定要写什么、做什么这种心态了。
新京报:你提到过年轻时曾计划写部长篇,还做了很多笔记,写了人物小传。这部小说还会想把它完成吗?
止庵:我是发现了年轻时的笔记本,看到当时的笔记,才记起来我有这个想法,我都已经忘了。这部长篇想写的是八十年代的那一代人,面对生活时所做的种种选择。那一代人每个人都背着一段历史,现在的人是没有历史的,每个人就是自己。现在大家都用手机,都发短信,一部电影出来大家都去看,选择和生活很趋同。大家焦虑的是一样的事情:房子,车子,工作,只不过有的人走的快,有的人走的慢,落后的人就更焦虑。
80年代是某种分水岭,出现很多变革,每个人选了不同的路, 从此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那一代人从60年代走过来,有人对经历过的历史离不开放不下;有的人就离开了放下了。当时的人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后来怎么样了,这种在大时代中的变迁很有意思。我觉得中国还没有人去好好写过这个情绪和记忆。我可能会继续把它完成,但也是顺其自然吧。
新京报:现在的生活一般如何安排?最近有读到什么好书吗?可以跟我们的读者分享下。
止庵:我近几年花很多时间在旅行上,去日本的次数最多,可能前后有二十几次了。最近还要再去。读书当然一直在读,但没有之前读得多了。最近读的书里,比较喜欢的是《科雷马故事》跟《思虑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