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虚无时代中寻找故事
──王威廉《北京一夜》写作中的意义
文·陈雀倩
(《南方文坛》2017年第1期)
王威廉,1982年出生于青海海晏,为80后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曾获第二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提名奖(2009)、首届“作品‧龙岗杯文学奖”(2012)、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2013)、首届《文学港》杂志年度大奖(2013)、第二届广东省散文奖(2013)、第二届《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2014)、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2014)、十月文学奖(2015)等多项知名文学奖的注目和肯定。已出版长篇小说《获救者》(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中篇小说集《内脸》(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并曾在《收获》《花城》《作家》《大家》《中国作家》《山花》《散文》《读书》《书城》等知名期刊发表大量小说、散文与评论。作品亦曾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刊转载;并入选《华语新实力作家作品十年选》、“华语文学突围文丛”、《中国先锋小说选》等重要选本,以及2007年至今的多种小说、散文年度选本。
自2007年迄今创作长达九年,表现可圈可点,精彩夺目。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评论王威廉“作为迅速崛起的青年作家,他的写作深刻而凝重,以超越同代人的思辨性拓宽了小说这种文体的可能性”。批评家李德南且提出:“他的文学才情与思辨能力,写作上的所来之路与个人风格,在近几年发表的《非法入住》《合法生活》《无法无天》《内脸》《暗中发光的身体》《没有指纹的人》《市场街的鳄鱼肉》等具有‘异端’性质的现代主义作品中已可见一斑。”可见王威廉小说文体的扩充和小说内在本质的现代主义已然被注目与认可。本文试以《北京一夜》里三类不同的主题路线来诠释王威廉写作上的意义。
诗意/感官的抒情之情
《北京一夜》叙述一对错过时机未能成为眷属的情侣,尽管相识时,女的念医;男的念文,却因为共同拥有对文学的喜好,及同为西北人,女的陆洁美丽善良,男的家桦对她一见倾心。他总是为她的文学兴趣找到发表的管道,且不断为她的文学执迷打开视野。然“他的直觉让他隐隐预感到,自己与她之间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他将承受生命中那种未知、无形却锥心的伤痛。说到底,这个女人还是一个谜”,“他觉得她那不可索解的内心,正是通往一个真实世界的路径”。家桦对陆洁的莫名执迷和一往情深,说到底,究竟是落入一种诗意的、无力的爱情之情,若只是单纯对她出色容貌和文学兴趣的耽溺,倒也无以支撑十年之久。然而家桦对陆洁的爱其实是超出一种常理,未经熟识即以一种“铸印”的情感将他和陆洁绾结在一起。北京一夜,承担十年之久的缪想与思念,当他们再度重逢,“他们的嘴唇既是在重温,又是在探询,探询岁月变迁中那些难以言传的滋味”,“有了时间的浓度,他与陆洁的感情早都发酵成了浓香却又辛辣的酒”,彷佛这一夜成了对彼此的相思、葛藤,以及十年性爱想象的浓缩物,强劲而感官的爱。对于残破而无以修复的爱情与青春的执恋,成了家桦绵绵无尽与意识缠绕的抒情形式,同时也成了一种悲哀的感伤:“他觉得自己对她的爱情尽管构不上不朽,但至少也是对永恒的一种假设,或者,是对永恒的一种发明。她曾用这种文学的方式告诉过他:她为了把他留在一种永恒里,所以总是远离他。”而男的却说:“我会一次又一次把你留在作品里。”在理性的思考里,两人都有对彼此眷恋的一种方式;然而在现实而寒冷的地坛公园里,两人流失的时间与青春,彷佛是“门后这座祭祀大地的方泽坛上,遗落下来的两件祭品”,沧桑而无奈,绞缠而无结局。
在《北京一夜》里无法成全的诗意爱欲,于《听盐生长的声音》中,亦有另一种的荒凉景致述说后现代疲态的情感欲望。文章叙述居住在盐湖的夏玲夫妇,接待欲前往西藏而路过此地的小汀和金静这对情侣,四人在盐湖一游中,男主人公“我”惊诧于金静锋利的美貌,彷佛他于无感的沉睡中刺醒:“这座冷落的小城,让我暗自忧伤,而金静带着她惊人的美貌,像一道过于明亮的闪电,让我忧伤的阴影愈加浓厚了。”就这样,一行四人观赏风景时,发生了彼此生命中的交集和共感:积雪般纯净的盐层,火星般奇特的荒凉、死海般淹不死人的湖、破裂肝胆般的夕阳西下,整个轰雷雷的震慑了小汀与金静的内心──“我无数次看过那样的风景,夕阳像是破裂的肝脏一般,鲜红的血流满了白色的绷带。我觉得有门看不见的大炮在向太阳轰击。就像有挺看不见的机枪在向我的生活扫射,我和夕阳一样血红一片……”──因而不禁发出这样的慨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太美的东西离死亡都太近了”。究因于盐湖的奇特与荒凉,小汀因而作了一张画,返家之后将盐湖大图寄给夏玲夫妇留念;而金静兴起了未来想葬身在玻利维亚西南部高原的乌尤泥盐湖,与万古洪荒融为一体。而“我”则在盐湖行旅中,消解了他对故友老赵的歉疚,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梦见老赵,但是却做了一个梦:一个人走在夜晚的盐湖边,听见盐生长的声音。翌晨醒来,恍然大悟于盐和生命都是生长与衰败着的一种变化:夏玲有了孩子之后,为了抚养孩子而离开盐湖,徒留“我”、还有那不停生长的盐陪着他,全文透露出一种孤独、虚无、冷调的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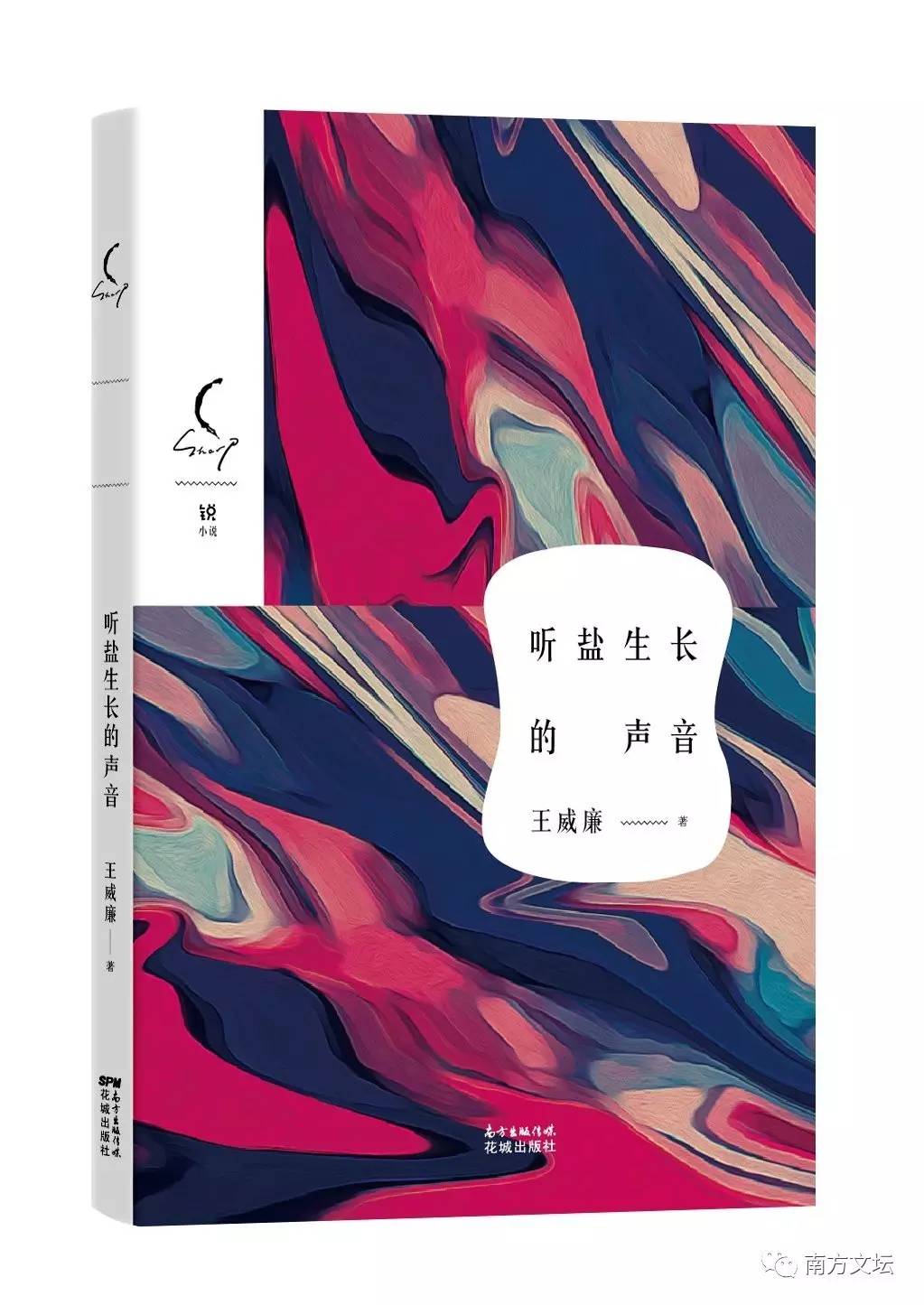
如果说,《北京一夜》和《听盐生长的声音》是一种爱情和虚无的衍生物,那么《书鱼》无疑是人性感官觉受极度灵敏下的一种想象的“变形”──卡夫卡式的现代摹写。文中的书虫(嗜书者)正在迷恋吴哥窟的废墟石壁时,发现了一只书虫(真正的),假的书虫进入了真的书虫的世界,对他而言,书中彷佛是一个虚拟世界,然而现实的他却感染了这种内心的幻象和神秘之事的潜在欲念,进入一种生理性病变:耳咽管开放症,彷佛像一台受潮发霉的旧音箱,由体腔、体液和声带的综合作用产生的怪现象。而最终,他想治愈神秘中医所说的“寄生虫病”,便如读书小童般,大声朗读书中的药草名,虫子因而感到噤声,从而消失,哪一种药名造成回音消失,就服用该种药,便药到病除,以一种现代主义式的变形记述说后现代书虫面临自己成为历史寄生虫的时刻是如何的样貌。
孺慕之爱和智慧之泉
在王威廉的小说中,不乏藉由对长者智慧的倾慕述说一则则隽永的美德,如《父亲的报复》在叙写一向被误以为“北捞”的北方人之桀傲不逊的性格,从抗议拆迁到毅然决然被视为是一个地地道道捍卫家乡原貌的广州人,文中父亲形象的描绘甚为清晰立体。特别是自己身为北方人的父亲,频频招唤已在北方工作的儿子返回故里──广州服务,以为广州才是自己的根,这样的意念成为父与子之间长久的对话与矛盾。劝子回归自幼生长的根──广州,而不是北方那条“虚无飘渺”的根,在此点上,父亲无疑在跟着自己的生命履历做拔河,一头是孤独血缘的故乡;一头是磨练成长的家乡,父亲的流浪历史奠定他的立根想望,他想把广州这个充满恶劣竞争与急速商业化的城市当成比山东更加确立的根柢,于是乎,他将儿子命名为“有为”(康有为的有为)。认同广州成了父亲生命深处日渐沉淀、迭加糅合的“隐形铁锚”,随着时光的推移,他几乎无法移动,至乎“作茧自缚的悲哀”。于是,从妻子眼中的漂泊“伞兵”到故里乡人眼中至死不毁的钉子户形象,一句“羊城河山可埋骨,岭南夜雨独丧神”似蛮横却是威武不屈的英雄灵魂,述说了他对于这块土地的依恋与悲愤力量。
70后代表作家张楚以为王威廉的小说“保持着对已知世界的狐疑和拒绝,让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由里及外的疏离感和硬朗的美感。他让爱与痛、明与暗、拯救与背叛在黑暗中各得其所,我们于废墟中看到了一切”。正是这样的汲汲劝求与坚持,父亲的形象成为永恒,成为儿子心中最完善与给力的强者剪影。
《绊脚石》叙述一场忘年之交舐犊情深、孺慕之情的际遇。一名年轻的出版社职员偶遇一名具有奥地利血统的上海老妇人,从个人的家族历史到民族的集体历史聊谈中,这两个类祖孙的动车聊谈便成为一场有意味的形式。“绊脚石”述说的既是异国血统的老年人寻溯父祖犹太文化迁移至中国的历史寻根;也是青年的父祖辈从珠江三角洲逃难到香港的历史寻根。借着这样的中西文化对照记,呈显了中国在不同历史场景和变异的歧义或者矛盾的面貌:它既是中国“辛德勒”何凤山、挽救奥地利犹太人的母土;也是腥风血雨的“文革”促使一批批青壮年窜逃至香港的故事场景。纯然的,都是不同时代因缘底下铸成的“绊脚石”,让这对忘年之交得以彼此舔抚家国伤口、滋生孺慕之感的绊脚石。
弥补暗黑灵魂的缝隙
在《北京一夜》书中所收录的篇章中,除了有虚无苍白的抒情之作,如《北京一夜》《听盐生长的声音》《信男》;再者,比较具有现代主义的变形叙述和扭曲写作的,就要算是《书鱼》和《第二人》了。《第二人》可谓本书中的惊艳之作,初次读到,甚为震撼,彷佛残忍地将后现代暗黑灵魂中最丑陋及最真实的谜底揭穿分晓。
故事主人公大山做为毁容者──“第一人”,他的被汽油毁容的脸庞呈现了与孪生弟弟小山完全不同的命运,然而他想复制的“第二人”并不是弟弟小山,而是失联甚久的小学同学作家──因为拥有对文字的驾驭,成为他“第二人”的不二人选──因为,“文字是人的另一张脸”,其作“内脸”说明了人性的真实面容和所获得的天赋或者利益,往往是背道而驰。文中藉由大山对于“内脸”的解读与诠释来说明他为何寻找一位文字创作者做为他复制“第二人”的念头:“你在那篇小说里写了两个女人,一个女人在权力的顶端,有着变化多端的表情,另一个女人的内心善良丰富,却得了一种病,失去了表情,你在和这两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中,探索了脸的很多意义”。对一个人的“内脸”有深入了解却反而没有完整外脸的大山,透过绑架写作“内脸”的作家,得以将他人生不能用外脸去面对众人的内在心情(内脸)──比如威慑、威慑孳生的恐怖,恐怖孳生的权力──来发挥他外脸的功能,所以他跟作家说的:“你在小说中表达了权力对脸的塑造,但是你却没想到脸也可以获得权力,这才是脸最奇妙的地方”。大山以他的内脸来驾驭对外脸残缺不足的弥补,然而在他过度利用自己的外脸之威慑所扩张的权力以及财富,却反而使他的内心更加欲求不足,更加的凋零扭曲,以至于他需要寻索一位对脸的探讨甚有深度的作家,来承载他自己内在永无止尽的欲望与怨怼,以及永填不满的深渊与沟壑。于是他想让作家感受到自己的感受,经历自己的经历,以女人和财富来兑换他的脸,而他的脸便成了另一人的另一个人生,于是乎,一阵热浪袭上了作家。此篇对于人性极致扭曲的叙写,故事情节的离奇架构,形成所收录的短篇里最鲜明的个人风格。
《信男》描述一位于出版公司担任仓库管理员王木木,面对离异之后的孤单生活、凋零且乏人问津的工作,在逐渐日暮的垂老心态中,他找到一个生命的出口:写信。写信给珍爱的女儿琪琪;写信给领导;写信给领导的女儿小琪。在寂寥的信男自述中,充分展现出一种现代主义式的空洞感:“在仓库里,变成一个老人已经是我生存的底线了,我不能想象离开这里我还能怎么存活下去?其实我也说不上来,究竟是我丧失了生存的能力,还是在潜意识里迷恋这种老人一般的绝望?绝望,离死亡更近一些,但作为生的壁垒,却更坚固。”他写信给严肃无趣的领导,然而却换来一声声的疑问;他写信给领导的女儿小琪,得到一种生命的跃动;他写信给女儿琪琪,终于得到回信。王木木信男形象的描绘,无疑是藉由写作来疗愈现代灵魂之间的空洞的缝隙,抚摸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交流和虚无的创伤。
《倒立生活》也以一种突梯的思考方式来铺陈一对偶发感情的恋人,如何藉由“倒立”来抒发神女的“反重力情结”,因为“重力”乃是神女悲伤的来源。于是他们模仿壁虎倒立在天花板上,享受眩晕的生活以及性爱。这样的故事虽然夸张而荒谬,但就如王威廉在《写作的光荣》后记一文所述说的:既然传奇已经消亡,要以更高的效率,像流水线那样来生产故事。在充斥网络节奏的时代中,
像王威廉仍旧愿意好好说故事──营匠“小说的事业”的人对写作感到光荣,可谓是以一颗真诚的心灵在虚无的时代中寻找故事。著名作家魏微说道:“王威廉的写作上承先锋,下接现实,使得我相信,萎蘼了二三十年的中国文学也许将在以他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手里得以重振”,不可不谓是对王威廉之小说志业极大的肯定。
陈雀倩,台湾宜兰大学人文暨科学教育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