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唯痞(ID:VP1VP1)
作者:黑豆
本文已获得转载授权
注:本文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2017年3月10日,女总统下台了、“大令爱死了”,我还活着。
多年以后,我肯定会常常想起这个遥远的下午,我坐在青瓦台,仔细打量四面高高的围墙。就像我9岁时,父亲拉着我的手,第一次以“大令爱”的身份住进这里时那样。

我听得到墙外的嘈杂。
我的支持者聚在青瓦台外,等着我恢复元气、重拾淡定。他们在期待,和我拒绝出庭死守青瓦台的态度一样强硬的演讲。
我的反对者也在那。他们高呼着胜利,等着看我难掩憔悴、灰溜溜的被赶出去,还要看到我道歉。

青瓦台的草坪上,还有500多位工作人员,等着和我告别。一个下台总统的告别,是最寒酸的。可我仍然不得不为此把离开青瓦台的时间从6点30分,推迟到7点20分。
到处都是警察。在我被弹劾前三天,首尔就进入了最高级别警戒。已经有支持者为我死去,有的切腹以示决绝,有的在和警察冲突时伤重不治。今天晚上,我三成洞私宅之外,还会有支持者的整夜守护。
我是谁?
大令爱、女总统?还是一个即将被投入监狱、说不定哪天就会离奇死亡的平民?
三天前,那个宣读弹劾我结果的女人,宪法法院的代院长,慌乱、局促。她表情尽量严肃,却忘了摘下粉萌的卷发棒,活像历史书上贴了张怪诞的漫画。

我想告诉她,不必那么慌张。9岁那年,民众为我发明了“大令爱”这个称呼时,我的宿命就已定下。
她只不过和我一样,突然被历史使命砸到身上。
父亲可能早就知道这一切。他幻想过,我作为平民岁月静好的一生。我被送到法国,准备成为一位学者。他奢求用这个温和的身份,能遮掩掉权力的光晕。
1978年到1997年,我逃离权力近二十年里,也曾管窥到我的结局。
“家族中的第一个人将被绑在树上,家族中的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
我终于读懂了宿命。可就在我读懂的瞬间,我的家族永远地消失了。
我甚至无法把答案告诉父亲。因为我,父亲的故居刚被纵火,遗像都被烧毁了。

2
2012年12月19日,我在大选时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戳中了很多人的心。
那时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深的孤独和绝望。
今天,我在三成洞的私宅门前,尽量放慢脚步,和我的支持者握手。等大门一关上,我只能一人睡了。
我没有亲人。妹妹早已和我反目成仇,曾依赖我的弟弟,正在等着他的审判。
我没有朋友,甚至没有能照顾我的人。这么多年唯一支持我的闺蜜,是让我陷入绝境的人。我的团队要留在青瓦台,包括我的厨师。还有几年前,三成洞的邻居们送给我的,两只捡来的小狗。它们现在也被留在青瓦台,不能跟我回家。
能陪伴我的,只有5箱行李。
我甚至开始怀念我的“敌人”,那个李姓前任总统,我两次的竞选对手。
好吧,我承认。即便在三年前我的胜利时刻,我依然有点羡慕他。
他的妻子,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被他称作“最坚强的后盾”。上一届他参加竞选时,4个子女都反对,只有妻子说:“我们不应阻挡男人的前途。”
那是我第一次作为大国家党代表竞选总统。我刚有斩获时,他的妻子提议:
“不要与女人争。在与女人的争吵中,男人从来没有赢过的时候。”
竞选时,他被传出有私生子。他的妻子却很坦然。
“如果有的话,应该送来,那么就能让私生子投支持票了,多得票是好事。”
所以那一次我失败了,他当了总统。他是唯一能善终、优雅卸任的总统,可能也因为有她。
年轻时,他家境很好的妻子,不顾一切的嫁给了他这个穷小子。我也曾有两个时刻,离爱情很近。
一次是我躲避迫害,漂泊异乡时。我又爱上了一个中国人,他高大英俊。我们不能在一起,因为他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甚至名字。因为他,我学了中文。
我庆幸没有选择爱情。我的国家,间于齐楚。我的民族,悲怆而又倔强。既然我没有拒绝萨德的筹码,迟早我的爱情是要烟消云散的。
另一次,就是我的初恋赵云。小时候,爸爸让我我读《三国志》,我爱上了他。每次读到他,我脸颊绯红,心如小鹿的脚步般砰砰跳。
我清晰的记得,毕业那年,母亲曾想为我寻找一位赵云一样孔武的将军。有一天喝下午茶时,她故意问我:“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怎样的呢?”
我羞涩的说:“这个我还真没有想过呢,您这么突然一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几十年后,在中国,他们演三国的京剧给我看。那天,我特意明黄色的传统韩式服装。那阵子我最爱穿黄色,全球媒体都说我笑容像少女般灿烂,很温暖。

3
孤独是我家族的徽章。自觉或是不自觉,每一位成员都佩戴着他。
孤独又是一把双刃剑。我的家族成员既害怕陷入孤独的泥沼,又以一种孤独的高傲姿态,对抗着孤独。
1917年,我的父亲出生于庆尚北道善山郡一个贫穷的家庭。他有段不算光明的历史,贫瘠的土地,让他不得不依附于我们的奴役者。他就读于日本的军校,当过关东军,他骨子里,因此染上了一股孤独、绝望又强硬的气质。

和前任李姓总统一样。几年后,我的母亲,一个忠清北道沃川郡富裕地主家庭的女儿,嫁给了这个政治前途尚不明朗的穷小子。
1952年我出生时,炮火将我的国家轰炸的仿佛失去了根基,甚至连人民的表情,也因为常年战争的阴霾,而显得苍凉伤感。
两年后,我的妹妹出生。直到1958年,被称为“幸运儿”的弟弟出生,父亲才开始交上好运。三年后,父亲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政权,接着便是十八年的高压统治。
当时的我,看不到父亲的血腥和杀戮。我只能看到他板结的脸上,专为我们挤出的微笑;只能听到他写给母亲,软绵绵的情书。
青瓦台里的一家人,慢慢都是爱。但仍不时有孤独又绝望的味道,透过各种缝隙泄露出来。
我的父亲,对我们的生活要求极其克制。母亲从不在国外购物,她会在全家人每月吃烤肉的日子,只烤不吃。
作为总统女儿、“大令爱”,我没有任何特权。父亲要我坐公交车上学,我的裤子,是母亲改小的父亲的军裤。读中学时,我带到学校的是大麦饭和酱土豆。
我不知道,孤独的烙印已经深深的打在我身上,同时烙下的还有家族的神圣感和使命感。
小时候,我爱看战争小说,看《三个火枪手》和《三国志》。中学时,老师对我的评价是“过度成熟”、“因过度慎重而沉默寡言”。
我隐约感觉到,富裕家庭出身的母亲,因不得不克制节俭感到孤独和压抑。父亲也是孤独的,失去母亲后,他终身未娶。
母亲被刺身亡的消息,我是1974年被紧急从法国叫回时,在机场的报纸上看到的。

我独自清洗了母亲的血衣,在日记里写道:“现在我的最大义务是让父亲和国民看到父亲并不孤单。洒脱的生活,我的梦想,我决定放弃这所有的一切。”
我也没想到,这只是我孤独与绝望的开始。
5年后,父亲被刺,悲剧重演。那天他去亲信家吃饭,但杀掉他这件事,“亲信”已经琢磨很久了。
27岁时,我身穿悲戚的黑白装、微微鞠躬后,带着弟弟妹妹离开青瓦台。我给外界留下了一个寂寞的背影,开始了十多年与孤独和绝望的对抗。
我不怪妹妹与我反目成仇,也不怪不成器弟弟的拖累。因为我知道,他们也佩戴着孤独的徽章,那只是他们对孤独的反抗方式。
1990年,妹妹集合了一群人,要求投票罢免我在陆英财团的理事长职务。苦撑两年后,我被迫下台,她上了位。

我尽量避免把这和利益联系起来。
十几年前,我22岁时,为了让父亲不孤独,代理了“第一夫人”的职责,却不小心把20岁的她遮掩在了阴影之下。陆英财团,是母亲成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我一厢情愿的认为,那是她在寻找和母亲的连接。
我也不能阻止姐妹渐行渐远。2008年我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她公开反对我。甚至有可能,她2个月后的荒唐婚姻,也是故意气我。
她的婚礼,我和弟弟都没有参加。那个我不愿意承认的妹夫,比妹妹小14岁,是个私生活很不检点的教授。他化名在我的博客上进行过40多次诽谤,因此被判刑1年半。就在我出事两个月前,妹妹还因为商业欺诈被起诉。
我的弟弟,曾被视为“太子”,被重点培养。在他没有特权的童年,这不过是个让他既没朋友,又被欺负的身份。父母双亡后,太子立即成了被监控的对象。
弟弟他和父亲一样固执,却缺乏想象力和野心。因此他故意颓废又荒唐的彷徨度日,因为涉嫌毒品,6次被立案并强制戒毒。
我的闺蜜,当然和他很熟,我隐约知道他们有事瞒着我。那些财团,因为感谢我的父亲,资助于他。
包括这次,他两次因为涉嫌干政和利益输送被调查时,我依然感到震惊。
既然我已经注定孑然一身,有的事情,是我不愿意想,也不愿意信的。

至于我的闺蜜,我也必须说两句。我隐约知道外面说的有多难听,我也不想辩解什么。
政治,根本没有对错。“政”,也本来就是一正一反。我求助相熟的律师为父亲平反那年,被冷漠的告知“不落井下石的,已是仁慈”之后;我们姐弟,不敢公开祭拜父亲之时,我早已看穿人心的多变和冷漠。
只不过,作为一个人,就算我知道我注定在绝望和孤独中度过此生,我也会忍不住做点什么。
她帮我打扮,帮我买衣服,让我能更像我的母亲。

闺蜜、神的指引、或是另一个世界父母的某种联络,至少可以用来骗自己,我真的有机会能和其它“人”产生点联系吧。
4
有时我会想,是不是我的国家也是孤独又绝望的。
甚至有时,它是自卑的。当年,“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戳中了他们的心。
现在回想,这是不是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和对我父亲的感谢?

而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从不以这样的方式感谢。
1945年,丘吉尔在竞选中落选。他带领英国人民打赢了二战,又发布了开启民智的《贝弗里奇报告》。
然后人们发现,他们不需要丘吉尔代表的保守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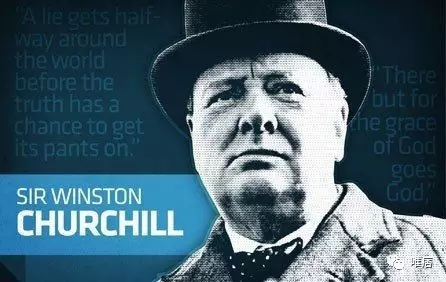
对于结果,丘吉尔也只能无奈的说:“英国人民成熟了。他们学会了选择,他们不需要一个英雄领导他们重建家园 。”
他还骄傲的说:“我打仗就是为了捍卫民众把我赶下台的权利!“
我父亲的悲剧也来源于此。
我所在的土地,在我成为“大令爱”之前,常年被战争蹂躏。后来,它干脆被战争割裂,我所在的那半块,由于之前的规划,更是一无所有。
我的父亲用铁腕,带领大家走向富强。富强开启了民智,然后他们开始憎恶我父亲的铁腕。
不久后,这个叫马孔多的村庄,全体居民都染上了不眠症。得了这种病,人们会失去记忆。他们不得不在物品上贴上标签。例如他们在牛身上贴标签道:“这是牛,每天要挤它的奶;要把奶煮开加上咖啡才能做成牛奶咖啡。”

我知道人们的健忘,我也知道相比残酷和血腥,他们更憎恨贫穷。
1997年的IMF危机,我在街上,看到露宿街头的人们排着长队,等着领取免费晚餐。“我还能独自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吗?死后又如何问心无愧地见父母呢?”
那一刻,我也找回了我的使命感。我决心回来,为我父亲正名。
人们热烈的欢迎我。
因为经济低迷,他们开始怀念我的父亲。2004年的一次调查中,我强权铁腕的父亲,竟然有48%的支持率,而那位“民主斗士”只有14%。
我连续赢得各种选举。最后他们以超过50%的高票,选我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他们把权杖交给我,希望我能开创一个新世界;可她们忘了,我是“大令爱”,就是那个拿着他们厌恶的旧世界权杖的人。

我亲和、开明,一边延续着我父亲的政策,一边对腐败绝不手软。
表面上,新旧世界的转换,只是一瞬间。背后,那么多年的观念和利益,才是牢不可破的。
“汉江奇迹”崛起的财团,三星、SK,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由我父亲缔造。他们是供养我弟弟的人,是拿钱给闺蜜的人。
我消灭不了遗毒,或者,我自己就是遗毒的一部分。
当然现在,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马孔多的村庄,在破译了寓言的瞬间消失,而且不会再出现。

我知道,只有我的家族消亡,才能有一个真正的新开始。
也有可能,这又是一场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他们又一次把权利交给黑暗,用来赶走另一段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