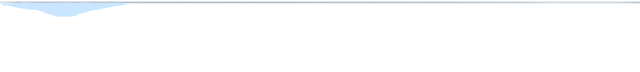节选自《雾中风景》
戴锦华 著 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版权所有。转载务请注明来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
王朔之为中国的达达,其怪异处之一,是王朔小说之形式并不具任何一种先锋或反叛的形态,相反,它是颇为流畅、工整的;换言之,他始终恪守着十分传统的闭锁叙事形式(所谓“我还是愿意按小说中的情节逻辑走,给读者提供一个可以看懂的东西”)。王朔的游戏正在于将有别于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意义结构得体地嵌入传统的叙事形态之中。如果借助格雷马斯的动素模型,似乎更容易辨认其作品的意识形态内涵。在王朔1980年代的大部分作品中,行为主体大都是“生着一张干净脸儿”的顽主,那是一个不从属于任何家庭或社会网络的街头游荡儿。而其中大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元社会的发送者——权威的指令者——消失了,行为主体本人的欲望与意愿便是他自己行为的全部依据。不仅如此,行为主体同为受惠人的扮者——一切为了自己,一切归于自己。叙境中的女性及相关的“爱情”故事,只能充当帮手或敌手阵营中的走卒,构成一个括入组合段,而非欲望客体(即使在他的“纯情名篇”《浮出海面》中亦如此)。王朔小说叙境中真正的、唯一的欲望客体只是金钱——一笔横财,一份介乎合法与非法缝隙间的获取。而文本中的敌手则是可见或不可见的、社会幽冥处的恶势力。与王朔的顽主们不同(他们“没有抢劫走私没有盗宝犯罪集团诸如此类的,有的只是吃吃喝喝和种种胆大包天却永远不敢实行的计划和想法……只是一群不安分的怯懦的人,尽管已经长大却永远像小时候一样,只能在游戏中充当好汉和凶手”),那些敌手才是真正可以杀人越货的歹徒。正是这一特定的动素模型的组合与旧有社会语境的参照,将王朔的顽主们定义为一种反英雄,一种并不新的“新人”——伴随着大陆都市化、商业化进程而出现的个人主义拜金者。王朔1980年代的小说是一些关于欲望的故事,不过那是些关于物欲的故事,那是些将利比多投向商品与金钱的物神崇拜的孤独者。也正是这一动素模型中的敌手——真正的恶棍与不法之徒——将王朔的顽主们摒除在反社会、反秩序的一群之外。如果说王朔小说的语词奔溢与施虐,他的市井气的狂欢毕竟带有某种反秩序的特征,那么这只是有限定、有前提的反叛。它是对大陆中国政治色彩浓重的传统、道德、价值秩序、常识系统的恶作剧式亵渎,所谓“麻着爪儿玩回心跳”;而其真义恰好是一种秩序化的行为:将商品社会的行为价值体系合法化、常识化。因其如此,王朔的顽主们绝少真正击败敌手,占有并保有那笔被追逐的横财(《橡皮人》或许是其中恰当的一例)。事实上,在1987至1988年,面对着奔涌而至的商业化大潮的“一浪”,面对西方世界物质文明的表象和经济、文化渗透的现实,王朔的顽主们并非这一挤压力的抗议者,而是在一种闹剧式的喧嚣——“起倒哄”——中成为这挤压力的一部分。王朔之为边缘,并非出自边缘人的自居与反叛,而只是一种现实的无奈。事实上,只要商品经济尚未成为中国大陆的主导经济,顽主们就只能屈居边缘。毕竟,王朔的顽主恰逢其时地出现并得到了命名,终于填充了那个空荡而寂寞的都市舞台;在补足了那幅“中国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的集体性幻象的同时,王朔之顽主的真实身份——老中国的不肖儿、“文化大革命”的遗腹子——正在不期然之中消解着这幅妙不可言的现代景观:仍是未死方生的中国、未死方生的都市。王朔小说仍是不甚成器的“现实主义”之作,一如他不无“谦逊”地承认:“我不过是时代的秘书”。

《顽主》
然而,事实上成了王朔现象命名式的“王朔电影”(1988年又称电影王朔年),却远没有王朔小说这般单纯。在1988年,颇为引人注目的四部王朔电影(1988年四部“王朔电影”分别是米家山根据《顽主》改编的同名影片,峨嵋电影制片厂;黄建新根据《浮出海面》改编的《轮回》,西安电影制片厂;夏钢根据《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改编的同名影片,北京电影制片厂;叶大鹰根据《橡皮人》改编的《大喘气》,珠江电影制片厂)中,与王朔小说成为和谐的小狐步舞伴、成为佳联偶句的是米家山的《顽主》。影片的片头段落出现了喧哗、纷乱的大都市街景,伴着流行歌手王迪的调侃式的劲歌。而这幅生机勃勃、令人目不暇接的大都市谐谑曲并不像其他中国大陆都市电影那样,只提供了一具悬浮的、空荡的舞台,一张足以乱真的现代景片,而是成了叙境中的一出喜闹剧(三T公司出演的)一方乐土。与其说这是一部“忠实于原作的改编”,不如说这一“电影版的王朔”,正是在小说《顽主》的延伸部凸现了王朔的意识形态真义。影片构造了一幕小说中略写了的“三T文学奖”的发奖仪式;正是这一场景,成了当代中国大陆杂陈的主流话语的大甩卖与活报剧。在一个喜闹剧的格局之中,以电影的话语形态呈现了王朔式的语词亵渎与语词施虐。伴着颇为深沉的音乐,在比基尼女子健美表演和时装表演的行列中,交错出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关于历史的、革命经典叙事的原型形态:拖着辫子的前清遗老,挽着民初妖艳的时装女子(关于民主革命与“复辟”势力的话语);头蒙白毛巾的持枪农民,押着一个日本军官(关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押送着身着将校呢军服的国民党军人(关于1949年共产党人在大陆的必然胜利);梳羊角辫、着旧军装的红卫兵小将挥动大字报,怒向老地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情境)。于是比基尼们便与神圣的“官方说法”同台并置。不仅如此,随着音乐节拍的渐次加快与渐次轻佻,这台杂烩式的演出终于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Disco欢舞:前清遗老与比基尼携手,共产党与国民党军人执手言欢,红卫兵与老地主共舞。于是,此场景的意识形态意图便昭然若揭:它无疑是在调侃与亵渎中消解着权力话语的神圣与历史的深度模式,同时在宣告权力朝向金钱的转移。而取代了原小说中的泡舞场、搓麻将的段落,影片的情节链条将“三T公司”非价值化的一味的闹剧伸延为喜剧性的价值行为。当于观、杨重、马青围起油布围裙,在医院里代尽人子之责,而患者一家数十口人坐在三T公司要吃要喝时;当于观“义重如山”、毅然决定做替身演员赚钱,拯救公司于危难时;较之于叙境中的全部社会好人物——庄严的德育教授、老革命的父亲、“《挺进报》”的儿子、道貌岸然的肛肠科医生、街道居委会的老太——王朔的顽主们无疑成了更真挚、更有道德的一群。影片文本便以反秩序(坑蒙拐骗、游手好闲)始,以新的秩序化(“职业”道德感、个人奋斗、“诚实”劳动)终。影片中元社会的负值呈现显见参照出顽主们在“新”的价值体系中的正值存在。影片的结尾处,在顽主们的视点镜头中,出现了被迫停业的三T公司的大门,门前等候的顾客排起了长长的队列,这无疑成了一次元社会的认可式。它在叙境中完成了现实中难于实现的价值体系的转换。也正是影片文本结构的完整之中,米家山添加了王朔小说所不具的想象性的完满,将人们附会于王朔的集体幻觉呈现为影片的文本肌质。

《轮回》
而其他三部“王朔电影”所呈现的文化症候群,则比《顽主》更为繁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黄建新执导的《轮回》。事实上,即使在第五代导演之中,黄建新也是极富社会使命感的一个。而对于一个富于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来说,他别无选择的现实立场便是对社会“进步”的信念和执行社会批判的责任;这种立场与位置的先在,已确认了他与王朔之顽主们的格格不入。然而黄建新们的困惑,在于置身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置身于改革/变革的大陆社会,同时囿于“世纪之战”的集体幻觉与话语之网,他们的社会/人类进步信念决定他们“必须”认同于王朔,因为后者无疑成了关于现代中国、现代都市的重要而有力的能指;是顽主们填充那座空城,完整了中国同步于世界的那幅奇妙的景观。但是,黄建新们的社会批判立场与责任,决定了当他们瞩目于现代/商品社会时,不可能无视盈溢其中的个人主义的孤独、疏离、无名无助、必然和拜金主义伴生的暴力及罪恶。但作为“五四”文化精神——科学与民主或曰进步信念——的自觉承袭者,黄建新们拒绝因一己的疑虑而动摇他们对“撞击世纪之门”的投入与行动。于是,黄建新选择了王朔,却因此而成就了一个布满裂隙与结构性自相矛盾的电影文本。首先,他在《浮出海面》这个王朔颇为自得的“纯情”故事上添加了主人公石岜倒卖批文、谋得巨款因而遭人敲诈的情节主线;并为这个顽主的世界点染一份绝望的痛楚和阴冷,而这份阴冷刚好来自顽主们所钟爱的舞台——现代社会空间。影片中最为精彩的场景是地铁站中石岜和于晶的游戏及美术馆里石岜和敲诈者的周旋。两个场景中巧妙的机位选取及娴熟的主观视点镜头的运用,将富丽、坚固而冰冷的现代建筑空间呈现为一处处颇为恐怖的迷宫,在都市的人流中、在不可见的角隅处,似乎处处潜藏着威胁。尤其是在后一场景中,敲诈者身着黑皮衣、黑色的摩托头盔,放下的深色面罩上只有阳光扑朔迷离的闪烁;这一切伴以急速地发动起来的黑色豪华摩托,将这群歹徒呈现为极具现代色彩的非人形象:似乎这是群为邪恶势力所操纵的机器人或仿生物。于是,影片所呈现的这处世界化、无名化的现代大都市便与顽主们如鱼得水的老中国未死方生的空间发生了错位。它在成就、完满了那份集体幻象的同时,裂解着那份狂喜和乐观。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黄建新将原作中石岜因车祸而致残的情节改编为主人公被敲诈者报复性地用电钻钻穿了腿骨。事实上,正是石岜的腿在钻头下血肉横飞的特写镜头之后,影片的叙事与意义结构断裂为两截。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建新拒绝历史感的消散。或者说,其作品内在地需要历史感作为依托。只有参照着这一动态的历史进程,黄建新方能自如指认他的时代,定位他的人物,结构影片的表述。他因此而不可能真正认同于“爱谁谁”的王朔。深刻的人文情怀,作为一种“文化宿命”,决定了他为《浮出海面》添上一柄电钻,并在闪亮的钻头与血肉的人体相触的时刻,脱离了王朔顽主们的世界。似乎必须捉回亵渎并试图逃离历史网罗的逃逸者,必须为顽主们注入一颗灵魂、些许痛楚,必须让这如鱼得水的一群同样成为“水土不服者”。自这一场景之后,影片叙境陡然封闭起来。石岜与于晶成婚,敲诈团伙伏法;不仅石岜、于晶在一个窗幔轻拂的新居中享有一对一的、合法的婚姻关系,而且石岜还充满厌弃、义正词严地痛斥昔日的同类。但这尚不足以为石岜赎回灵魂,尚不足以表达黄建新在美丽新世界中体味到的痛苦和疑虑;他由是而为影片《轮回》设计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结局。在这一场景中,石岜满怀自我厌弃地与自己的镜中像面面相觑,而后挥动手杖击碎了镜子。他扳倒台灯,将自己的身影投在漆黑的墙壁上,那朦胧的影子显然不能使他如意。于是,他用手杖在墙上勾出一个硕大、粗壮的人形。而那力士般的身影刚好与现实中孱弱的石岜形成了反讽式的对位。端详片刻之后,石岜走上阳台,翻身而下。而在影片的镜头设计中,石岜之跳楼,与其说是坠向夜色中灯光闪烁的街道,不如说是怀着绝望的情愫扑向空中的一轮红月亮。不约而同地,叶大鹰也为“橡皮人”设计了一个想象性的自杀结局。似乎通过这样一场象喻性的死,黄建新们为顽主设置了一个赎救式,在完满其使命感的同时,为影片叙事赢得了历史感。
然而,真实的历史感自有它浮现的方式。1989年,第四代导演谢飞的《本命年》(《本命年》,导演谢飞,1989年,青年电影制片厂)无意间成了1980年代的谢幕式。都市电影所负载的忧患与狂喜的话语乌托邦,与李慧泉颓然倒下的身影一起消失于历史视野的画框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