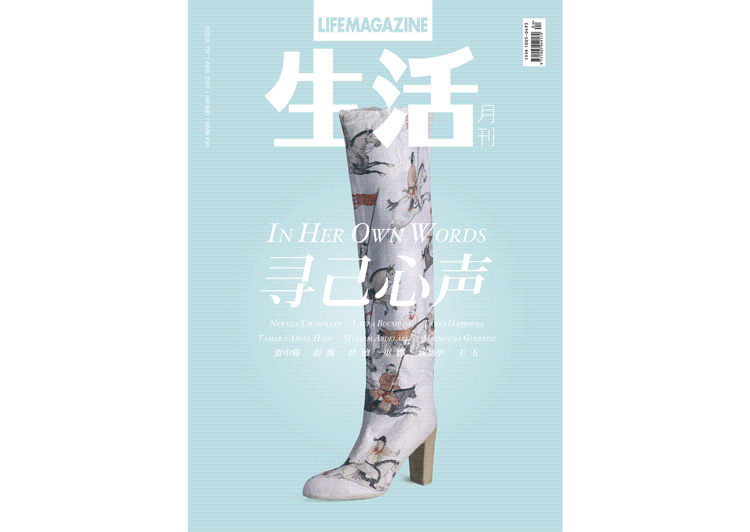如今,《当德彪西遇上杜丽娘》已经历了博物馆版、园林版、剧场版、美术馆版与音乐厅版。观众们常常猜测:I FANTASIE,“我的幻想曲”中的“我”是谁?顾劼亭扮演的角色,是杜丽娘梦里的柳梦梅,还是另一个时空中的德彪西?

顾劼亭大约是在同一时间遇上了德彪西和杜丽娘。
两岁半时,有位钢琴教师来她家做客,发现她“手掌很大,适合练琴”。小小的顾劼亭笔直地坐在加高的琴凳上弹德彪西。而她在苏州的家中,常年回荡着昆曲、古琴、评弹,以及其他的民族民间音乐,这是父亲顾克仁的研究兴趣。18岁,顾劼亭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德彪西的母校。等待她的是繁重的课业和严厉的校规。昆曲被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父亲在家乡创建了中国昆曲博物馆。
德彪西和杜丽娘尚未相遇。前者与马拉美、魏尔伦的象征派诗歌为伴,而杜丽娘还在梨花春影里秉烛夜巡。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弹奏起德彪西,总有一种似曾相识感,让她回想起童年中耳濡目染的东西。德彪西的魂魄,也曾经飘去中国吗?

顾劼亭 GU JIETING
青年钢琴家、舞台导演。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钢琴硕士。旅法期间曾举办“肖邦系列音乐会”、“阿尔贝尼兹系列音乐会”、“利盖蒂钢琴练习曲系列音乐会”等个人音乐会,并与瑞典大提琴家Hanne Dahlvist组成二重奏。2013年受邀回国,成为上海东方交响乐团驻团独奏钢琴家。2014年发起新剧场形态“戏剧x音乐事件”,并正式作为舞台导演进行创作。
她成为百年来巴黎音乐学院的第一位华人钢琴硕士。而作为职业表演者,需要确认自己的独特性。顾劼亭考虑过专研现代音乐或法国音乐,或是创新某种技法,最后却寻归自身:出身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又长年在西方读书生活,强烈的冲突性贯穿了她整个人。“那我就想,找一个冲撞性最厉害的来看看——冲撞未必是坏事啊。”
这两方面原因,促使她着手进行一个规模庞大的类比。最终的研究报告《论德彪西钢琴音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异曲同工》凡70页,探究德彪西这位西方现代音乐的奠基者与中国传统诗词、戏曲、水墨画、园林建筑等,在美学和意境上的共通点。
可她不想让这些“机缘巧合”只是被鉴藏在图书馆中,她要通过最直观的表演艺术将它们传达出来。2013年受邀回国之后,她开始创作总题为“I FANTASIE”的舞台作品,首部钢琴与昆曲的对话定名为《当德彪西遇上杜丽娘》,顾劼亭一个人摸索,像是用针尖将血液里固有的东西一点一点挑出来。
起初,父亲并没有当真。直到2014年创作发布会前两个礼拜,忐忑的女儿才终于在家中堵住了父亲,打开电脑说:“真的请您听一下,我需要您告诉我。”
父亲听完这个15分钟的demo,沉默了很久。讲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我对你的关心太少了”。第二句是,“你应该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在这之后,顾劼亭开始持续地听取专家的建议,将这部作品从15分钟逐渐扩充到完整的60分钟。

在德彪西的作品中,顾劼亭最喜欢的是一套12首钢琴练习曲:“他看似用的是一种非常戏谑的手法,但是其实在里面又有很多他自己的小心思。”
身为导演、出品人和钢琴演奏者,顾劼亭对于一切阐释保有着开放的心态,但就她而言,自己的角色正是“I”,而“I FANTASIE”这部作品,真的就是她的梦。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东方与西方的音乐,仅仅是作为多重梦境的线索。杜丽娘梦见了她和书生的相遇,德彪西梦见了在梦中游魂的东方少女,而对这一场遥远共鸣的诉说,又在钢琴家顾劼亭的梦中。最后,那首《月光》伴随影像中的圆月升起,观众从这场千年的梦中醒来,或许会遐想,自己也曾经是那个追梦的人。
每个人都有独属自己的梦,对作品的感受并没有对错之分。顾劼亭说:“确实,德彪西应该被更多的人在专业上认识,但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是要有更大的部分是开放性的,是面向观众,最起码让观众觉得,‘我’是有这个权力来参与这件事情,有权力来诉说‘我’的感受。”
也有人会问她,现在的作品到底属于什么类型?
顾劼亭并不想将作品划入“高雅”或“通俗”中的任何一类,但她确切地知道,她在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我们作为这样一个经典文化的承接者,就有义务把它传播出来,但是我们要以当代人的态度把它打破、重组。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任何东西都是跟个体发生关系的,作为艺术创作者,应该是走在时代前锋的人物,怎么可以是闭塞的——这扇门我也要关,那扇门我也要关,那你把你师承到的这些东西也关在里面了。”
顾劼亭自觉是清高的,但在创作的时候,她希望能够直面所有的人。

2016年10月13日,“I FANTASIE”剧场版在上海大剧院首演
对话顾劼亭
《生活》:弹了这么多年德彪西,您觉得他的作品在演绎上有什么特点?
顾劼亭:多变。德彪西的作品,对于我来讲,层次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种丰富的程度,“后无来者”我们肯定不能说,但是“前无古人”是真的有,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大量地去运用乐谱里面的表情记号,这种表情记号可能夸张到平均两个小节就会有一个,并且你能看到从ppp(极弱)到fff(极强),跨度、层次是拉得很开的。
很多人对于法国作品的理解就是非常虚无的、缥缈的,但这只是一个印象。它跟技法,不能说完全不相关,但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比如说我前面讲的,他每一两个小节就有一个变化,那我们怎么通过十个手指,去做出这么多的层次、这么多的变化;包括从轻到响这么多的级别,我每个级别定义在哪、某个阶段收在哪个地方⋯⋯这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在曲子中摸索的阶段。但是首先你要有这个意识,就是说,休想用同一种弹法来完成一个作品。就像你看印象画,你说印象派画家给予你的感觉就是雾蒙蒙的,所以他这个画就是从头到尾不用力地画出来的?肯定不是这样的。反而他们叠加颜料的方法比以前很多派系的画家更为复杂、更为精准。

顾劼亭位于上海巷弄的工作室中,一架1976年制成、自欧洲拍回的羽管键琴。
《生活》:二月底在MoCA的首演,您用的钢琴很特别,琴盖上印着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吻》。您对这幅画作有特别的理解?
顾劼亭:这一次是我们跟Bösendorfer的项目合作,他们知道我们想讲一个关于女性、关于情感的话题,所以给了这一架克里姆特限量版的钢琴。也有人会问我们,《吻》这幅画放在我们整个大作品里面,是不是有一定的含义。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作品蛮有意思的一点是,每一个参与者,包括影像的部分,包括我们音乐,昆曲、钢琴、电声等等,包括这架琴也是,每个东西在这个舞台上,它都有自己的意义和态度在这里。
《生活》:这部作品从2014年首演,之后经历了很多的空间形态。空间的变化有没有带来不同的体会?
顾劼亭:可以这样说,一旦我们把这个作品做成开放式的,那么空间也成了其中很重要的元素之一,它同样以它的态度进入到了整个作品的阐述当中来。包括为什么我们最后把这个作品定义为“音乐事件”,也是因为我们把空间放了进来。我们绝对不会说,因为形成了这么一套班子,就把这套班子从A点搬到B点,从C点搬到D点。如果是这样搬的话,这些空间是没有意义的,它是复制型的。
2014年我们是在苏州博物馆做了一个短短15分钟的创作发布演出,这个地方是精心挑选的。因为苏州博物馆是完全符合了我心目当中“东西方融会贯通”的这么一个地方,首先设计者贝聿铭他的经历就是东西方都打通了,而他的作品你可以看到水、看到桥,看到庭院,东方式的机要的东西他都在,但是结构又完全是西方式的,那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太适合来阐述我们的观点了。后来我们进了剧场,进了园林,包括在龙美术馆西岸也演过,到今天MoCA、音乐厅等等。如果说苏州博物馆跟我们的作品是百分百match,其实别的地方乍一看都有点像钢琴和昆曲放在一起的感觉,风马牛不相及的,或者说会让人怀疑是不是个噱头。但是渐渐地适应了自己的节奏以后就会发现,并不是说一定要找一个跟我百分百match的,我才能演。任何空间,只要你将它融入到作品的阐述里面去,而不是把空间推开,它就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部分。所以今天在空间上,哪怕我就在上海新天地的一个广场上演出,这个空间的设置做好以后,它也可以完全地融入其中。

《当德彪西遇上杜丽娘》中,国家一级昆剧演员吕佳等饰演杜丽娘
包括对于观众也是,最初我们会束手束脚,觉得是不是我们要请对钢琴和昆曲已经有一定涉猎的人群,是不是这些人才能读懂我的东西。实际上我们一场一场演出试下来以后就发现,有时候你的态度就决定了观众是不是对你有戒心、有顾虑。我们首先做的就是消除所有的顾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打开,随便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它,随便你是不是懂,观众才会觉得说,那我愿意来尝试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这在我以前的行业是很困难的,就是说如果你不懂,你来评判,人家直接把你划分为外行嘛,你有什么权力来批判来指责这个东西?哪怕你懂音乐,你懂古典音乐吗;哪怕你懂古典音乐,你懂德彪西吗;哪怕你觉得你懂德彪西,你真的懂吗?其实真正转到这个行业状态的时候,确实是有这个界限在的,确实,德彪西应该被更多的人在专业上认识,但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是要有更大的部分是开放性的,是面向观众,最起码让观众觉得,“我”是有这个权力来参与这件事情,有权力来诉说“我”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对是错,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都来评头论足,这个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生活》:2009年您在法国完成了一篇论文,论证德彪西的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曲同工之处,能不能分享其中的几点发现?比如提到德彪西对于休止符的大量运用,像是一种东方式的留白。
顾劼亭:第一个是关于他这个休止符的运用。从表达上来讲,按照中国人的讲法,你就完全可以感受到这是一种“留白”,所谓的无胜于有,好像特别地“东方哲理”哈,恰巧德彪西他也用的是这样的方式,并且他也想做一种含蓄的表达。第二个是,我当时去看了大量大量的他的手写谱,包括后来的印刷谱,发现德彪西作为一个钢琴作品产量非常大的作曲家,很有意思,他非常喜欢运用三行谱——正常来讲,以前的钢琴作品只会用两行谱,高音谱号和低音谱号,一个给右手一个给左手,除了音符多得写不下以外(比如李斯特)。德彪西的谱子完全不是。他没有几个音嘛。所以,他在写谱的时候完全只是为了一种美感,而采用了三行谱。它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观感呢?就是很稀很稀。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美感?你就会想到我们前面讲到的留白这一点。所以我为什么说德彪西绝非可以仅仅用单一性的词来形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立体性结构非常好的人,甚至他都顾及到了谱面上的观感。
还有一个好玩的点是他写命题音乐嘛,就比如说我们用在作品中的一首,就叫《月落荒寺》(Et La Lune Descend Sur Le Temple Qui Fut)。这不是我为了配合这个作品翻译成这样的,不是说因为我们正好讲到杜丽娘回魂以后发现这个牡丹亭都没有了,变成一个很苍凉的梅花庵观,在这个时候我们承接上《月落荒寺》这么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是德彪西命名的。很好玩的是,在整个法国都没几个寺,而寺庙对于欧洲人来讲,能够感受到荒凉的部分,更是几乎没有了。所以我甚至去大量地搜索,到底他是真的看到了这个寺庙,然后写下了《月落荒寺》,还是说他写下了他当时心中的那一种和声体系,最后他认为这种意境是“月落荒寺”,这些史料上都没有记载。但是在讲到这种共通性的时候,我们可以抛开这些史料,因为摆在面前的这个东西,它就是通的。
《生活》:您对于跨界这个概念怎么理解?它在当下是一种大趋势么,还是说只是部分从个人出发的尝试?
顾劼亭:我觉得跨或者不跨,都可以。但是,如果没有跨界这个部分,在这个时代是不可能的。在过去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相对来讲是单一的,现在是不是四面八方而来?特别是在互联网诞生和推广之后的这一代人,他们可能(生来就)已经是一个跨界时代、立体时代的人。我更多地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所以,一个艺术门类、艺术社会当中的一种形态,怎么可能逃避这个问题呢?到了某一天,跨界就是一个常态了,有一部分人就是在从事着立体式的、铺陈式的艺术表达。
当然在最初期探路的时候,肯定会出现很多的状况,包括可能由于我们所认为的跨界艺术出了一些状况,而束缚了我们对于跨界的想象。很多人想到跨界就觉得说,我有一杯茶,我有一杯咖啡,两个东西兑一兑倒在一起给你,这就是跨界了。慢慢地更多的人就会发现,其实跨界是个很大很大的概念,当然也会出现越来越多好的立体式的舞台艺术——其实不仅仅是舞台艺术了,因为在整个当代艺术的范畴,大家都在打破格局。像是走在最前线的舞蹈,其实当代舞诞生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跨界载体了,因为它运用的已经不仅仅是舞蹈的语汇,还潜藏了很多其他东西。包括话剧,现在也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作品了,它采用的很多舞台调度,肯定不是从话剧自身衍生来的。
破格局这件事情,不是说我要把你原来这件东西彻底推翻,而是原来好的东西,加上现在我新发现的东西,让它成为一个新的局面。从来没有说我做了跨界音乐,我就觉得古典音乐不好。我还是热爱古典音乐,而且我自认为哪怕我的作品是开放性的,我在做古典音乐的时候仍然是非常严谨,而绝非就是花里胡哨、自成一派。我觉得越是严谨地在做某一件事情的人,才有能力更好地来破这个格局,否则就是乱破嘛,对不对。一定要在已有的格局之上,你才能够找到新的方向。
* * *
以上 节选自《生活月刊》2017年4月号
"乐" 栏目《顾劼亭 弹琴给的信使》
撰文:侯婧婧,摄影: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文字和图片版权均受到保护
任何未经允许的复制或转换都将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