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牟学苑老师《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的发生学研究》一书第一章(赫恩的“实像”与“虚像”)第一节(关于赫恩的几个问题)的第二、三部分。
【作者简介】牟学苑,1977年生,山东淄博人。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比较文学及西方现代派文学。著作有《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小泉八云思想与创作研究》等,译著有《消逝的话语:现代性、幻象、日本》等。
《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的发生学研究》(节选)
文/牟学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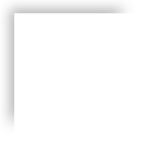
“归化”与赫恩的身份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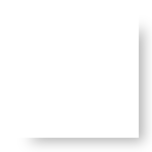
1890年4月,赫恩抵达日本,自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这片古老的土地。他在日本娶妻生子,甚至加入日本国籍,变成了日本人“小泉八云”。这在十九世纪末的日本无疑是件奇事,尤其是入籍日本,或曰“归化”一事,更是许多猜测、想象、误解的来源。

【拉夫卡迪奥·赫恩(Hearn Lafcadio,即小泉八云,1850-1904),日本作家、翻译家、教师。】
其实即便在今天,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英美人士入籍日本的情况也并非司空见惯。在赫恩的时代,西方人与日本人的通婚(主要是西方男人娶日本女人)在口岸城市并不少见,但极少有人因此加入日本国籍。多数西方男子只不过把这种婚姻看作是一种异国生活的调剂,一段猎奇的经历,有时甚至是一种变相的买春(如洛蒂的《菊子夫人》中所描写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婚姻本质上只是同居,是不被法律承认的。如著名的英国日本学家萨托[1]、桑瑟姆[2]等,都曾与日本女子同居生子,但最后都抛妻别子回国了。葡萄牙人摩拉蔼思[3]是与赫恩齐名的“爱日本者”,他也长期与日本女子同居,但并没有到入籍的程度。而赫恩能够为了妻子入籍,这与他心地的善良和对日本的热爱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对日本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喜爱是赫恩“归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有一个细节是很有意味的:赫恩在《日本试解》的附录里收录了赫伯特·斯宾塞写给金子坚太郎[4]的一封信[5],斯宾塞在信中给日本当政者提出的建议十分保守,甚至超过了赫恩的预想,比如禁止外国人在日本拥有土地、财产,掌握矿业、海运,乃至建议禁止日本人与外国人通婚。斯宾塞的这些建议对于日本相关法律的制定是有促进作用的,直接影响了赫恩的切身利益,是造成他长期困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赫恩不但没有什么怨言,反而认为这些建议是非常正确的,他甚至说:“以我的愚见,非常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建议没有被更严格地遵循。[6]”赫恩的这种态度除了他对斯宾塞敬如天神般的崇拜,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日本的热爱已经超越了自身利益的局限。
但如果将赫恩对日本的这种热爱大肆渲染,甚至加以神化,就偏离了事实的真相。赫恩赴日、结婚、入籍、定居等种种选择,是他生存境遇中的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仅仅出于什么“理想”。就“归化”这件事来说,赫恩更多地是从实际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1890年4月,赫恩抵达日本。赫恩赴日,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机缘,同时也是为了谋生。此时的赫恩对日本只有一些从书本上得来的模糊印象,并无“倾慕”可言,相比来说,倒是对中国,他的兴趣还更大一些。日本对于此时的赫恩,就是一个“异国”或是“东方”的形象,与西印度群岛对他的意义没有太大的差别。
抵日后,赫恩与哈珀斯出版社关系破裂,失去生活来源的他首先要在这陌生的日本生存下来。8月,经张伯伦教授介绍,赫恩赴松江任教。经过同事西田千太郎的撮合,次年1月,赫恩与小泉节(1868-1932)结婚。小泉节出身于松江藩士之家,后成为远亲稻垣家的养女,稻垣家也是一个败落的士族。1887年,稻垣家为节子招赘了一个叫做前田为二的人,但前田不堪这个贫困家庭的重负,不久便逃走了。所以赫恩与小泉节完婚的时候,都可算是“梅开二度”。在小泉节的时代,日本人特别是士族嫁给外国人还算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再加上家庭经济的困窘和两人结合的速度,这件罗曼司中,看不到什么爱情,倒有几分生存的无奈。
但赫恩与小泉节婚后感情甚笃,于是赫恩开始认真地考虑他的家庭的未来。赫恩在结婚时其实只是举行了婚礼,并没有进行法律注册,这也是一般欧洲人与日本女子结婚的通行做法。当然赫恩的出发点倒不完全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他更多是为了他的“新娘”考虑。按照当时日本的法律,赫恩如果与节子在英国领事馆注册结婚,节子以及他们未来的子嗣都将成为英国公民,但外国人不能在日本拥有不动产,所以他们将无法拥有自己的土地、房产,赫恩死后,妻儿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把节子带到外国去则是赫恩无法接受的。一者他在日本正乐不思蜀,不愿回到压力巨大的西方社会;二者对母亲境遇的深深同情使得赫恩不愿让同样的悲剧在自己的妻子身上重演,他说:
把这个小妇人带到另一个国家将会使她非常不快乐;因为她将失去自己的社会氛围——那种思维和感觉与我们的完全不同,这是任何关心和舒适都不能补偿她的。[7]
所以1891年夏,赫恩就开始认真的考虑入籍问题,因为如果赫恩变成了日本公民,节子就可以保留自己的公民权。8月,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赫恩说:“只有变成日本公民,我想我会这么做的,才有可能让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8]”。赫恩曾为此事咨询过张伯伦,张伯伦8月26日致赫恩的信中说:
你知不知道一个英国人变成日本人的唯一途径就是被日本人招赘?我看不出除了变成一个英国妇人你妻子还能做什么。还有第三个选择,无疑这个方法在这个国家是被广泛采用的,即避免任何法律的婚姻。我估计你不太会想变成一个日本人,而要把一个日本妻子带到美国去也会让人大费踌躇,她可能会非常不快乐。[9]
大概是张伯伦的建议起了作用,赫恩暂时搁下了入籍的事。1893年11月,赫恩的长子一雄[10]出生了。中年得子的赫恩对一雄非常喜欢,入籍的心情也急迫起来。在儿子出生的当月,赫恩即开始为与妻子正式注册的事奔走,但事情比想象中要难得多。他在给西田千太郎的信中说:
然而这整件事就是个困局。我自己成为日本公民,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但现在看来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横滨的一个英国人,在变成日本人之后他的工资立即减到了非常少的地步,人家说:“现在成为日本人了,就要安心于像个日本人一样生活”。[11]
而此时的赫恩供养着节子的养父母、养祖父母、兄弟、仆人等一大家人,“像个日本人一样生活”是他绝对无法做到的,所以入籍的事又被耽搁下来。直到1895年,赫恩在神户的《编年史》杂志工作的时候,这件事才进入正轨。这时的赫恩已经积蓄了一定的财产,而且给他支付薪水的不是日本政府,无需担心薪水降低的问题[12],赫恩才下定决心“归化”。1896年2月10日,赫恩办完了入籍手续[13],正式成为日本人“小泉八云”,从法律上说,直到此时,他才与节子正式结婚。

【赫恩与妻子】
赫恩在书信中跟许多朋友都讨论过“归化”的问题,他有方方面面的考虑,妻子、儿子、房子、票子,甚至连“归化”后儿子长大要服兵役都考虑到了,却从来没有提过放弃作为一个英国人的身份的内心感受。可以说赫恩考虑“归化”问题基本是从经济和法律的角度出发的,很少有文化、心理上的障碍,日本始终是他旅居的异乡,“归化”并没有改变这一点。赫恩也并非刻意要终老日本,他在日本定居主要还是出于生活的考虑,在被东大解聘后他在西方的几个大学谋求过教职,而且几乎成行,后来也是因经济问题才作罢。无论在“归化”之前还是之后,赫恩对别人介绍自己时都说自己是英国人(实际上日本人也没有因一纸法律文书就把赫恩看作了自己人),因为他的自我身份认同始终都是一个英国人;“归化”后他的大多数书信依然署名“拉夫卡迪奥·赫恩”,而不是他的日本名“小泉八云”[14];而在创作上,赫恩从来没有也无法改变自己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日本文化的“他者”的角色。所以对赫恩的“归化”问题,我们应该重视,但绝不应该过分夸大其意义。如路易斯·艾伦所说:“他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无可救药的西方式的,他的文学背景是欧洲式的,他的衣食父母——除了他的教职之外——是那些美国文学期刊的读者们。[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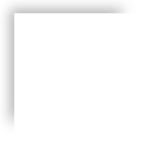
赫恩对日本文化的“狂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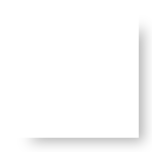
赫恩对待日本的态度,可说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了。一般人提到赫恩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对日本文化的狂热,这也是他最为人称颂、好奇、不解或是厌恶的地方。就事论事地说,赫恩对日本文化的热爱确是实情,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我们同样可以举出赫恩不喜欢日本和日本人的证据。要理解赫恩对日本的热爱,我们就必须还原赫恩所处的历史语境,找出制约和影响他的种种因素。
赫恩在赴日之后的确对日本相当喜欢,他喜欢日本的建筑、风俗、生活习惯,喜欢日本人,对日本妇女赞不绝口[16],说日本人的脚娇小而匀称[17],连眼睛和皮肤都是日本人的好看些[18]。此种心态称之为“狂热”绝不为过,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赫恩在抵日之后不久就陷入了这样一种“狂热”?
赫恩对日本的喜爱背后首先有个人生存境遇的因素。赫恩的前半生颠沛流离,他又不善理财,所以一直为金钱所苦。而到日本后,赫恩收入颇丰,又娶妻生子,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自然不会对日本抱有恶感。赫恩在《辛辛那提商报》做记者时工资是每周20美元[19],在新奥尔良时大约是每月40美元[20],但美国的物价水平较高,赫恩在新奥尔良租住的房间租价是每周3美元[21],而且用这样的薪水赫恩还购买了2000美元左右的“奇书”[22],不难推测他平时的生存状态。赫恩在松江工作时月薪是100日元(在东京大学任教时最高达到每月450日元),当时日元与美元的比价大约是2比1,所以从数目上看赫恩的工资比在美国时要高不少,而且由于日本的生活水平较低,这笔钱在日本绝对可以算是高收入了。“所以我可以住城里几乎是最好的房子——除了几个非常有钱的人以外——有几个佣人做饭,还可以让我的小妇人穿得非常好。[23]”这种生活是赫恩从未体验过的。正如比斯兰所说:“他从中学和师范学校得到的工资,再加上他用笔挣来的钱,使他生平第一次在金钱上宽裕起来。[24]”除此之外,因为教学认真,又没有西方人的傲慢,赫恩在学校受到学生的欢迎;他出手大方,小贩、旅店老板等普通日本人也对他热情备至;岛根县知事与他交好,报纸上常有他的演说和消息;甚至连他的身高在日本都不再是一种缺陷了。这样的日本当然是赫恩的乐园,他没有理由不热爱它。
除了个人生存境遇的影响,赫恩对日本的热爱还源自于他的“东方梦”。赫恩在西方社会艰苦挣扎的四十年使他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他对于西方社会发达的现代工业文明体系深恶痛绝,而对东方文明则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实际上这种心态在十九世纪末的西方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知名的如托尔斯泰、斯特林堡等都将东方文明视为治病的良药。所以当赫恩亲眼看到日本时,愉快的个人体验与怀抱的梦想相印证,便很快将日本看作了他所追寻的乌托邦。赫恩对日本夸张的赞颂,其实是作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对立面出现的。比如他对日本人脚的赞美是因为它们美得天然,不像西方人的脚被皮鞋折磨成了畸形;他爱穿和服是因为舒适自然,不像西装那样假正经;他爱日本人,因为他们“温和”、“天真”,不像西人傲慢虚伪;连日本的落后他也并不嫌弃,因为这是没有受到工业文明污染的标志。
所以所谓赫恩热爱日本文化的说法,既正确又不正确。因为在赫恩的心目中有两个日本,一个是美丽的、自然的却在一天天逝去的“老日本”,一个是丑陋虚伪而势力却越来越大的“新日本”。赫恩认为“老日本”才是真正的日本,他拜访佛寺、神社,尊崇传统的风俗,过日本式的生活,挖掘各种传说、怪谈,而“新日本”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西方文明入侵的产物。但赫恩的问题在于,任何一种有生命的文化都不是静止不前的,日本文化的特质之一就是善于吸收、学习外来的文化,明治维新之后快速变化中的“新日本”又何尝不是“日本文化”呢?但赫恩对这样的“日本文化”是敬谢不敏的。此外,任何异质文化的传递都不可能只是历史的变迁和空间的平移,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虽然引进了西方的工业、制度、观念乃至生活方式,但许多来自西方的东西经过选择、碰撞、融合后实际已经日本化了,而赫恩却要徒劳地把它们剔除出来,或是将其视为皮相而非日本文化的精髓,这种观念是有些机械的。所以赫恩热爱的,准确的说,其实只是“传统的日本”,特别是日本的宗教文化。
其实西方人对东方的批评不一定全出于傲慢,对东方的赞美也未必尽是善意,如鲁迅所说: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25]
赫恩向以平等为追求,赞美日本主要是出于对西方文明的厌恶和对东方文明的幻想,自然并无恶意,但不得不承认,在赫恩抵日的初期,他同普通的旅游者一样,也有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在杵筑,由于西田的介绍,赫恩得以进入出云大社参观,成为第一个进入出云大社的欧洲人。对此赫恩非常自豪,在《杵筑: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中几次提及:“一想到我看到了其他外国人没有权利看到的东西我就禁不住有些得意[26]”;小泉夫人也回忆说:“他非常喜欢旅行,但总是选择那些偏僻的,没有外国人去的地方。[27]”所以即便是对“传统的日本”,赫恩也有他自己的选择标准。赫恩在他的“日本创作”中,从来没有写过歌舞伎、能乐、浮世绘、相扑和艺伎,而这些是普通西方人对日本最为好奇的一些标志性事物。
赫恩对日本文化的这种过滤,有个人兴趣的影响,同时也是西方读者对日本的阅读期待的一种表现。在赫恩的时代,随着日本开国后与外界交流的频繁和国力的增强,西方人对日本的兴趣越来越大,而赫恩并不是描写日本的先行者。在陈词滥调的日本已被一部分读者厌倦的情况下,自然会有猎奇的需求,而赫恩以宗教、习俗为描写重点的“陌生的日本”恰好迎合了这种需求。在赫恩的书信中多次提到,出版社对于他的创作会提出许多要求,这种要求不仅是在形式方面的,也会涉及到题材的选择,而这种要求其实也就是西方读者阅读期待的间接表达。
赫恩对日本全盘接受的“狂热”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891年11月他迁居熊本后,赫恩就开始体验日本的另一面。如比斯兰所说:“松江是老日本。而熊本则代表着变化中的远不能令人满意的日本。[28]”熊本的天气没有赫恩想象的温暖,城市更加欧洲化,没有什么像样的佛寺、神社。九州人也不太热情,同事、学生都不跟他讲话,孤独的赫恩在每天午休的时间只能到学校后山上与墓地里的石佛相伴[29]。这时赫恩的书信中充满了愤懑和不满,日本在他心目中那道理想的光环逐渐褪去了。1893年5月,赫恩在一封“忧郁的”信中对日本充满了失望:“我第一次想要说:‘这该死的日本!’记住,失去民族独立性可能还不是她最坏的命运。[30]”而在半年后的另一封信中,赫恩则表达了回到1400年前的日本的希望,因为那才是他所爱的“真正的”日本,而“熊本对我来说根本不是日本,我恨它[31]”。其实赫恩的失望并不完全是由于民风和地域的差异,因为许多负面的东西本来就存在于日本文化之中,只是他没有看到而已。
熊本的经历虽然令赫恩痛苦,却使他的日本观更加接近真实。但如此一来,赫恩再也写不出《陌生日本之一瞥》中那种单纯、快乐,充满异国情调和理想色彩的日本了。所以赫恩后期越来越倾向于创作冷静、客观的学术化作品,这当然要归因于他对日本文化理解的加深,但同时也是一种对思想矛盾的逃避:一方面他深知日本文化的多面性,而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自己千辛万苦才寻求到的“理想”,无需明确的情感态度的怪谈类作品和学术化创作就成了他的最佳选择。
注释:
[1] Ernest Mason Satow(1843 - 1929),英国外交官,日本学家。曾被派驻日本、暹罗、乌拉圭、摩洛哥和中国,其中在日时间近三十年。曾任英国驻日公使、驻华公使,1906年退休。著有《外交实践指南》(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一个外交官在日本》(A Diplomat in Japan)等书,是日本亚洲协会(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的创始人之一。
[2] George Bailey Sansom(1883-1965),英国历史学家,日本学家。著有《日本文化简史》(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日本史》(A History of Japan)等书。
[3] Wenceslau de Moraes (1854-1929),曾任葡萄牙驻日领事,著有多部介绍东亚及日本的作品,如《大日本》(Dai-Nippon, 1897)、《德岛的盆踊》(O Bon-Odori em Tokushima, 1916)等。
[4] 金子坚太郎(Kaneko Kentaro,1853-1942),日本政治家,曾为伊藤博文的秘书官,历任农商务相、司法相等职,曾参与日本宪法的拟定。
[5] 1889年金子坚太郎曾奉伊藤博文之命,携英文本日本宪法前往欧洲,征求各方意见,并会见了斯宾塞。1892年8月,斯宾塞曾给金子写过三封信。写于21、23日的两封信在转给伊藤博文阅后,金子向斯宾塞转达了一些疑问,所以26日斯宾塞又写了第三封信,此信实际上是对日本当政者特别是伊藤博文的答复(可参见David Duncan,The life and Letters of Herbert Spencer, London: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6. 319-323)。赫恩在书中收录的就是写于8月26日的第三封信,此信在斯宾塞逝世后,于1904年1月18日在《泰晤士报》上首次公开发表。
[6] Hearn, Lafcadio, Japan: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 (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12),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464
[7] Hearn, Lafcadio, Life and LettersⅡ(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14),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163
[8] Hearn, Lafcadio, Life and LettersⅡ(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14),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146
[9] Koizumi, Kazuo ed., More Letters from Basil Hall Chamberlain to Lafcadio Hearn and Letters from M. Toyama, Y. Tsubouchi and others, Tokyo: Hokuseido Press, 1937. 26
[10] 赫恩与小泉节共生育了四个孩子,长子一雄(Kazuo),次子严(Iwao),三子清(Kiyoshi),幼女寿寿子(Suzuko)。
[11] Hearn, Lafcadio, Life and LettersⅡ(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14),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267
[12] 明治维新后,作为“求知识于世界”的一项举措,日本政府雇佣了大量外国专家(主要来自英美等国),1868年至1900年,政府雇佣的外国人共计2400人。相比于日本人,明治政府付出的工资相当可观,最高达到两千日元,而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工资也不过800日元。多数受雇外国人的工资在200日元上下,赫恩在松江时月薪100日元,算是中下水平,但他所在中学的校长工资是55日元,一般教员只有十几日元上下(参见Ardath W. Bruks ed., The Modernizers: Overseas Students, Froeign Employees, and Meiji Japan,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5. 226-241)。如果赫恩入籍的话他就不能再享受作为外国专家的高工资,所以难免会有顾虑。赫恩后来在东京大学任教时已经“归化”,但他仍按外国人享受每月400日元的薪水,其实是作为特例处理的。
[13] 赫恩从1895年下半年开始办理入籍手续,具体过程较为复杂,所以关于赫恩正式入籍手续完成的时间,在日本研究界有不同的说法,本书取信钱本健二、小泉凡所编赫恩年谱的说法。
[14] 1896年赫恩署名“Y. Koizumi”或英和名并署的信件稍多一些,在8月致西田千太郎的一封信后甚至还歪歪扭扭地写了“小泉八云”的汉字,这可能是出于刚刚入籍的新鲜感,此后署名“小泉八云”信越来越少,而且大多是发给日本朋友的。
[15] Allen, Louis, “Introduction”, Louis Allen and Jean Wilson eds., Japan's Great Interpreter, Folkestone: Japan library Ltd., 1992, 1
[16] Hearn, Lafcadio, Life and LettersⅡ(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14),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137
[17] Hearn, Lafcadio, 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 Ⅰ,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4. 11
[18] Hearn, Lafcadio,Japanese Letters(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16),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142
[19] Bisland, Elizabeth, “Introductory Sketch”, Lafcadio Hearn, Life and LettersⅠ(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13),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49
[20] Hearn, Lafcadio, Life and LettersⅠ(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13),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155
[21] Hearn, Lafcadio, Life and LettersⅠ(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13),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160
[22] Hearn, Lafcadio, Life and LettersⅠ(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13),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284
[23] Hearn, Lafcadio, Life and LettersⅠ(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14),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146
[24] Bisland, Elizabeth, “Introductory Sketch”, Lafcadio Hearn,Life and LettersⅠ(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13),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113
[25] 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一卷)·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16
[26] Hearn, Lafcadio, 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 Ⅰ,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4. 208
[27] Noguchi, Yone, Lafcadio Hearn in Japan, Yokohama: Kelly & Walsh, 1910, 62
[28] Bisland, Elizabeth, “Introductory Sketch”, Lafcadio Hearn, Life and Letters Ⅰ,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6. 125
[29] Hearn, Lafcadio, Life and LettersⅡ(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14),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206
[30] Hearn, Lafcadio, Japanese Letters of Lafcadio Hearn,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0, 99. 赫恩的原文为“D——n Japan!”即“Damn”一词的避讳略语。
[31] Hearn, Lafcadio, Life and LettersⅡ(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14),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263
本文原载于牟学苑《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本期编辑
李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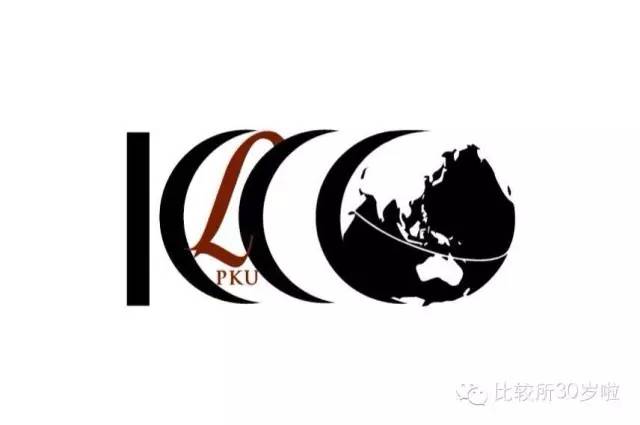
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公众号
比较所30岁啦
微信号:pkuiclcc30
尊敬的畅言客户,您好。您所使用的网站评论功能已广告作弊被限制使用,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电话400-780-9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