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王小波的研究,“坚硬的冰”或“炽热的火”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渴望有一股和煦的风吹来,吹散笼罩在王小波头上的阴霾与光环。唯有在宽容、多元、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才能窥见王小波的真身。
原文:《王小波在当下》
作者:山东师范大学 张丽
苏州大学 房伟
王小波是20世纪90年代文坛特立独行的存在。今年是王小波逝世20周年,他生前受冷落,逝世后名声大噪。这么多年过去,何以大家对王小波的关注热情不减?这种狂热是否有其合理性?当下对王小波的接受是从哪些维度进行的?存在哪些问题?
“后现代性”维度
对王小波的研究和接受,其实存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维度。所谓现代性维度,即注重王小波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和杂文,对建设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作用,特别是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功用,对现实有比较强的抵抗和反思性。后现代维度,注重从多元化、解构、权力分析等角度进行解读,更关注他的虚无主义色彩,更注重王小波作品的消费因素和流行因素。

可以说,王小波身上这两种因素其实都存在。后现代性,源自整个1990年代之后中国文化格局。全球化的想象之中,告别革命、性别政治、多元文化与消费主义等思维,都影响了王小波的创作。王小波小说之中的现代性因素,则更具本土生成性,是针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现实缺乏自由主义思维而言的。由此,考察王小波去世二十年之后的研究,就会发现,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王小波具有了文化资源的本土原发性和全球化视野下的普世性。
学者孙郁曾言:“王小波式写作改变了文学生态,在这一百年内独一无二,是原点般的存在。从他开始,我们有了拉伯雷、卡尔维诺、马克·吐温式的写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理论登陆中国,表现出深度削平模式。纵览王小波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后现代性因子——他以戏谑、调侃、反讽的笔法解构一切,消解革命神圣光环,打破时空、虚实、真伪的限制,反思历史和现世的荒谬,消解逻各斯霸权,以自由之笔抒写历史与权力的游戏。
1998年,戴锦华就指出《黄金时代》是“荒诞喜剧”,陈清扬与王二之间存在“无所不在的化妆狂欢”。王小波笔下的性爱与S/M场景,是福柯所言的微观权力场,是一种“有效权力实践”。王小波“所拒绝和颠覆的,并非某种具体的权力、意识形态或话语体系,而是权力机器与‘历史’自身”。她的这种论断无疑具有去历史化色彩。近年来,又有陈晓明、黄平等的评论文章与之遥相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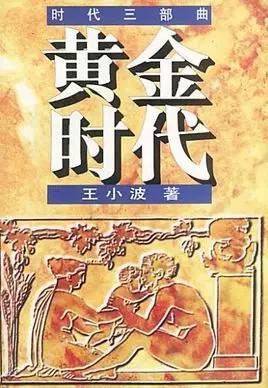
2011年,陈晓明也曾对王小波的《我的阴阳两界》进行剖析,他从中嗅出“戏谑与批判”、“逃亡与自由”、“爱欲与死亡”的味道:“正是自由、荒诞、虚无,这奇怪的‘三人转’,才有王小波小说的奇妙之处。”无独有偶,黄平在《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中作出王小波是一位“‘脱历史’的局外人”的断言。黄平将王小波的“文革”写作与村上春树的“二战”写作并置,指出他们的后现代式创作都是为治愈人类精神创伤,缓解“历史负重的焦虑”。除此之外,从性爱文学、权力与爱欲等后现代视角解读王小波,似乎成为王小波去世之后,一种越来越主流的方式,甚至港台地区与海外的王小波研究,也大多从此入手。
这种“后现代化”王小波倾向,还表现在20年间,媒体宣传王小波时侧重点的转变。王小波刚刚去世的那几年,舆论宣传的重点主要在,“对抗文坛的王小波”、“自由主义王小波”、“启蒙者王小波”、“公共知识分子王小波”等方向上。但近几年,宣传方式却越来越中产化、娱乐化与消费化。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猝死于北京顺义,海内外媒体展开一系列追踪报道,各种悼念文章蜂拥而至。网络赛博空间更是推波助澜,以“西祠胡同·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为代表的网民纷纷将王小波视作“标杆”。王小波被奉为“我们的精神父兄”和“人生导师”,成为“接头暗号”。近几年,王小波更摇身一变成为新一代“网红”,“王式幽默”是“段子手的标配”,网上诸多经典语录使他成为“金句小王子”;《爱你就像爱生命》中他为李银河所写的热情诚挚的情话更让他化身为“撩妹高手”,“写情书的王小波”大量“吸粉”,“王小波式的恋爱”令人欣羡不已。诚如陈晓明所言,全球化、商业化、资本化时代,“当代文学正在努力成为消费社会的一部分”,文学受到消费文化宰制,王小波的边缘身份被转化成“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他以各种方式被纪念、崇拜、模仿着,变为符号化、标签化的存在。他是“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但就不是他自己。
“现代性”维度
但是如果单把王小波纳入“解构”阵营则是片面的。我们不能忽视其创作是从“革命时代”转向“后革命时代”的产物。

王小波是革命思维的叛逆者。“后革命氛围”中,他看到“革命时代”专制思想的延续,并与其抗争到底。他反对无智、无性、无趣的人生,虽抨击权力机制但并不解构所有价值。在对自由、民主、平等、宽容、多元的不懈追求中蕴藏着现代性的启蒙精神。这一切绝非“后现代”所能涵盖。王小波离开体制从事文学创作是自主选择的结果。他们只看到王小波戏谑、狂欢的解构姿态,却不见其对前现代的批判和启蒙思想锋芒。
另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城市中产阶级群体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是这一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与审美趣味。鉴于文化身份、职业经历和受教育程度等,过于通俗或专业的读物都不符合他们的期待,介于高雅与世俗之间的王小波便一跃成为媒体首选。王小波承担着都市白领智、性、趣“启蒙者”角色。他对“知识性、趣味性、特立独行”的强调与“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相契合,对王小波的消费是中产阶级“媚雅”的表征。由此可见,时下“王小波热”的延续与中产趣味的形成关系密切。阅读王小波可以彰显其非凡、不俗的文学品味。王小波是一个性格内敛的人,他像“猪兄”一样竭力反抗“被设置”命运。他没有让自己的“想法和作品成为甚嚣尘上的正宗”,但却在市场时代被推上“神坛”,成为后革命时代“被‘劫持’的偶像”,成为失去意义的空洞能指和象征符号。这种“书写文化英雄”症候,对信仰自由与多元的王小波来说简直是莫大嘲讽。

在20年间,文坛对王小波的接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能以“冷漠与拒绝”进行简单定义。从文学史编写来看,纪念王小波去世二十周年,界面文化的文章谴责说:“即使是在现在大学中文系通用的教材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2007年第2版)和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版)都对于王小波只字未提。”这个说法太武断了。洪子诚和陈思和都对王小波做出过较高评价。如《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版),洪子诚说:“对‘当代’历史,包括‘反右’、‘文革’等事件的反思性主题,在90年代的其他作品中也有继续,如李锐的《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修订版),洪子诚在第二十七章《90年代的小说》谈到“小说创作与文化事件”时,用了一页多篇幅论述王小波及王小波之死,并声称“他的创造借鉴的文化资源,更多不是来自20世纪中国作家影响巨大的感伤、煽情的一脉,而是有着飞扬想象,游戏精神和充沛幽默感的作家。”陈思和也认为,“诸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都堪称当代文坛最美的收获。”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2012年版),同样用半页篇幅来介绍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与杂文随笔。有的文学史还有专章论述,如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009年版)。
这些情况表明,当代文坛对王小波的接受有了新动向,但当代文学评价体系和经典化的建构受到文化权力制约。关于王小波的研究,“坚硬的冰”或“炽热的火”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渴望有一股和煦的风吹来,吹散笼罩在王小波头上的阴霾与光环。唯有在宽容、多元、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才能窥见王小波的真身。同时,相关研究不应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牵强附会。关于王小波早期作品、未竟稿和剧本创作仍有可供探讨的空间。王小波的作品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和研究价值。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3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欢迎转载原创文章。如转载,请在文章前注明:本文首发于社会科学报。
做优质的思想产品
社会科学报
微信号:shehuikexuebao
社会科学报官网:http://www.shekeba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