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播剧《白鹿原》中,白嘉轩的族长角色令人印象深刻,上至祭天问神,下至领里纠纷,无不由这位宗族的领导者来裁定,而族长主持大小事务、行使族权的场所便是祠堂。
与传统宗法制的产物祠堂不同,古希腊的广场(Agora)是公民抒发政见、参与辩论之地,是更加开放、更具公共性的议事空间。
本期微信中我们将看到,在广场这一舞台上,政治家是如何以雄辩与极富煽动性的修辞来影响民众的决策与判断的。
可以想象,自带卡里斯玛光环的白嘉轩如果穿越至古希腊,也应是一位极具感召力的演说家。
内容选自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所著《“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


祠堂,传统宗法制度下同族人共同祭祀祖先的房屋


古希腊广场(Agora)体现了其公民政治属性,兼有市场、知识传播等功能,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复合中心
演说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表演行为,是演说者与其听众在特定场合中进行互动的过程,演说者在演说现场说服听众,力图使听众接受他所传达的信息以及所坚持的观点,同时向听众展示其演说的才能。这是对演说表演属性的简要概括。
古希腊语中,logos是最常用以指称“演说”的名词,其动词形式为legein,legein的阳性分词legōn也常用于指称“演说者”。由于雅典民主政体的三个主要机构——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公民法庭——都是依靠演说来运作的,无论是提议、控诉还是申辩,均以当事人现场演说和听众或陪审员的现场判断为其基本程序,正如德谟斯提尼所说,雅典政体是建立在演说之中的(en logois hē politeia);因此,当演说运用于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活动中,演说行为便具有了特定的政治功能与政治属性。
于是,“演说”(logos)即成为“政治演说”(politikos logos),其更准确的意思是“与城邦事务相关的演说”。《亚历山大修辞学》将“政治演说”具体分为“公民大会演说”(dēmēgorikos logos)、“诉讼演说”(dikanikon logos)与“展示性演说”(epideiktikon logos)三种类型。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也使用了相同的分类法,只是没有明确指出三者均属于“政治演说”(politikos logos)。他进一步解释说,展示性演说的听众是在观看演说者的说服“能力”(peri tēs dunameōs ho theōros)。这说明,在以上三类演说中,展示性演说最直接的以表演为目的,它可能包括一些与城邦公共事务相关的仪式性演说,如雅典著名的葬礼演说,故而,在此意义上展示性演说也可作为“政治演说”之一种。但是,笔者所讨论的政治演说则主要集中在与雅典民主制运作最直接相关的公民大会演说和诉讼演说。


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
亚里士多德从演说术内部阐发了他对政治演说之表演属性的认识。他在《修辞学》中开篇即对当时所流行的演说技艺提出批评,他指出,“现在那些编写演说技艺的人”(nun … hoi tas tekhnas tōn logōn suntithentes)所传授的内容都是教给演说者如何进行恶语攻击(diabolē),如何引发听众的怜悯(eleos)、愤怒(orgē)以及诸如此类的情感(pathē)。亚里士多德将这些演说技艺统称为“事实之外”(tōn eksō tou pragmatos)的内容,因为它们与演说所涉及的事实本身(pragma)无关,而只是对听众施加影响,使之处于某种特定的心理状态。亚里士多德在此特别针对诉讼演说提出要求,他认为,不就事实本身进行演说,其危险在于演说者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歪曲法律。他甚至提出,法律应该限制那些运用情感手段的演说,禁止演说者将听众引向愤怒(orgē)、嫉妒(phthonos)和怜悯(eleos)等情感。亚里士多德进而以这种对情感手段的批评为标准评价公民大会演说,在他看来,由于比诉讼演说较少需要情感手段这类“事实之外”的内容,公民大会演说因而“更高尚”且“更适合于城邦政治事务”(kallionos kai politikoteras)。可见,亚里士多德是从城邦法律、政治与道德的层面对演说技艺中的情感手段加以批评的。
然而,尽管有此批评,亚里士多德同时却也承认情感手段对于演说本身的必要性。他在《修辞学》第二卷中指出,既然演说术的目的在于“裁判”,那么演说者就应该在听众面前表现出(phainesthai)某种形象,并且使听众处于某种状态(diakeimenoi)。亚里士多德还说明,演说者道德形象的表现对于公民大会演说更有积极效果,而影响听众的心理状态则更为适用于诉讼演说。他继而进一步解释说,演说者面对不同的听众会受到不同的“裁判”,朋友和敌人、愤怒的人与情绪平和的人对待演说者的态度是存在差异的。显然,亚里士多德对情感手段必要性的认识,是以演说者与听众的关系为出发点的。他明确意识到,诉讼演说之所以更加需要这种影响听众心理状态的情感手段,是因为诉讼涉及的是当事人彼此之间的事务,与作为听众的陪审员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而公民大会演说所讨论的事务则“更具公共性”(koinoteron),听众便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peri oikeiōn)做出“裁判”(krinei)。我们从中看到,情感手段的作用在于实现演说者与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它因此成为演说表演功能最基本的实现方式,从而也是演说表演属性最常见的表现形式。

德谟斯提尼,古雅典雄辩家、民主派政治家
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一方面以第二卷整卷的篇幅对情感手段详加阐述,另一方面却于开篇即对之提出严厉批评。这种矛盾的态度具体而集中反映了他对政治演说之表演属性的认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亚里士多德在对情感手段进行批评时将它称为“事实之外”的内容,明显是将情感手段与“事实”(deiksai to pragma)对立起来。他强调,诉辩双方在演说中要做的只有“阐明事实是否存在、是否发生”(deiksai to pragma hoti estin ē ouk estin ē genonen ē ou genonen),而“事实”的严重程度及性质——“大”或“小”,以及“正义”与否(mega ē mikron, ē dikaion ē adikon)——则应该由陪审员自己去了解(gignōskein),并非由演说者告知(manthanein)。可见,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作为听众的陪审员只有通过演说获得有关“事实”本身的准确信息,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对“事实”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做出判断。因此,亚里士多德将诉讼演说的功能局限于“阐明事实”(deiksai to pragma)以向陪审员提供准确的信息,并将情感手段视为对此功能的损害而予以排斥。上文已经说明,情感手段是演说表演属性的基本体现,所以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尤其关注政治演说之表演属性对听众的认知所造成的影响,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影响主要是负面的。
通过以上这些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德谟斯提尼在演说实践中对“阐明事实”的关注与亚里士多德在理论上的强调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亚里士多德着意突出了“阐明事实”与情感手段之间的矛盾;而德谟斯提尼在现实运用中却试图兼顾二者,因为他作为实际进行演说的诉讼当事人必须使演说同时发挥其表演功能和政治功能,既要利用情感手段实现他与陪审员的有效沟通,又要表明自己的演说具有符合城邦法律与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可以说,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在理论上对“阐明事实”与情感手段之矛盾的强化,还是德谟斯提尼在演说实践中对二者的兼顾与调和,它们都反映出,雅典政治演说事实上处于由其自身的表演属性与政治属性所造成的张力之中。这种张力在涉及城邦公共事务的重要政治演说场合则表现得尤为强烈,它不再只是“阐明事实”与情感手段的关系问题,而是进一步演化为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以及对政治家“欺骗”民众的批评。

古风时期拉托的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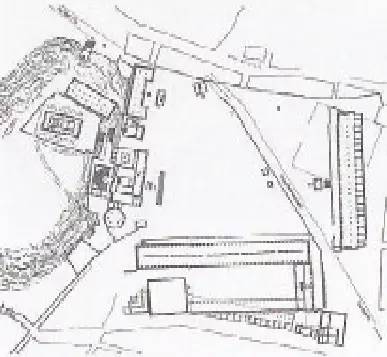
希腊化时期雅典广场
前文曾经论及,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大会演说“更高尚”且“更适合于城邦政治事务”(kallionos kai politikoteras),因为它关乎“更具公共性”(koinoteron)的事务。这说明雅典人对公民大会演说的政治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之赋予更重要的政治属性,于是更加凸显了演说的表演属性与政治属性之间的张力。这一点尤其可以从修昔底德笔下的克里昂(Cleon)曾经对雅典公民大会演说的批评中清晰地反映出来。在修昔底德记载的著名的密提林辩论中,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政治家克里昂指责公民大会成员好像是“智术师们的听众”(sophistōn theatais),而不再是“商议城邦事务的人”(peri poleōs bouleuomenois)。克里昂将公民大会中进行提议演说的政治家称为“智术师”,我们知道,“智术师”在当时主要是以其演说技艺著称的,他们是掌握和运用演说技艺的大师,他们所进行的演说因而成为表演属性的集中体现。同时,克里昂将公民大会成员称为theatais(观众),这一般是对戏剧表演场合中的观众的称呼,克里昂用它来强调,公民大会演说竟然堕落为一种纯粹的演说技艺的表演;而且在他看来,这种表演功能已经完全取代了公民大会演说应有的政治功能,即“商议城邦事务”(peri poleōs bouleuesthai)的功能。克里昂还指出,公民大会成员对政治家演说技艺的过分注重,以及他们对公民大会演说政治功能的忽视,使得他们成为容易“被欺骗”(apatasthai)的对象。此外,克里昂既然将公民大会中的政治家称为“智术师”,他也就必然了解“智术师”演说技艺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如柏拉图在《会饮》中所做的比喻:他以谐音方式将高尔吉亚的说服力量比作能够让人变成石头的“戈尔贡之首”。可以说,克里昂在这里也明确意识到演说的表演属性对听众认知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同样这种影响被他认为是负面的,而且非常严重:不仅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在诉讼演说中影响陪审员对案件性质的理解,更是在公共事务方面对民众进行“欺骗”,甚至使民众完全丧失自主的认知能力,从而导致民众无法正常从事政治商议。
我们从克里昂的这一批评中看到,他对公民大会演说政治功能的要求主要是“商议城邦事务”,而演说技艺所代表的表演属性则被认为是与这种政治功能相对立的,甚至是对它的妨害。这就像诉讼演说中“阐明事实”与情感手段的矛盾关系一样,反映出一种针对政治演说自身所具有的双重属性的批评,即肯定其政治属性,否定和排斥其表演属性。但是,表演属性实际上是演说作为一种公共表演行为所固有的,雅典民主政治依靠演说进行运作,难以避免这种表演属性。当雅典民众作为听众出席公民法庭或公民大会时,他们便成为演说现场的说服对象。在听取演说的过程中,现场听众这一身份相对于他们作为陪审员或公民大会成员的政治身份更占据主导地位,这也造成演说技艺得以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当政治家和哲学家对演说的表演属性加以批评时,他们要求演说者不能把政治演说场合的听众仅当作现场的被说服者,或者不能把政治演说仅视为发挥说服能力的表演行为;相反,应该重视演说听众的政治身份,以实现演说的政治功能为首要目的。这种批评分离了演说的表演属性与政治属性,并且强化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张力。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问,像德谟斯提尼这样主要凭借演说来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家,在政治演说的实践中是如何面对这一张力的?而且,这一张力对政治家演说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
李尚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北大博雅好书
博识雅行 学知天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
微信号:boya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