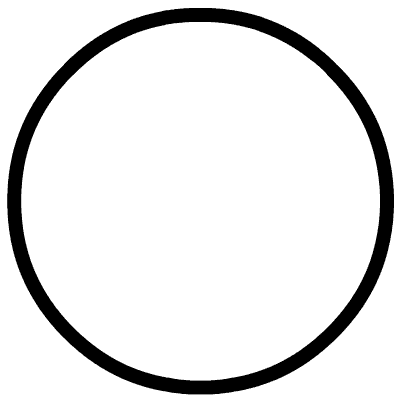
2015年春天某个周六,我陪一位老师,沿着圣日耳曼大道走,走到但丁路,转弯,看见巴黎圣母院的侧影,那些被建筑学家反复念叨的、瘦骨嶙嶙的飞扶垛时,那位老师激动起来:“啊!圣母院!”
走到双桥边时,左转,走出十来步,我指着布舍列街37号,一间逼仄小巧的店。没说话呢,那位老师先嚷了:“莎士比亚书店!”因为是周六,书店里有一大群讲英语来朝圣的人,那位老师排开众人,到柜台问:“这里有《流动的圣节》卖吗?”“有,在中间。”

书店挺窄,正中靠左廊一排按例搁经典书。《艾玛》《包法利夫人》《堂吉诃德》《老人与海》之类,中间夹着两本《流动的圣节》。其中一个版本,封面是海明威当年在莎士比亚书店门口拍的照片。
我跟那位先生在旁边的咖啡馆坐下来,我跟他说,刚才沿但丁路走过来,路边就是索邦大学,考虑到这里离圣米谢勒不远,所以,当年……不等我说完,那位老师大声说:“当年海明威就是在这里遇到的马尔克斯?”类似的细节,外人可能听着觉得云里雾里,对写字的人而言,却像是彼此认亲的密码。

大概十年前,我在上海,与一些写东西的朋友,通宵夤夜,谈论品钦、马拉默德、卡尔维诺、索尔·贝娄、克洛德·西蒙、海明威、马尔克斯;争论译本、译者、结构、语言。某个朋友在QQ群里留下一句“陕西南路某某书店,某社的马尔克斯集子,只有一本了”,会引得几个相熟的朋友去抢。大家各自写练习文本,在苍老的旧版书找到一些珍贵的冷门文本,然后手打上网,给朋友们分享。那时大家各自野心勃勃,不忘随时吹嘘:“我近来这个构思,不得了!”
后来呢?那些朋友有的做了编辑,有的去写了歌词,有的做了广告文案。不,这并不是一个“当时我们年轻有梦想,后来就背弃了”的故事。

2016年春节前夕,一个朋友跟我联系上了,给我看他最新写的几则并不拿来出版的短文。我看了看:“这段是向赫拉巴尔致敬的吧?”他拍手大笑,乐得跟小孩子似的。说到这位老师,他在国内做出版,都是挺地道的畅销书。但私下里,他说:“我现在等车的时候,就写小说。工作归工作,私下里,自己想写的是什么,自己知道,抓紧碎时间写,自己也高兴。”
所以许多文艺青年们老了,转行了,不像少年热血时似的,将一些宏大的名字挂在嘴上吹嘘,但真心热爱的,无时或忘,只是,并不拿出来抖搂了而已。
我在巴黎有位长辈,做生意的。我初次到她家吃饭,看到她家的书架,着实吓了一跳。“这都是您读的书?”“我先生的。”“啊?先生是写东西的吗?”“哪有啊,跟我一样做贸易的!”我简直不太相信,因为那书架上虽然书不多且旧,但品位非凡,主题划一,是内行读书的脉络。于是我问那位长辈:“叔叔以前应该是文艺青年吧?”“我倒不觉得他怎么文艺啊!”

过了段时间,再跟那位长辈聚餐。她说自己后来也问了先生,先生出国前是拍过电影的。只是那些他自己并不想提。我回去查了下。那位先生1983年给吴子牛导演当过摄影师,拍过一部很先锋的电影,其中有跟《四百下》与《姿三四郎》致敬的段落。
一个30年前的先锋范儿电影摄影师,在巴黎大隐隐于市,连自己太太都没太注意到。但书架里放的那些书,到底将他暗藏的英华,流露出来了。
格言杂志社(geyanzaz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