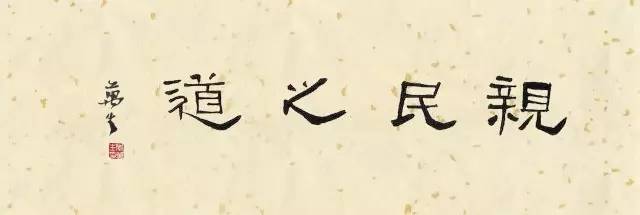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字少禹,男,江苏六合人,哲学博士,江苏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与政治哲学。

摘要
阳明南赣乡治实是一场顽民归化运动,其综合运用儒家征伐、政刑、礼乐三大治道,卓见成效。然检讨此次运动,则阳明全无政权、政道之自觉,惟有治权、治道之安排。在其主要着力的治道层面,于征伐一途,则在战区伪诈杀降、屠戮过多,在后方行十家牌法、保长法又混战时法与和平法,使之久成恶法;于政刑一途,则强推官办之“南赣乡约”,空前挤压乡村自治空间;于礼乐一途,兴社学实为明伦之正道,然依赖个人官威,不能解决人亡政息之虞。其在政权上则自甘为皇权的执行者。在政道上只知官府一途。在治权上又仅止于精英政治,全无民众的自治。
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阳明擢升都察院佥都御使,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开展了一场顽民归化运动。在此过程中,阳明综合运用了儒家征伐、政刑、礼乐三大治道,以军事征伐扫荡顽民,以乡约调控束顽民为新民,以社学教化迁新民为良民,最终取得南赣乡治的空前成功。然愚以为,若超越此“事功”的光环,转而检讨其不足,可能对厘清阳明南赣乡治的本来面目乃至对儒家政治思想的健康发展更具意义,故献曝如下,以就大方。
一、
“顽民”问题的由来
阳明《集》、《谱》中所谓南赣汀漳之盗贼,即“顽民”,实际上是由畲(輋)、汉两大族群组成,其形成过程可分述如下:
其一,北迁畲民侵陵汉民。阳明在《横水桶冈捷音疏》中云:“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各自称盘皇子孙,收有流传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1] 342盘皇即盘瓠,此盘瓠信仰源自于汉时武陵夷[2],故暴动者为畲人无疑。对此结论,学界已多有讨论。南宋后,畲民抗元失败遂北迁,其中一支进入南赣山区。然赣南素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也是客家人数最多居住最集中的地区[3]。如此一来,畲民北迁,客家南下,两大族群的活动范围发生重叠,矛盾即不可避免地产生,以至前者动辄“占据居民田土数千万顷,杀掳人民尤难数计,攻围城池,敌杀官兵,焚烧屋庐,奸污妻女,甚为荼毒,有不忍言”[1]313,而且愈演愈烈,造成“处处山田尽入畲,可怜黎庶半无家”[1] 747之局。
其二,少量汉民入山为盗。由于南赣地区山大地细,生存艰辛,若逢官府厚敛、天灾加剧等,即有汉民入山为盗。此如阳明云:“(尔等)乃必欲为此(为盗),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1] 561另外畲民的不赋不役也诱使汉民归隐畲中,如明代江西“吉安府龙泉、万安、泰和三县并南安府所属大庾等三县居民无籍者,往往携带妻女,入輋为盗”。
上述二股势力相合为害,至阳明时,终于酿成以南赣、粤北、闽西三处为中心的暴动。以至“南中盗贼蜂起。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浰头,皆称王。与大庾陈曰能、乐昌高快马、郴州龚福全等攻剽府县。而福建大帽山贼詹师富等又起。前巡抚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乐昌贼掠大庾,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吴玭战死”[4]5160。
以上为阳明入赣的背景。则阳明巡抚南赣,其核心问题即是如何迅速妥当地处置顽民。儒家于夷狄,本无歧视。如孔子认为凡人都服从于同一的道德标准,故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甚至“欲居九夷”(《论语·子罕》)。并反对以大国以暴力毁灭小的文化共同体,要求“兴灭国,继绝世”(《论语·尧曰》)。又如所谓夷夏之辨,韩愈即解释云:“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5]146阳明前番谪龙场,其地“万山丛薄,苗、僚杂居”,阳明“因俗化导,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4] 5160-5162阳明此次面对顽民,既不愿野蛮地屠杀镇压,也不能一味地迁就求和,故决定展开一场归化运动,综合运用儒家几乎全部治道,以军事征伐扫荡顽民,以乡约调控约顽为新,以社学教化迁新为良。正是由于此次运动的特殊性——如板荡的时代背景,不同族群的、素质低下的民众等,宣告以前所有儒家乡治理论——如“范氏义庄”之同一宗族、“吕氏乡约”之素质粹美、“朱子社仓”之和平从容之失效。然而这种特殊性却正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检讨阳明乃至整个儒家政治思想普遍性的机会。下面先集中检讨阳明治道的三个环节,然后再讨论其政权、政道以及治权之不足。
二、
对“顽民”军事征伐之检讨
征伐是战时法。对儒家而言,若邪恶激化至限,则战争是人类自我净化的最后的不得已手段,故从未否定之。如《孟子》云:“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滕文公下》)然儒家对征伐素有原则:一是出师性质是为了兴公利除公害。此如《荀子》云:“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正论》)二是必须有合法程序。如《论语》云:“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季氏》)。三是慎战少杀,尽量减少伤亡。如《孟子》云:“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尽心下》)四是最好剿抚并用,如《尚书》载禹征苗时:“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大禹谟》)
阳明此次征伐的过程、效率及功绩,要其大者,于战前,则选民兵以汰老弱,更盐法以充粮饷,总指挥以得便宜。于战中,则奇计迭出,虚实有度,速战速取,务在殄灭。在后方,则立十家牌法剪其耳目断其联系,选保长以强化突发警情之处理。其“所将皆文吏及偏裨小校”,自正德十二年(1517)元月至次年十月,“平数十年巨寇,远近惊为神”[4]5162,是为阳明三大事功之首。下面我们来检讨此征伐中的问题。
其一,在战场上伪诈杀降、屠戮过多。阳明用计之妙,不可否认。但是用计与行诈当有界限,杀降更属不该。阳明在攻桶冈时先行招降,盗首蓝天凤已准备择日正式投降,阳明却俟蓝军松驰之际,突袭破之[4]5161,此举太过狡诈,委实不够光明磊落。如果说蓝天凤部尚在交战状态情有可愿,而破浰头池仲容部则坐先诱后杀之实。当时池氏兄弟已陆续亲至官军营中归降,阳明一使苦肉计,杖击池氏死敌以去其戒心;二使缓兵计,大办灯市以广和意;三赠节物,诱仲容入城答谢;四使攻心计,熟络感情以去其卫士。至此,池氏由“严战备”至“信且疑”再至“益自安”,可见降心已笃。阳明却在此时,伏刀斧手尽诛之,而后亲率兵士突袭山寨[4]5161-5162。此举有违诚信,战亦有道,堂堂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必如此。而阳明的伪诈,在当时也是出了名的,后来在平广西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时,二人即云“王公素多诈,恐绐(欺骗)我”[4]5166。可见此说并非愚之孤论。阳明在征伐中,又杀戮过多。如首征大帽山,“连破四十余寨,俘斩七千有奇”[4]5160。征桶冈,“破巢八十有四,俘斩六千有奇”;“破福全,其党千人突至,诸将擒斩之”[4]5161;征浰头,“斩馘(割左耳以计数)二千有奇”,“余贼奔九连山……擒斩无遗”[4]5162。故斩首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伤者更不计其数,如此杀戳岂不过哉!
其二,在后方行十家牌法和保长法,久为恶法。明代乡村一般是行里甲法,以控制人身,征收赋税,但此制存在种种弊端,故迅速朽败[6]。阳明在战后区域,于里甲基础上,新立十家牌法专司日常的严防,又立保长法专司突发状态下的自卫。此二法动静结合,防战结合,一则能充分调动民间力量,自我纠错;二则效率高,发生即发现,发现即除掉,除恶务必尽;三则形成一个网络,由户及甲,及甲及保,由保及乡,由乡及县[1]1153,故取得较好效果。但是其中的问题如下。
一是后戡乱时代的困局。十家牌法加保长法,在平定南赣后,继续沿用,但很快就表现出问题,首先是法立弊生,人亡政息。阳明自云:“大抵法立弊生,必须人存政举,若十家牌式,徒尔编置张挂;督劝考较之法,虽或暂行,终归废弛。”[4]1153其次是官员懈怠、民众受扰。阳明自云“案照本院先行十家牌谕,专为息盗安民。访得各该官员,因循怠惰,不行经心干理,虽有委官遍历城市乡村查编,亦止取具地方开报,代为造缴,其实未曾编行。”此是言行法官员皆敷衍了事。又云“且承委人员,反有假此科取纸张供给,或乘机情查流民,分外骚扰,是本院之意务要安民,而各官反以扰民也。”[1]1106-1107此是言民众极受骚扰。
二是十家牌法的性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法都会步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不是的,凡不残贼人性反而滋养之者,则行无碍。反之,只要是恶法,其违背伤害人性,则无论外在的推动力如何强大,终将败亡。十家牌法的问题并不在于其准军事化管理,而在于其在和平时期压制自由,故成恶法:一则为使民众伏于王法,以连坐来恐吓、惩罚,使民众处于一种恐怖和不安全感中;二则相互监督,鼓励告密,使个人隐私乃至正常生活时时处于“老大哥”的监督之下,使传统的家庭与乡村伦理受到破坏。
三是战时法的限度。但是此十家牌法产生时并非恶法,其本身就是战时法(阳明亦自知此点[1]530),不能用于和平时期,戡乱结束,即当作废。然而阳明以之顺手,一直保留,使之成为和平法,也为后面的专制政权所沿用。这种战时法,它是以暂时牺牲民众的自由与自主为代价,以军事化管理与控制为手段,以获得秩序与效率。但是所有的秩序与效率是为了人性的滋养和社群的成长与完成,而非相反。平民不是军人,和平时期的社会管理也迥异于战争时期。如果错误地迷恋于此牺牲自由自主而得来的秩序与效率,以战时法代替和平法,则良法即成恶法。其必然对被治理者的人性造成巨大的舛害,必遭民众反对,就连执行者本身也会受对此双刃剑的伤害。
三、
对“新民”政刑巩固之检讨
相比征伐,政刑则是和平法。本来儒家对政刑即很重视。如《论语》云:“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尧曰》)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公孙丑上》)只是要求以礼乐为主、政刑为辅,反对独任政刑,故《礼记》亦总结云:“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记》)
阳明为巩固军事成果,特别创建推行了“南赣乡约”。此乡约可以说是特别为新民——即归化的顽民所量身订做的。如阳明自云:“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1] 599-560对于这些新民,阳明诲诲教导道:“授招新民,因尔一念之善,贷尔之罪;当痛自克责,改过自新,勤耕勤织,平买平卖,思同良民,无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灭绝;约长等各宜时时提撕晓谕,如踵前非者,呈官征治”。[1]602对于本来的良民,阳明也一再强调要放弃前嫌,和衷共济:“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诚不忍言;但今既许其自新,所占田产,已令退还,毋得再怀前仇,致扰地方,约长等常宜晓谕,令各守本分,有不听者,呈官治罪”。[1] 601故此是和平时期的制度建设,以期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基层管理控制制度。但是其问题如下。
其一,官方性。“南赣乡约”的本质已完全由“吕氏乡约”的民间自治契约变而为官方制订、平民遵守的强制性治安条例。其在乡村中选出士绅,形成组织机构,对乡村事务展开日常管理,以弥补公权力在基层社会的久缺。且其是以十家牌法为基础的,如言“不得坐视推托,陷人于恶,罪坐约长约正诸人”[1] 601。上文已言,十家牌法已成恶法,现在则又在此恶法上再套一副“乡约”之枷锁。
其二,强制性。“南赣乡约”的推行完全是强制性的,其空前挤压乡民的自由空间。如“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日逐出入所为,知约司之”[1]600。此与十家牌法无异,严密控制人身自由,徒增约司权力,平添民众烦扰。又如“同约之人每一会,人出银三分,送知约,具饮食,毋大奢,取免饥渴而已”[1]600。此必须出钱与聚餐,实为穷人额外的负担。又如“会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许先期遣人告知约;无故不赴者,以过恶书,仍罚银一两公用”[1]600。如此聚会即完全不是民众的自主自愿,而是官府胁迫下的强制性例会。又如“通约之人,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视推托,陷人于恶,罪坐约长约正诸人”[1]601。如此同约民众的有所作为,乃是以连坐为前提的,而非一颗仁心的发用,此是最无道者。
其三,软弱性。“南赣乡约”貌似沦为官府的基层派出机构,实则不然。如其规定“寄庄人户,多于纳粮当差之时躲回原籍,往往负累同甲;今后约长等劝令及期完纳应承,如蹈前弊,告官惩治,削去寄庄”[1]601;又如“亲族乡邻,往往有因小忿投贼复仇,残害良善,酿成大患;今后一应门殴不平之事,鸣之约长等公论是非;或约长闻之,即与晓谕解释;敢有仍前妄为者,率诸同约呈官诛殄”[1]601。此是要约长主动解决逃税问题,解决争讼、斗殴等基层矛盾,为官府分扰。然而约长并不具备公权力身份,没有法定的约束力,所以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官府。故而乡约本身在行动力上是极其软弱的。
其四,短命性。“南赣乡约”云:“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人等若揽差下乡,索求赍发者,约长率同呈官追究。”[1]601我们知道,这些基层职务或因袭前朝,或由太祖亲自制订,然不过百五十年,这些“官员”已成乡村之蠹。现在阳明又重新设计一批基层“官员”,以之来纠前一批之非。此不能不让人叹息。因为前一批“官员”失效的原因依然存在,则新的“官员”将很快沦为他们。因为这种自上向下产生的权力没有监督、制约、惩治与罢免等,注定其是短命的。太祖解决不了的问题,阳明也解决不了。则后来者,或因循太祖旧制,或辟阳明再立新规,然皆逃不了此恶性循环。
四、
对“良民”礼乐教化之检讨
如果说征伐是战时法,政刑是和平法,则礼乐即是理想法、永恒法。儒家素来视礼乐教化为建成善政最根本之手段。早在《尚书》即载:“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舜典》)《论语》中孔子亦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阳明道:“君子之政,不必专于法,要在宜于人;君子之教,不必泥于古,要在入于善。”[1] 897故其南赣乡治特重对基层之教化,其有社学与书院两项。针对精英分子,则兴讲学、办书院。阳明在繁忙军务之中,犹讲学不缀,如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刻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八月门人薛侃刻《传习录》,九月修濂溪书院,四方学者云集。针对普通子弟,阳明则大办社学。社学始于元代[8],明亦承袭,于洪武八年(1375)诏天下兴办[9]38。其性质是由中央政府倡起的、地方政府予以监督的、经济上以由乡民负担、管理上由胥吏执行的以社为依托的具有强制性的蒙学[10]。但由于经费不继,师资不力,管理扰民等原因,至洪武十三年(1380)革去,十六年(1383)复设,变成民间自办[9]47。阳明清晰地认识到兴办社学可以“使人知礼让,户习《诗》、《书》,丕变偷薄之风,以成淳厚之俗。”[1]1165故在没有力量完全官办的前提下,即不顾朝廷规定不许有司干涉的命令,采取了官督民办的模式。首先,亲自规定教学的原则与内容。如《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云:“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1] 87又制订了《教约》[1] 88-89,规定了每天师生之间的学习内容与程序。其次,要求基层官员严加督办,要择优质师资并保障薪酬 [1]604,要加大对师资的管理监督 [1] 610-611,要加强宣传对就学的蒙童家,务使尊师好学 [1]604。在阳明南赣乡治三法中,兴办社学可以说是釜底抽薪者。就对象而言,它包括所有适龄子弟,没有歧视。就性质而言,它不是奴化教育,而是明人伦、正道德,皆是农耕文明的礼法之正。就结果而言,庶几可至“有耻且格”。故可以说,此是南赣顽民归化的收官之作。
但是,阳明社学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阳明社学是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的机构,诸如师资的延请、经费的保障、学舍的建立、学生的动员等,完全建立在阳明个人的权威基础上,阳明在位,凭其权威,可令下属严格执行,如在《行雩都县建立社学牌》中要求县府“即于该县起立社学……毋得违延忽视,及虚文搪塞取咎”[1]1165。但这种办学模式具有先天的不可持续性,一旦权威消失,即无法延续。因为一则名不正,其非国家明令必办者;二则大规模的基层办学经费没有保障,其既非国家投入(如官学),亦非商业运行(如私塾),亦非慈善捐赠(如义学),完全靠下属官员自筹,师资等亦如此。故若官员意志强、能力佳,亦难为继,遑论庸官弱吏,至于阳奉阳违、敷衍了事者更不必说了。明代的社学发展也正如此,权威在则社学在,反之亦然。
然则针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教化模式何在?作为阳明后学的由王心斋所创立的泰州学派则走出了另一条舍弃官办,由儒士自由讲学、化行乡里的新道路。其义理以“百姓日用为道”[11]10,明确奉守“苟得移风易俗,化及一邑一乡,虽成功不多,却原是圣贤经世家法”[11]186之理念。师弟亦纯任平民,如心斋本为盐户,弟子有樵夫朱恕、吏胥李珠、窑匠韩贞、商人林讷、农夫夏云峰、布衣颜钧等[12]719-721。教化对象亦为平民,如心斋弟子韩贞“以化俗自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讲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12] 720相比而言,在国家力量不足以实行普遍的基础教育的历史条件下,此法可能更具有可行性,特别对于儒家来说。
五、
治道之外的反思——阳明良知的限度
所谓政治,至少包括四大要素。一是政权,即公共权力之所有。二是政道,即政权的表现形式。三是治权,即公共权力执行权之所有。四是治道,即治权的表现形式。阳明本有伟岸之人间理想,其在《与顾东桥书》中描写了人人良知具明,各据才质而安于职分,以成一和谐人间[1] 54-55。此理想社会中,上述政治四大要素均收涵于良知,此时良知真能生天生地,神鬼不测,圆善无碍。然而,那毕竟是终了义,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这四者又绝不可不论。然综观阳明南赣乡治,其完全没有政权与政道的自觉,惟有治权与治道的安排。治道之检讨前文已述,下面略析余下三者。
其一,阳明对政权即公权力本身的性质完全没有反思力。如将官民关系比喻成父母与赤子,其云:“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1]561又如将官民关系理解为管理与纳粮输赋的主奴关系,如云:“世岂有不纳粮,不当差,与官府相对背抗,而可以长久无事终免于诛戮者乎?……就使尔等各有子弟奴仆,与尔抗拒背逆若此,尔等当何以处之?”[1] 613-614此去《礼记》“天下为公”,《孟子》“民为贵”远矣,又完全是韩愈《原君》“尊君”之老调[5]146,以皇权的执行者自居。
其二,阳明对政道的理解也有相当倒退。阳明只知官府一途,连宋儒开创的乡约传统也强以矫改。如“南赣乡约”的纲骨其实就是参照《管子》、《商君书》以及王安石的“保甲法”而创立的。可以说,阳明在乡治问题上,由儒入法,与之沆瀣一气。法家遵行弱肉强食、以弱奉强的丛林法则,从来都要求皇权深入民间,直接控制每个人,以为自己服务。儒家则素来警惕公权力深入基层社会,而欲在现行君权之外别有一种理想模式——即基层社会的自主、自治。可以说,在基层乡治中,儒法的分界就是自主、自治与否。儒家在唐宋后皇权不下县的“政治双轨制”下,于乡治屡有建树。如“吕氏乡约”舍弃国家公权模式,建立乡人自治之契约。又如明初方孝孺亦发明《周官》、折衷宋儒,设计出“乡族法”此一地方自治制度。上述二者在设计、运作、监督、嘉惩等方面,其主体均为民众自身,完全抛弃了运行数千年的“君主臣治”的公权体制,创造了政治实体运作的又一种可能。故与先贤比,阳明是个退步。就是与同时代的人比,也如此。如正德年间,山西潞州南雄山仇氏家族组织了乡约组织,其以蓝田“吕氏乡约”为蓝本,又以仇氏家范配合而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致“为当代之所崇尚,秉笔之士亦笑谈而乐道之。”[13]
其三,阳明对治权的理解,只止于精英政治。此与孟子所说的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不同,阳明认为治理权永远掌在官府以及官府委任的贤良手中,群众毫无自治之可能。如阳明充分认识十家牌法的实行对基层社会是一个全新的扰动,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官员与士绅作用方可 [1]1153,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一个良法益于民众,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则无官亦自行,如果相反,对人民与执法者的生活造成妨碍,则强硬的暴力机构不能压迫,不论什么圣贤也不能劝从。阳明其实从来没有认识到,也不会认可民众的自主自治。
所以,阳明动辄言良知如何,但是其发用,落实在政治生活中,这个良知的主体就特指精英的良知,良知的内容对民众而言就表现为服从皇权。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则这种良知绝不是人的自由与解放——即仁的状态,而是奴役与枯萎——即不仁的状态,则前述《与顾东桥书》那种理想社会又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参考文献:
[1]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南朝宋]范晔. 南蛮传[A].后汉书[C].北京:中华书局,1965:2825-2826.
[3]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13-73.
[4] [清]张廷玉.王守仁传[A].明史[C].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唐]韩愈.韩愈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0.
[6] 施由明.论明代的里甲制与农村社会控制——以江西为例[J].农业考古,2010(1).
[7] [清]顾炎武:顾炎武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988.
[8] 柯劭忞:食货志[A].新元史[C].上海:开明书店,1935:168.
[9] 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
[10] 陈时龙.论明代社学性质的渐变与明清小学学制的继承[A].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3)——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论文集[C].2009:445.
[11] [明]王艮.王心斋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12] [明]黄宗羲,明儒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 曹国庆.明代乡约研究[J].文史,1998,46:201-202.

本文原载《贵阳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经作者授权发布
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