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左:笛安父亲李锐 中:史铁生 右:笛安
我已经想不起来具体拍摄这张照片的年份,我认为是1995年或者1996年。我惊讶地想,我的爸爸在这张照片上怎么那么年轻。而我——头发剪这么短的时候,应该已经读初中了。满脸都是跟所有人闹别扭的青春期表情。中间那个人,就是铁生叔叔,因为我们三人都是坐着的,所以看不出他坐了轮椅。
那个时候,《我与地坛》好像还没有被选入语文读本,我也没有读过——我对于“史铁生”这个人的认知,首当其冲的并不是“一个作家”的身份,我最先记得的,永远是,他是爸爸的好朋友。
— —
我爸爸这个人,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处女座,他没什么朋友的,他把一个人认作“朋友”,那其实就等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托付。至于我们普通人都有的“普通朋友”“酒局朋友”“泛泛之交”——对我爸爸来说,都是世界观之外的存在。
爸爸是在北京长大的,和铁生叔叔一样。他们一同在20世纪 60年代的时候去乡下插队,做“知青”,在日复一日的艰苦劳作中渴望着能读点书,阅读能让他们心里有种吹吹海风的错觉。

▲ 史铁生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据我所知,爸爸开始写作的时间大约比铁生叔叔早一点。因为那场导致他坐上轮椅的疾病,铁生叔叔回来了北京,而爸爸没有。
小学时候,每个暑假,爸爸会带着我到北京,准确地说是回奶奶家,有一个项目是每年都不会漏掉的——总会在一个下午或傍晚,爸爸骑上三叔或者姑姑的自行车,把我放在横梁上,我们去看铁生叔叔。
— —
他摇着轮椅给我们开门,脸上总是笑着的。我静静地坐着,浑身紧张,我是个神经质的孩子,来的路上爸爸嘱咐过我,绝对不可以问关于铁生叔叔的腿的问题,于是我紧紧咬住牙,似乎觉得只要精神松懈了,关于“腿”的事情就会不受控制地被我说出来。
可是,铁生叔叔给我的感觉,却是一个爽朗的人,喜欢开玩笑,于是我不由得想,是不是即使不小心问到了“腿”的问题,他也不会介意的——当然,我就是想想。
他看着我,问:“我们说的话是不是很无聊呀,你好像都犯困了。”

▲ 史铁生在地坛公园
就这样,一年一会,直到第四年,我才真正读了铁生叔叔的书。第一篇,不是传说中的《我与地坛》,是一篇讲述他少年时在陕北插队的文章,叫《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我觉得,在字里行间,我听得见铁生叔叔说话的声音,平和、宽厚,说的都是贫瘠的千里赤地上一些没什么希望的人和事,但是,语调里没有苦难,只有包容。我跟爸爸分享过这种感觉,爸爸说,那当然,铁生是好作家。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年就是这样见一两次面。后来因为铁生叔叔的身体状况,连一年一次会面的频率都无法保证了。

▲ 史铁生著有《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病隙碎笔》等
后来,在我已经上大学之后,某次跟着爸爸去吃饭,忘记了是见谁了,席间有人谈起铁生叔叔的近况,指的无非是他又在做透析之类的,爸爸突然有点激动地说:“铁生那个时候的《我之舞》,写得多好啊。我看完都傻了,可是他们不懂,那些人什么都看不懂,根本不知道奇迹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发生……”
至于“那些人”指的是谁,我不问了,席间其他食客也没问。中国人是非常擅长化解尴尬的——那一瞬间,我在想,所谓的高山流水,指的应该也就是这个了。
虽然他们是同行,可是写作对他们二人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我爸爸始终把他的工作看成是人间庄严的使命,可是铁生叔叔渐渐地,把写作当成了接近神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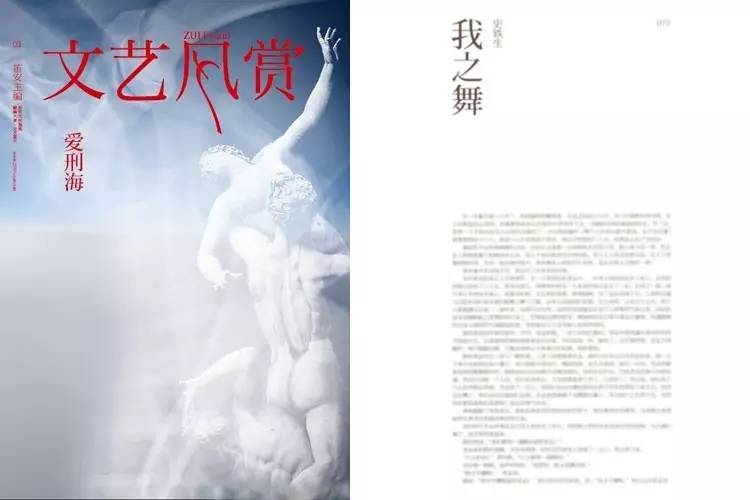
▲ 《文艺风赏》创刊号 刊登史铁生小说《我之舞》
爸爸最后一次和铁生叔叔通电话,还是跟我有关,他帮我问,我主编的杂志上可不可以刊发铁生叔叔的旧作,就是那篇我们都喜欢的《我之舞》。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当然可以用了,不用给什么稿费——小孩子真的长大了啊……”
可是,就在我们为了这本杂志创刊准备开发布会的时候,铁生叔叔走了。我躺在上海的酒店里,黎明时分,手机里涌入了无数人的信息,我觉得,此时最该跟我分享这个消息的人还是爸爸。
我说:爸爸,铁生叔叔走了。
他回复:离他六十岁生日就差了一天。这么巧就差一天。他应该挺高兴的。

▲ 80年代后期,史铁生在家中
我的合作伙伴在外面敲我的房门,她想问我该给那篇《我之舞》怎么算稿费。我心里却一直想着一个遥远的画面。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把一个庙会上买的塑料小戒指丢在了他们家。第二年的夏天,铁生叔叔从容地把它从抽屉的某个角落拿出来,问我,这是你的吧?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他替那个孩子保存着她自己早已遗忘的玩具。

我只是想知道,过去的一切都会消失吗?
那些少年发出的声音,还能听得见吗?
2017年《最小说》
选题书第三辑——
《在成为平凡的大人前》
八篇青春小说,八种少年模样,
捕捉每一个渺小却独特的声音。
六大复古文化专题,展现一个时代
青年者喧嚣而璀璨的精神世界。
“要成为被仰仗的大人物好难啊……”
“那不如,先成为闪闪发亮的少年吧!”
2017年7月30日 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