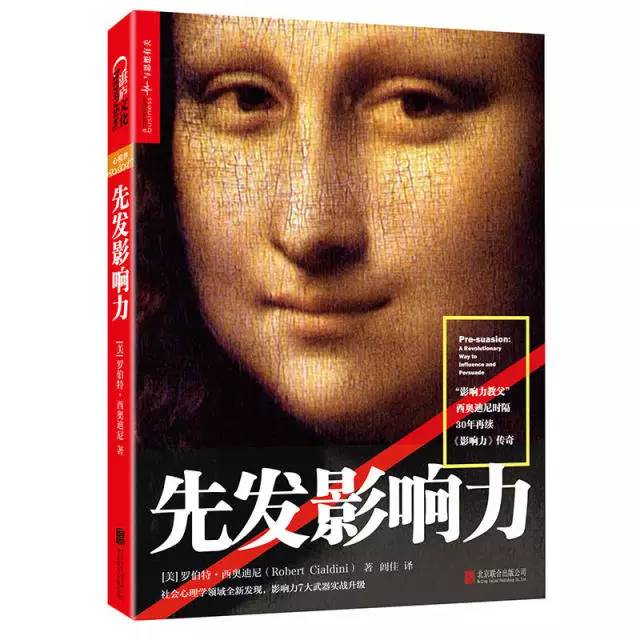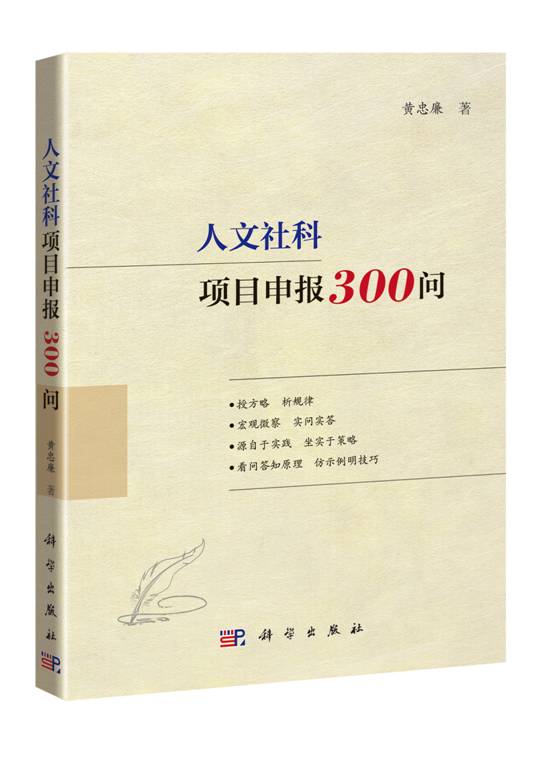
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疑难
韩潮
作者简介:韩潮,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韩潮,男,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人大复印:《外国哲学》2017 年 06 期
原发期刊:《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0172 期 第 5-17 页
关键词: 马基雅维里/ 现实主义/ 乌托邦/ 极端主义/ 政治想象/ Machiavelli/ realism/ Utopia/ extremism/political imagination/
摘要:在马基雅维里的研究领域存在着一个共识,即马基雅维里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这可能也是马基雅维里的方法论内核。但是,《君主论》最后一章的叙述、修辞和论证却无不表明,马基雅维里思想中包含着某种“不太现实”的成分。并且,按照休谟等人的看法,马基雅维里的“新方法和新秩序”,并没有触及现实的力量,只是一种对现实的邪恶想象,甚至或许只是一种“邪恶”的“乌托邦”。因此,似乎更应该将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理解为某种“极端主义”。但更进一步说,极端主义也只是理论层面的设定,在实践上马基雅维里却是要用“极端”的手法,造成一个“正常”的幻觉。

马基雅维里并没有创立一套新的政治语言,他并不是一个政治术语的发明者,我们今天所有用于描述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词汇,他本人都没有使用过。在他的词语表里,我们看不到后世那些加诸他本人的词汇——现实主义、国家理性、政治科学、共和主义、民族主义,等等。单从政治语言的角度,我们很难将《君主论》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君主宝鉴”式著述中区分出来,[1]甚至是马基雅维里所使用的论说方式如“美德与命运”的关系,其实也是再传统不过的人文主义主题。
当然,这并不表明,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并不存在实质的创新。如果我们认可马基雅维里对现代政治思想的创始意义,那么上述现象就只是说明了一种悖论、一种表述和所欲表述的悖论——马基雅维里始终是用过去的语言诉说着现代政治思想的秘密。甚至,夸张一点说,没有任何一个马基雅维里的词汇,不需要经过“翻译”就直接可以运用于当代政治话语的讨论。以赛亚·柏林在他的名篇《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中为我们揭示了现代以来各种面相、几近眼花缭乱的马基雅维里阐释,可为什么在所有思想家中,唯有马基雅维里引发了如此多的争议?其根本原因恐怕恰恰在此——马基雅维里对我们来说始终是熟悉的陌生人,他诉说了现代政治思想的秘密,使用的却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翻译”的语言。
尽管如此,却很难说马基雅维里本人对创新毫无自觉:在《君主论》的献辞中,他明确表达了对传统人文主义君主宝鉴文体修辞的不满;此外,无论在《李维史论》还是在《君主论》中,他也曾多次使用过“新方式和新秩序”(modi ed ordinin uovi)这一带有明确方法论意味的表述;①而在《李维史论》开篇首句,他更是直接表达了意图探索“新方式和新秩序”、涉足前人从未触及领域的理论意趣。
这种方法论的自觉尤其体现在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十五章中的一段著名表述中:
既然我准备写一些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直接说出事情的实际真相(verita effettuale della cosa),而不是事情的想象方面(immaginazione)。[1](P73)②
根据曼斯菲尔德的研究,马基雅维里此处的表达不仅在马基雅维里本人的著作中仅此一处,而且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也仅此一例。[3](P19)不过,今天似乎几乎所有《君主论》的会心读者都以不同的认知方式领受了马基雅维里此处关于事物的“实际真相”与“想象方面”的区分。我们会认为,通过在事物的“实际真相”与“想象方面”之间所设置的距离,马基雅维里实际上与人文主义、并且通过人文主义与作为人文主义前提的西塞罗或柏拉图式的古典政治哲学相决裂;我们也会认为,现代学术中事实和价值、实然和应然、政治和道德的分裂恐怕都或多或少发端于此处;而且,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马基雅维里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对事物的“实际真相”的兴趣,是因为他已经对古典政治哲学的空想性感到厌倦。
在所有的这些阐释、理解和“翻译”中,最为内核的应当是马基雅维里这句表述中体现出的现实主义取向,这不仅是因为马基雅维里首先使用了被鲁索(Luigi Russo)称之为“马基雅维里用他的新直觉创造出来”的effettuale一词[4](P171)——而此前的人文主义者从没有使用过这个表达——而且,还因为他使用了一个新的表述immaginazione(想象)用以形容古代君主国和共和国的政治话语,③更因为马基雅维里就此确立了一个新的、以前从没有被界定过的、在政治现实和政治想象之间的对立。
因此,如何理解这一段话,关系到的是马基雅维里学说的整个方法论意义。如果我们希望把现代世界中事实和价值、实然和应然、政治和道德的分裂归之于马基雅维里——例如曼斯菲尔德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在《君主论》第十五章中发现一种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是后来的事实和价值区分的先驱,并且,这种现实主义认为,不应当从应然中推出实然来”[3](P258)——那么,从根本上说所有这些回溯都必须借助一个“现实主义”的内核。
一、“现实主义”何以成了一个疑难?
对马基雅维里的解释一向可谓众说纷纭,但“现实主义”可能恰是所有解释的内核。维罗里曾不无感慨地说,“如果要说在马基雅维里学界还存在什么共识的话,那么,这个共识就只可能是,马基雅维里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5](P466)而G.B.Mindle在一篇同名论文中甚至干脆说,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科学的标志就是他的“现实主义”,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未免会有自说自话之嫌[6](P212)——可问题恰恰在于,什么是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共识的确可靠吗?马基雅维里的文本是否只呈现出现实主义的一面,他所说的“事情的实际真相”是否摆脱了“事情的想象方面”?在马基雅维里文本的内在逻辑里是否还存在着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想象”?
事实上,仅就马基雅维里的文本阐释而言,即便我们承认这样一种现实主义内核的存在,在文本阐释上也至少需要面临两个挑战:首先,《君主论》的“实际真相”是否可以延伸至其他文本比如探讨共和国命运的《李维史论》;其次,《君主论》的文本内部是否可以提供一种融贯的关于“实际真相”的看法,或者说一种统一、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政治立场?
对于大多数马基雅维里的研究者来说,这两个棘手的文本问题几乎是不可回避的。比如,在卓越的文艺复兴史家、20世纪马基雅维里研究的代表人物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那里,就体现得尤为突出。吉尔伯特在他关于《李维史论》的一篇论文里曾经分别把马基雅维里的两部著作《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称之为“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7](P156)有意思的是,在他另外一篇关于《君主论》最后一章的研究中,吉尔伯特还曾提到,“弥漫于《君主论》最后一章的民族主义呼吁在情感上是理想主义的,而构成此书其他章节鲜明特征的则是对于政治力量的冷酷的现实主义的分析,二者形成了一种惊人的对比”。[8](P38)
吉尔伯特的判断是一种相当具有代表性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首先应当把马基雅维里的所有文本区分为方法论上截然不同的两类文本,即《李维史论》为代表的政治理想主义和《君主论》的政治现实主义;其次,即便对《君主论》这个文本而言,也应当注意其内在逻辑可能存在的冲突,比如前二十五章的基调是政治现实主义,而《君主论》的最后一章即第二十六章的基调仍然是某种政治理想主义。
实际上,这种看法牵涉两个类型的问题:其一,如何理解《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的关系,是否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现实主义”只涉及《君主论》的文本,而《李维史论》则体现出马基雅维里的另一面,换言之即“政治理想主义”?继而,如果这个区分是成立的,那么,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这是否意味着,共和制的原则是理想主义,而君主制的原则是现实主义?“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的区分恰好对应于两种政体原则的区分?其二,如何理解《君主论》前二十五章与全书最后一章的关系?是否《君主论》最后一章热切的民族主义情感与前二十五章冷静的现实主义政治分析构成了某种矛盾?如果《君主论》中的确存在着这一矛盾,又应当如何理解这个文本内在逻辑上的矛盾?是否《君主论》中还存在着诸如此类的矛盾?
大体上,这两个问题代表了马基雅维里那里的“现实主义疑难”。前者涉及的是马基雅维里整体政治思考的自洽性问题,后者涉及的是《君主论》文本的自洽性问题。前一个自洽性问题,可以说几乎是马基雅维里研究领域近于永恒的话题。由于按照通常的意见,《君主论》似乎是一本君主专制的教科书,而《李维史论》则是共和派的教科书,因此,同时传达两种教诲的马基雅维里就几乎成了克罗齐所说的“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马基雅维里之谜”。不过,自从哈林顿、斯宾诺莎和卢梭以来,将马基雅维里解释为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的努力几乎从未断绝,随着晚近以来汉斯巴隆对文艺复兴公民人文主义的发现,以及剑桥学派在此基础之上对早期现代共和主义传统的阐发,曾经的邪恶“老尼克”(old nick)现在居然冠冕堂皇地成了共和主义和公民传统的首要代表。但是,任何要将马基雅维里解释成一个一以贯之的共和主义者的主张,都很难回避马基雅维里毕竟写作了一本共和主义难以消化的著作《君主论》。因此,为解决这个自洽性问题,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不惜将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解释为一部讽刺作品;[9]④而汉斯·巴隆(Hans Baron)则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的写作时间上大做文章,以期证明马基雅维里实际上只是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偏离共和主义的阶段,又重新回到原本的共和主义立场上去。[10](P27-53)
不过,这个自洽性问题其实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是棘手的。转换一种表述,或许就远没有像初看上去那样“永远无法解决”。严格说来,共和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从概念的内涵上来看,我们可以说,自由的政体(共和制)和不自由的政体(君主制)是二择一的关系、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是二择一的关系,却绝不能说,共和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二择一的关系。它们本身就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实际上,今天,恐怕很少有人会像吉尔伯特一样,把马基雅维里的共和主义当作一种与政治现实主义相对的政治理想主义。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关于共和国应当如何利用暴力、党争和宗教的教诲,恐怕无论如何也配不上“理想主义”这个“高贵”的名词。相反,有些学者更愿意用“共和主义式的现实主义”(Republican Realism)描述马基雅维里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相对特殊的观念形态。[1](P206)、[12]因此,马基雅维里那里的第一重“现实主义疑难”其实并不能算作太过难解的问题。
事实上,由《君主论》文本的自洽性问题带来的第二重“现实主义疑难”却比通常所见要棘手得多。如前文所述,按照吉尔伯特的观察,《君主论》前二十五章是对于政治力量的冷酷的现实主义的分析,而弥漫于《君主论》最后一章的民族主义呼吁在情感上则是理想主义的,二者之间的对比不能不说是相当惊人的。⑤吉尔莫(M.Gilmore)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他看来,在《君主论》最后一章,“政治现实主义方法的伟大分析家屈从于民族主义的浪漫立场”,马基雅维里的民族主义诉求事实上采取了一种非历史的方法。[13](P135,140)
吉尔莫之所以对《君主论》最后一章的“非历史性”指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基雅维里的民族主义立场似乎来得太不合时宜,它看上去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现实没什么关系,却关系到遥远的19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浪潮尤其是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
也就在19世纪,费希特第一次将马基雅维里视为一个民族主义者,麦考莱继之再后,他关于马基雅维里的判断极大地改变了马基雅维里在欧洲思想界长期以来的恶名。从那时开始,随着民族主义浪潮尤其是马志尼和伊曼努尔二世的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兴起,马基雅维里开始被视作一个意大利民族解放的先知,而《君主论》也开始被视作一个带有民族主义预言性质的爱国主义文本。19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史学家维拉里(Pasquale Villari)写作的马基雅维里传记是为马基雅维里正名的一部重要文献。维拉里认为,马基雅维里对意大利政治问题的诊断是极为正确的,马基雅维里深刻认识到,外部干涉以及四分五裂、无法统一的政治格局才是造成此后意大利政治灾难的根源,他所有著述的深层动机都可以归因于对意大利统一的渴望。另一位意大利学者、当时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弗朗西斯科·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甚至称马基雅维里为“意大利的马丁·路德”[14](P463)——在他那里,所有为马基雅维里所做的民族主义正名达到了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就在意大利最终统一、罗马获得解放的那一天,德·桑克蒂斯在他的《意大利文学史》中写道:“在我落笔的时刻,远方传来的钟声诉说着,罗马已经回到意大利的怀抱,窗外的人们不停地喊着,‘意大利万岁’——光荣属于马基雅维里!”[14](P545-585)
民族主义叙事的兴起毫无疑问是将马基雅维里从冷漠的道德立场中解放出来的重要一步,同时民族主义叙事也让马基雅维里成了一个预言家,然而却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预言家。对于19世纪的意大利人来说,马基雅维里几乎就是一个先知;而对于16世纪的意大利人来说,马基雅维里却只是一个似乎来得太早的先知。
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疑难”才成了一个真正棘手的问题。我们的确不清楚,是否应该把先知的穿透几个世纪的预见力看作一种贴近现实的洞察力?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最后一章提供的图景,究竟是“事情的实际真相”还是“事情的想象方面”?
二、《君主论》的“想象方面”
不过,无论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我们应当做出怎样的判断,单从《君主论》最后一章的文本角度,马基雅维里的文本实际上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建议的确存在着某些“想象方面的事情”。
《君主论》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奉劝君主“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这就是后世引之为民族主义叙事的来源。马基雅维里给出的这个统一意大利的建议,无论从语言修辞的角度还是从劝说逻辑的角度,都有偏离前二十五章的现实主义政治观察之嫌。
首先,从《君主论》最后一章的语言修辞来看,我们很难不对马基雅维里所采用的若干表达感到诧异。按照卡西尔的说法,《君主论》行文至最后一章,马基雅维里突然抛弃了之前的那种逻辑分析的方法和冷漠超然的态度,风格为之一变,其行文风格“不再是分析的,而是修辞的”。[15](P143-144)卡西尔的观察是准确的,但他并没有加以细致分析。事实上,举例而言,《君主论》二十六章之前的章节,征服或杀戮是以一种轻描淡写的中立性方式被描述的,比如第五章建议征服一个共和国最为稳妥的方式是消灭它,又比如第三章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语气中立地谈论法国为什么没有占领意大利。前者似乎完全没有设身处地考虑到佛罗伦萨本身作为一个共和国所面临的被征服的困境,后者也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意大利作为征服对象所面对的遭遇。但是在最后一章,对意大利被占领的描述却完全不一样。对于意大利被占领这样一个事实,第二十六章的描述借助了许多遭受暴行的情感词汇,而没有使用中立性的征服或占领式的表达。比如,在第二十六章中,马基雅维里谈到了蛮族对意大利的暴行和侮辱(crudeltà et insolenzie barbare),而在描述蛮族的暴行时,他甚至一连使用了四个音节饱满的情感性词汇以形容意大利所遭受的劫难:“被打击、被破坏、被撕裂、被劫掠”(battuta,spogliata,lacera,corsa)。[2](P121)、[16](P367)很明显,叙述的情感强度随着音乐性而得到了强化,意大利被占领不再作为一个中立性事实而出现,而是呈现为一个被征服者的苦难叙事。
其次,从《君主论》第二十六章所采取的劝说方式来看,《君主论》最后一章给出的建议也很难说是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的权力分析。严格说来,马基雅维里并没有提供解放意大利的具体方法,而是采取了某种倾向于忽略现实条件的道德鼓动。之所以如前文所述《君主论》最后一章在语言层面摒弃了前二十五章的中立性语言而采取情感性修辞,归根结底是因为他需要为意大利解放提供某种正当性诉求,这是“征服”或“占领”等中立性陈述无法提供的。
比如,第二十六章最为引人注目的段落之一是马基雅维里竟然引入了“正义战争”的观念,他饱含深情地说道,“伟大的正义(giustiziagrande)是属于我们的”,为此他还引用了李维的一段话:“对那些迫不得已(necessaria)进行战争的人来说,战争是正义的;对那些除了拿起武器就毫无希望的人来说,武器是神圣的。”[2](P121)、[16](368)
需要指出的是,“正义”(giustizia)一词在前二十五章只出现过一次,而唯一的一次恰恰出现在第21章马基雅维里试图证明君主必须在敌人和朋友之间做出选择、不要模棱两可地采取中立立场的时候。[2](P108)这似乎表明,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正义”与中立性立场是截然相对的,正当性诉求出现的时刻,也就是必须在敌人和朋友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刻,同时也就是必须放弃置身事外的中立性态度。对将意大利从蛮族手里解放出来的目标而言,其正当性诉求是明确无疑的,其敌友关系也是明确无疑的,因此,《君主论》前二十五章中那种近于刻意的、冷漠的中立语气和中立性分析方法反而是不适当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君主论》的最后陈词几乎是在一种强烈、甚至近于泛滥的正义感召中结束,似乎一切困难在“正义事业(impresegiuste)的那种精神和荣光”面前都将迎刃而解——“什么门会对他关闭?有什么人会拒绝服从他?怎样的嫉妒会反对他?有哪个意大利人会拒绝对他表示臣服?”——很明显,这是一个运用“正义感”说服听众的传统修辞术,在这种修辞中,正义淹没了对现实困境的度量。
又比如,在《君主论》最后一章中,马基雅维里还试图说服君主,眼前是一个将意大利从蛮族手里解放出来的良好时机。关于这个时机性的规劝(Exhortatio),马基雅维里使用的是在他那里常见的美德和命运的修辞。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马基雅维里的规劝逻辑,就会发现,第二十六章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时机性规劝实在是太过离奇、太不合理、太不具有现实意义。
为了说明这是一个解放意大利的良好时机,马基雅维里并没有分析意大利政治乃至于欧洲政治的现实格局,也没有提供解放意大利的任何切实有效的方法,他没有告诉我们该怎样对待独立的威尼斯共和国、该怎样处理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外部干涉力量、该如何应对教皇国在意大利的实际存在;相反,他仅仅举出了摩西、居鲁士、提修斯三位古代建国者,将他们三位视为摆脱外部压迫、实现民族独立的典范,并且指出,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是与他们的伟业相似的功绩。如果意大利目前的局面和他们曾经面对的局面极为相似,因此,能够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的人,也必定是与他们相似的豪杰。而为了认识这样一位意大利豪杰的能力,必须让意大利的现实处境和三位古代立国者的处境相似,甚至要更胜一筹,也就是说,“就必须使意大利沉沦到它现在所处的绝境,必须比希伯来人受奴役更甚,必须比波斯人更受压迫,必须比雅典人更加流离分散,既没有首领,也没有秩序,受到打击,遭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躏,并且忍受了种种破坏”。
仅仅从劝说的效果来说,马基雅维里的劝说方式遵循的是一种看起来再奇怪不过的逻辑。为什么现在是将意大利从蛮族手里解放出来的良好时机(occasione)?——是因为局面太糟糕了,命运太恶劣了。但只有局面太糟糕了、命运太恶劣了,能力和美德才能彰显出强大。如果能够在这种极其恶劣的局面里获得成功,那么对于君主的美德是无上的肯定。换言之,希望越是渺茫,荣耀越大。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美德彰显论的劝说,即困难是用来彰显美德的。不能说这种劝说没有效果,从鼓动君主追逐荣誉的角度,这种劝说或许的确可以起到一定的影响力。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意思反过来毋宁是说,荣耀越大,希望越是渺茫。马基雅维里当然清楚这一点,他其实承认上述三位立国者的行迹是带有某种奇迹的色彩,在行文中他甚至不惜借助了《出埃及记》中的神迹:“大海分开了,云彩为你指出道路,巉岩涌出泉水,灵粮自天而降,一切事物已经为你的伟大而联合起来……”
对于规劝君主行事而言,再没有什么比奇迹更不具有现实意义的劝说了。一旦借助奇迹,就等于是说,这并非是基于现实的分析,而是寄望于命运的修辞。因此,马基雅维里此处所传达的摩西立国式的感召,恐怕一定包含着事情的某些“想象方面”。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与马基雅维里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圭恰迪尼那里看得更为分明。圭恰迪尼可能是当时少数严肃对待马基雅维里统一意大利学说的学者之一,不过,恰恰在这一点上,他比马基雅维里要“现实”得多。圭恰迪尼在他的《关于李维史论的评论》中的一段话,表明他对马基雅维里的计划不抱任何希望,在他看来,马基雅维里没有估计到两个疑难:首先,没有一个君主愿意响应意大利统一的呼吁(1.10),因为,僭主是不可能有解放祖国的欲望,因为他感受不到给别人带来自由的那种快乐,对他来说,唯一的快乐只是权力;[17](P402)其次,意大利人的自由传统也不会对意大利统一有响应,尽管意大利的分裂带来了很多问题,但一个统一的君主国,其危害还是要大过分裂,意大利不同于法国,意大利从没有过一个统一的权力支配。对自由的渴望是意大利人的天性。尽管对于意大利以及统一意大利的那个城市来说,意大利的统一是一种荣耀,但是对于意大利其他的地区却毋宁是一种巨大的灾难。[17](1.120,P404-405)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吉尔伯特曾准确指出的那样,如果说马基雅维里那里的确存在着某种“民族主义”,我们也需要将他的“民族主义”与后世通常所谓的“民族主义”小心地加以区分。因为,我们很难确定,马基雅维里式的意大利统一,究竟是军事上的联合、政治上的联邦、还是某种统一的民族国家。[8](P38)马基雅维里并没有透露任何关于统一的意大利的未来政治构想,他也从没有把民族同一性作为立国的根据。因此,可以说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并不存在严肃的民族主义立场。后世如维拉里、德·桑克蒂斯乃至当代的阿尔都塞式解读只是自说自话,拿马基雅维里浇自家的块垒罢了。
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就此认为,第二十六章涉及的意大利的解放,只是一种纯粹对于新君主的激励,或者说只是一个纯粹修辞学的产物,其中是否包含着某些“实际真相”?这一点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三、《君主论》的“想象方面”与“实际真相”
事实上,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最后一章的劝说逻辑最终指向的既不是一个空洞的解放意大利的意愿,也不是与此相关的对实现意大利统一解放意大利的现实条件的分析,而是一个甚为奇特的立场——在他看来,解放意大利,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一个组织形式的“方法论”问题。
在二十六章最后一部分,马基雅维里分析了意大利人何以每每在军事上失败以及如何获得转变军事失败局面的解释,但是这一部分的解释与其说是正面论证意大利的军事实力足以和西班牙人、法国人或瑞士人相对抗,还不如说马基雅维里采取的是一种条件促成式的劝说。也就是说,马基雅维里所指出的并不是军事和政治领域里意大利的实际具有的实力,他指出的毋宁是意大利人可能具有的实力。他刻意描述了一组对比:即意大利人在决斗中或者在少数几个人的搏斗中体现出的力量、机敏和智力上的优异,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在大规模的军事组织和战争中的一系列溃败,通过这一对比,马基雅维里试图说明,意大利人的个人能力是强大的,但欠缺的是一种将意大利人的个人能力组织起来的“新方法和新秩序”。
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还是在《君主论》中数次使用过这一表述,⑥在《李维史论》开篇首句,他更是直接表达了意图探索“新方法和新秩序”(modi ed ordini nuovi)、涉足前人未及领域的理论意趣。可以说,所谓的“新方法和新秩序”就是马基雅维里本人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而马基雅维里之所以在《君主论》第二十六章的尾声部分采取那种具有诱导性的条件促成论的劝说,其论述的要点其实并不是论证意大利统一的现实可能性,而是论证新方法和新制度对于促成意大利统一的必要性。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意大利的统一并不是一个对现实条件进行经验分析的产物,而更像是一个用以验证其在前二十五章提出的“新方法和新秩序”的可能的政治实验室。夸张点说,对马基雅维里而言,方法论问题要大于现实问题,方法论的条件分析要高于现实的条件分析。
从马基雅维里的文本来看,他未必没有估量到可能遇到的批评和责难,实际上,马基雅维里甚至有意采取了一种忽略现实的表述。如果我们循着马基雅维里本人提供的方法论意识的线索,会发现,就在同样出现了“新方式和新秩序”这一表述的《君主论》的第六章开篇部分,马基雅维里提出了一个有意识引导我们忽略现实条件分析的著名比喻:
然而一个明智的人总是应该追踪伟大人物所走过的道路的,并且效法那些已经成为最卓越的人们。这样一来,即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他们那样强,但是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他要像那些聪明的射手那样行事,当他们察觉想要射击的目标看来距离太远,同时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们瞄准时就比目标抬高一些,这并不是想把自己的箭头射到那样高的地方去,而是希望由于瞄准得那样高,就能够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标。[2](P24)
第六章开篇的这个比喻,最直接的含义用通俗的话来讲,无非说的是,要想射得远,就必须抬高瞄准的目标。但是,马基雅维里同时也说到了,即便能力不足以达到聪明射手的程度,但模仿聪明射手的方法“至少会带有几分气派”。谁是那些“聪明的射手”?按照第六章的标题,应当就是马基雅维里所属意的新君主、“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地位创立国家的新君主。但我们同时应当注意到,第六章所引入的主题和研讨的人物,恰恰就是第二十六章马基雅维里试图让统一意大利的君主效仿的人物——也就是说,摩西、居鲁士、提修斯三位古代的建国者或新君主。从第六章开篇的比喻来看,马基雅维里实际上很清楚,作为古代建国者的摩西、居鲁士、提修斯本身就是极难效仿的对象,他所要设定的目标其实对于当时的意大利来说实在太过高远,意大利的统一只是那种要想射得远、就必须抬高瞄准点的目标而已,实际上远不足达到聪明的射手所能达到的“射程”。但即便不可能实现,也仍然有必要以之为模仿的对象。也就是说,马基雅维里在提醒我们——忽略第二十六章、转向第六章——更进一步说,忽略现实、转向方法。
因此,第六章的新君主和第二十六章的意大利解放者之间的对应,凸显的既不是二者实际能力的对应,也不是两者现实条件的对应,而只能是一种方法上的对应——即同时出现在第六章和第二十六章中的表述:“新方法和新秩序”。但问题在于,什么是马基雅维里的“新方法和新秩序”?如果这个新方法指的就是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第十五章中提出的关于事物的“实际真相”与“想象方面”的区分,换言之也就是我们在文初提及的作为马基雅维里思想内核的“政治现实主义”,那么,很明显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处境:这个政治现实主义的方法恰恰无助于我们理解或切中意大利的现实,而马基雅维里本人则近乎在以某种方式提醒我们——要忽略现实,关注“现实主义”的方法。
很明显,这里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概念裂隙,即对马基雅维里而言,在“现实”与“现实主义”之间很可能存在着某种无法弥合的差异。如何理解这个奇特的概念裂隙?是否在马基雅维里那里,“现实”和“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无法弥合的差异?
我们不妨选取一个角度,从马基雅维里所面临的批评来看这个奇特的概念裂隙。休谟在《论公民自由》一文中曾对马基雅维里提出过一段看上去极为有力的批评,他说,马基雅维里的论断几乎没什么教益。举例而言,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23章里说,一个软弱的君主如果过于依赖于他的某个大臣,这个大臣就会取而代之。问题是,几乎当今所有欧洲的君主都依靠他们的大臣而统治,马基雅维里的断言过去两百年之后,却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的君主遭遇过马基雅维里所断言出现的局面。大臣篡逆的事情从没有发生过,也几乎不可能发生。[8](P51)
初看上去,休谟似乎提出了一个对马基雅维里来说真正的诘难——为什么君主制不像马基雅维里想象的那样邪恶?休谟本人给出的答案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马基雅维里的原型只是古代的僭政和意大利的小公国。
有意思的是,佩里·安德森对马基雅维里的评价和休谟几乎如出一辙。在他看来,尽管马基雅维里所举出的忘恩负义、背信弃义、虚伪、欺诈等等堪称作“马基雅维里主义式的狡诈”,但这些统统只是意大利的小僭主们在本地统治所依赖的提纲挈领式的格言。它们与西欧君主国复杂得多的依赖于阶级力量式的政治思想全然搭不上界。马基雅维里所处的只是意大利僭主政治短命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世界,只是属于他所赞美的对象恺撒鲍尔吉亚的世界。实际上,“马基雅维里对王朝合法性的巨大历史力量几乎一无所知”。[19](P167)
休谟和佩里·安德森其实都认为,马基雅维里式的狡黠并没有触及现实的力量,只是一种对现实的邪恶想象,甚至不妨说只是一种“邪恶”的“乌托邦”——换言之,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其实与真正的现实经验无关,根本就算不上现实的“实际真相”!
但是,无论是休谟还是佩里·安德森似乎都没有看到,马基雅维里讨论的原本就不是休谟所面对的两百年的世袭君主制国家,也不是已经具有王朝合法性巨大历史力量的西欧君主制国度,我们称之为“马基雅维里主义式的狡诈”的那些东西,本来就是他在讨论一个特定的君主国类型即新君主国才会遇到的现象。
实际上,恰恰相反的是,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的第二章初论君主制时就已经区分了世袭君主国和新君主国,并且早早得出了一个足以回应休谟和安德森的重要结论——相对于新君主,世袭君主要更具道德性。
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2](P5)
马基雅维里的分析遵从的是这样一种逻辑:(1)在世袭君主制之下,人民习惯被世袭君主统治;(2)因为人民习惯被世袭君主统治,所以,世袭君主的统治就更具稳定性;(3)因为世袭君主的统治更具稳定性,所以统治者就更没有必要采取非常恶劣的手段来维持统治地位,因而统治的道德性就更强;(4)因为统治的道德性更强,所以统治的认同度就越高,世袭君主就越容易得到被统治者的爱戴;(5)因为世袭君主越容易得到被统治者的爱戴,所以被统治者就越习惯被世袭君主统治。由此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几乎无法打破的循环。
然而,马基雅维里《君主论》讨论的主体却并不是这样一种沉浸在“世袭统治循环”中的世袭君主国,世袭君主其实只是作为新君主的参照对象而被提及,并不在《君主论》实际研讨的对象之列,相反,恰恰马基雅维里要反对的就是这个世袭君主制的统治循环。在他那里出现的典范,摩西、居鲁士、提修斯等三位古代人物统统不是世袭君主,而只是山河破碎之日出来收拾山河、重建家园的建国者。因此,《君主论》实际上并没有讨论一般的君主国,甚至可以说,他把君主国的“一般”模型统统置于一边不谈,而只是讨论一种“特殊”的、“例外”的、与众不同的君主国类型——新君主国。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似乎更应当叫作《新君主论》,因为在他那里,并没有世袭君主的位置。而这一点往往被后来者忽略了,所有后人谈及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式的狡诈”,以及所有的所谓现实主义政治分析,其实都是局限于这样一个特定政治类型的分析的产物。
因为,根据马基雅维里在紧接下来的第三章开篇部分的分析,与世袭君主相比,新君主也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人民没有被统治的习惯;(2)由于人民没有被统治的习惯,新君主的统治也是不稳定的;(3)由于新君主的统治是不稳定的,所以统治者只能采取相对恶劣的手段维持统治,因而新君主相对更不具有道德性;(4)由于新君主相对更不具有道德性,所以统治者只能被畏惧而不是被爱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君主论》第十七章那个著名的残酷与仁慈的主题——实际上早已在第二章区分世袭君主和新君主时就已经交代在先——亦即那种“与其被人爱戴不如被人畏惧”的冷酷的现实主义,并不能被视作给予所有君主的建议。这个通常认为是典型的马基雅维里式的现实主义道德,其实按照马基雅维里文本自身的逻辑,完全不能适用于一个正常的、被“王朝合法性的巨大历史力量”所笼罩的社会,而只能适用于新君主的道德世界。换言之,他的“现实主义道德”所描述的当然并不就是现实的“实际真相”,这种“现实主义道德”只是一种特定情境的产物,远远谈不上描述了现实的全部,而只是一种特定的、有限、极端状态下的“现实”经验。
然而,一旦我们将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道德”理解为一种特定情境下的现实经验,那么,我们就将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这种特定情境下的现实经验又怎么能同时被视为“事情的实际真相”?难道在马基雅维里那里,“现实”和“现实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几乎无法弥合的差异?
四、《君主论》的“实际真相”?
综上所述,如何处理新君主与世袭君主的关系,于是成了理解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的关键所在。就文本而言,《君主论》第二章关于新君主与世袭君主的论述又是这其中关键之关键。
对此,Grant B.Mindle有过一种解释,他认为,《君主论》第二章关于世袭君主的论述只是一种试探性的思路,其表述具有一定的误导性(tentative and misleading)。因为,如果世袭君主国的统治确实如马基雅维里第二章中所描述的那样简单容易,那么整部《君主论》都是荒谬的,如果《君主论》只是为新君主而写,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世界上的世袭君主根本就不需要马基雅维里的建议。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将世袭君主的统治排除在外,那么,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科学就几乎只是一个对常态政治的补充而已,他只是讨论一些不同寻常的处境里的不同寻常的人物而已。
而在他看来,不同于第二章的试探性论述,马基雅维里的真正主张其实是这样的:每一个君主,无论他是靠世袭还是靠自己的能力或运气得到他的王位,只要他准备保住他的地位,就必须把自己设想为一个新君主,就必须设想一个极端、不同寻常的状态,像一个新国家的新君主那样行事。
也就是说,新君主在马基雅维里那里不仅具有绝对的优先性,而且还具有绝对的典范性,尽管就现实而言,新君主是一个极端状态的产物,但是一切常态政治都必须模仿极端的、非常态的政治。所以,Grant B.Mindle认为,在马基雅维里那里,“现实主义最终成了极端主义;常态最终融入了非常态”。[6](P214)从根本上说,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不同于已经存在于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古典现实主义和古代政治科学,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端主义”(extremism)。[6j(P214)而这种极端主义已经成为我们的政治和道德的基础。
根据Grant B.Mindle的看法,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其成果最终毋宁是一种不断革命论的学说。[6](P217)在他看来,马基雅维里的读者需要注意到,由于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拒绝任何一种现存秩序的合法性,君主不可能依赖于臣民的那种惯性的保守主义。马基雅维里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忠诚的世界,在这个没有忠诚的世界里,只有不断攫取他人,才能生存下来。
应当说,Grant B.Mindle的阐释的确不失其意义。马基雅维里在第二章区分世袭君主和新君主时曾经留下了一个伏笔,在他看来,世袭君主的统治之所以稳定,还有一个原因在于,“革新的记忆与原因,由于统治已经年代久远并且连绵不断而消失了”。[2](P5)这个判断表明,对马基雅维里来说,新君主的确具有某种优先性。因为,一切世袭君主从根本上说都来源于某个曾经的建国者或新君主,世袭君主本身的合法性来自于某个革新被遗忘了的新君主。也就是说,世袭君主中必定隐藏了某种新君主的成分,创新的成分对于任何一个王朝统治而言都是无法摆脱的,只不过这种成分已经顺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忘了——扩而言之,甚至不妨说,世袭君主只是新君主被遗忘的状态,“合法性”只是“非法性”被遮蔽之后的产物。
这个被遗忘和遮蔽了的“非法性”,仿佛是世袭君主无法摆脱的某种原罪,只要有世袭合法性的地方,就有这个原罪相伴随。安德森和休谟那里的“王朝合法性的巨大历史力量”,以及那种依附于这种王朝合法性统治的道德优势同样无法摆脱这种原罪。
Grant B.Mindle的阐释大体上代表了施特劳斯学派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与此相似而观点更为成熟、论述更为有力的是法国学者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马南的立场一贯与施特劳斯学派的立场相近,他的论述似乎是给休谟和安德森的质疑以一个确定的回答。
马南指出,马基雅维里最乐于研究的是“极端的情形”,比如国家的创立、政体的变迁以及政治阴谋的领域。与亚里士多德相比,马基雅维里通常采取的是起源或发端的视角,这些起源和发端则往往是充满暴力和不公正的。因此,二者相比较,亚里士多德采取的是一种城邦目的的视角,而马基雅维里采取的是城邦起源的视角。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城邦目的既包含了城邦的本质和城邦自足的发展,但对于起源视角而言,创建和守成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逻辑。马南指出,马基雅维里并没有否认,在正常的情况下,公民社会中存在着和平和某种正义,但马基雅维里实际上指出的是,这些寻常情形下的道德取决于不寻常的道德。因为,“‘善’的出现和维持只有通过‘恶’才能实现”。[20](P17)
在马南看来,如果说马基雅维里那里存在着某种现代政治思想中的“现实主义”,那么这并不意味着,马基雅维里认为,现实只有谋杀、阴谋和叛乱。马基雅维里实际上承认,在某些时段和某种政体下,“现实”中并不存在谋杀、阴谋和叛乱。显然,恶是一种现实,恶的缺失也是一种现实,只不过,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在政治上,“恶”比“善”更为重要、更为基础,也更加“现实”(real)。[20](P15)
无论是Grant B.Mindle 还是马南的论述,概而言之,大体上都是一种“极端主义”或例外论的解释。这种解释在所有对马基雅维里现实主义的理解中可谓独树一帜,它准确地把握了马基雅维里现实主义构造性的一面。经过“极端主义”视角解释的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毋宁说是一种对现实的新构造——空想性和现实的冲突在这种构造中消失了,因为,“现实主义”并不等于现实,它只是简化了现实,或者说构造了现实。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或许并没有真正触碰到当下的实际,但是它的意图也并不在于仅仅准确把握住时机性的当下现实,而是重新构造一个更加“现实”(real)的“现实主义”视角。
应当说,这种极端主义解释有着相当强的合理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区分亚里士多德的古代现实主义和马基雅维里的现代现实主义,极端主义解释也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古代的现实主义,无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古代政治科学那里、修昔底德的古代政治史学那里抑或是在君主的密室里发生的“统治心术”,都是一种时机化的产物,并不具备构造性的含义。实际上,光是让这种隐秘的心术得到明目张胆的宣扬,并不足以造就马基雅维里开启的现代现实主义。只要时机化的成分没有转化为构造性的成分,那么现代的“曙光”就远不足以到来。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妨把波考克也放在这一解释的序列里,看看他对马基雅维里所做的构造性的理解。在他看来:
必须设想一种情形,质料没有形式,最重要的是没有先前存在的形式,只能由革新者赋予它形式;而革新者必须是立法者。因此逻辑上的必要前提的是,英雄发现他的人民处于彻底的混乱状态;如果质料的形式已荡然无存,这可使他的“德行”摆脱对“命运”的完全依赖。[21](P169)
波考克的新君主(革新者)解释借助的是一个“没有形式的质料”概念,这显然是一种想象的极端状态——“现实”中当然不可能存在“没有形式的质料”——而绝非是真正贴近“现实”的洞察。但这却恰恰又是马基雅维里的“现代现实主义”的意义所在。
因此,方法未必而促成现实的相关性,但是却可以构造出一个新的“现实”——这就是在马基雅维里的“新方式和新秩序”照耀下、作为其思想内核的“政治现实主义”。概而言之,马基雅维里在理论上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发明了一种新的“现实”,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基雅维里毋宁是发明了一种新的视角转换的方式。古代的政治理论徘徊于典范和现实之间,但马基雅维里式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对古代的颠倒,并不是用现实的优先性取代了典范的优先性,而是重新发明了一种新的视角转化的方式,即在常态现实与非常态现实之间的视角转换。这种非常态的视角在名义上是一种“现实主义”,实际上却是一种在现实中几乎无法抵达的“乌托邦”——后来的自由主义理论通过自然状态学说、马克思主义通过革命政治、当代生命政治通过赤裸生命概念一再重复了这个视角的转换——后者也几乎构成了现代一切政治思想的前提。
五、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方法”
但是,我们还不能就此止步。
马基雅维里并不就是后世的种种的极端主义,“极端主义解释”的问题在于,它更类似于一种理论后设的解释,更类似于“施密特主义”而并非一般所谓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尤其是,当Grant B.Mindle指出,“每一个君主,无论他是靠世袭还是靠自己的能力或运气得到他的王位,只要他准备保住他的地位,就必须把自己设想为一个新君主,就必须设想一个极端、不同寻常的状态,像一个新国家的新君主那样行事”——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马基雅维里的原意了。一方面,这种“马基雅维里主义”仅仅指出了例外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但同时却丧失了马基雅维里本人那里实践上的意义:把世袭君主的行为准则等同于新君主的行为准则,则更近乎一种缺少克制的疯狂实践,反而坐实了休谟和安德森那种邪恶乌托邦的指责。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解释在文本上也缺少依据。
实际上,在《李维史论》里,马基雅维里恰恰提供了另一种反对滥用“非常手段”的说法:
在共和国里,人们并不希望事事动用非常手段,因为非常手段彼时或许有益,开此先例却贻害无穷。一旦有人养成了为行善而打破成规的习惯,在这种风气之下,后人也可以为作恶而破坏成规。事事以法律规范之,每遇危机皆有确定的因应之道,待之以一定之规,非此共和国不足以称善也。[22](P135)
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在《君主论》里,马基雅维里也并没有完全置合法性于不顾。实际上,马基雅维里并非只是在第二章讨论了世袭君主的问题,在全书结尾的第二十四章,马基雅维里实际上又回到了第二章的主题。在那里,他明确指出,“上述各种事情,如果能够审慎地遵守,就能够使一位新君主宛如旧君主一样”。[2](P115)而这恰恰意味着,在马基雅维里那里,除了“极端主义”的一面外,还存在着另外看似“保守”的一面: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并非只是在理论上指出了,极端和例外相对于常态和正常的优先性、新君主相对于世袭君主的优先性,而且,他实际上还告诫我们,在实践上,新君主的所作所为其目的在于最终“宛如旧君主一样”。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马基雅维里并非完全置合法性于不顾,在《君主论》里也并非只有关于新君主实践与世袭君主实践的断裂和区分,这个伟大的政治文本同时还描述了新君主与世袭君主的连续性。事实上,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新君主当然不仅是某种意义上的革命君主(全新)或某种意义上的征服式君主(半新半旧),而且也还是潜在的世袭君主的前身。《君主论》其实不乏构造合法性的途径(或者说构造由不合法到合法的连续性),只是这一点非常隐晦,不容易辨识分明。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第八章“论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一节曾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表述:
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这样一来,由于不需要一再从事侵害行为,他就能够重新使人们感到安全,并且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怯懦或者听从坏的建议不这样做,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而且他永远不能够信赖他的老百姓,而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因为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些;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2](P43)
这个著名的段落看上去是一种典型的马基雅维里式的“狡诈”,因为马基雅维里在这里公然主张,坏事要一次性做绝,恩惠则要慢慢赐予。毋庸置疑,马基雅维里的这个主张带有他一以贯之的道德冷漠和对于人性的蔑视,但是我们不应当被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马基雅维里此处的表述尽管的确是“狡诈”的,但是他毕竟主张,新君主应当让人民感到安全,不应当一再损害人民的利益。尽管这些主张只是为了巩固新君主的统治,尽管在道德上我们仍然不可能对这些主张假以颜色,但毕竟相较于那种最激烈的“挑衅式的邪恶”,马基雅维里的这里的主张似乎要“显得”更为“道德”一些。
更为重要的是,马基雅维里此处的表述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对《君主论》一个重要主题的“修正”。在《君主论》第十七章里,马基雅维里曾明确表达过,君主应当被人畏惧而不是应当被人爱戴,而在这里,马基雅维里实际上的观点却是: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爱戴还是要好过被人畏惧。当然,马基雅维里这里的主张在表述上要更为狡黠一些,他告诉读者,任何一个新君主,如果时时刻刻给人带来畏惧,那么他的统治是不可稳固的,因为,这样他就必须时时刻刻拿着钢剑,就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
如何协调这两种立场?
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这段表述实际上是为《君主论》一以贯之的“残酷与仁慈”“恩惠与恐惧”的主题最终添加了一个创新和守成的要素。马基雅维里事实上主张,守成应当依赖于缓慢的恩惠,而创新应当取决于迅速的、一次性的暴力。缓慢和迅速的对比,意味着一个时间性因素的引入,而时间性因素的引入,已经使得新君主原本单纯的创新行为已经包含了守成的要素,也就是说,已经包含了合法性的重构了。⑦而一旦引入了合法性的重构,道德似乎注定会以某种面目回到政治的视野里。
一般认为,《君主论》的十六章到十八章对传统美德主题的挑衅式重构,是典型的马基雅维里式的道德,比如君主应当被人畏惧而不是应当被人爱戴,就是马基雅维里式道德的核心命题之一。但是,这实际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考虑到上述的时间性要素的引入,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认为,属于新君主的那种挑衅式的不道德行为,几乎在一次性的暴力完成后就已经消失,因为他不可能时时刻刻提着他的钢剑。⑧
这实际上也就是被后来者称之为“暴力的经济学”的主题,沃林(Wolin,S.S.)在《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与创新》一书中讨论马基雅维里的名为“政治与暴力经济学”的一节已经注意到,马基雅维里的暴力运用完全不同于索雷尔式的暴力应用,在她看来,马基雅维里意识到暴力的有限功效,他致力于阐明的是暴力如何得到有效运用的技巧,“比起那些鼓吹用暴力的圣火进行净化的理论家来,他对政治的道德困境要敏感得多”。[23](P233)而这种包含着道德敏感的、对于暴力运用的技巧性的一面,既体现在第八章关于以邪恶之道取得君权的讨论中,也包含在第十八章关于狮子和狐狸的著名比喻的讨论里。
就在这一章节里,马基雅维里告诫新君主,首先,“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其次,不仅如此,“并且还要这样去做”;再次,“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2](P85)我们当然可以说,马基雅维里鼓吹的仅仅是“伪善”,因为,他同时还以另一方面方式告诫新君主,“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2](P85)——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需要“伪善”?为什么仅仅像狮子那样作为是不够充分的?
这不仅是因为,“伪善”实际上是道德敏感度的一种标志,而且还因为,这种狐狸式的狡诈本身对应的是一种扎根于现实中的“政治想象”。正像此章下一节所说的那样:
一位君主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语不是洋溢着上述五种美德的说话,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君主显得具有上述最后一种品质,尤其必要。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眼睛更甚于依靠双手,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样的,但很少人摸透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这些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2](P85)
这里著名的关于“眼”和“手”的区分,其实恰恰说明了“伪善”何以从根本上是无法摆脱的——因为,大多数人依靠的是眼睛而不是双手,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你的外表,所以,表现得“伪善”才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恰恰由于大多数人无法摆脱“政治想象”,所以君主才无法摆脱“伪善”和“狡诈”。必须指出的是,在大众的“政治想象”和君主的狐狸式“伪善”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关联性。如果撇开这一点谈论马基雅维里式的“狡诈”,将没有任何意义。
阿尔都塞敏感地觉察到这里包含的政治意味,他准确地指出了,马基雅维里的骗术实际上是一种与暴力无关的特殊意识存在。用一种时代错乱的讲法,这种“骗术”所指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用语里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君主其实就是国家的公共面孔,所以他必须注意把人民对他的形象的表述纳入人民的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在政治上对他有利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骗术才起了作用”。[24](P496)
如果一定要使用某个概念术语来形容这里出现的与政治狡诈相对应的大众幻相,为避免时代错乱之嫌,我宁愿借用维罗里使用的词汇——“政治想象”(Political Imagination),[5](P496)而不采用“意识形态”这样一个过于现代政治科学的用语。无论如何,“政治想象”是从第十八章这里关于“眼”和“手”的著名区分里衍生出的一个主题。它实际上是对《君主论》的第十五章关于“事情的实际真相”和“事情的想象方面”区分的重要补充,二者合而为一才构成了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的全体。
与第十五章的表述不同,在这里,实际上,“政治想象”是作为政治现实的一部分而出现的。马基雅维里在这里实际上表明,一个真正彻底的现实主义立场,不仅需要区分在理论上什么是现实的什么是想象的,而且还需要知道在实践上运用“政治想象”甚至制造“政治想象”。只有走到了这一步,“事情的实际真相”和“事情的想象方面”才真正得到了全面的回答。
继而,如果我们认识到,不仅宗教中包含着政治想象的成分,而且世袭制中也包含着政治想象的成分(比如遗忘),那么所有现实主义疑难也就有了答案: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是一种“极端主义”,但在实践上却并非如此——因为,他要用“极端”的手法,造成一个“正常”的幻觉。
收稿日期:2016-09-26
注释:
①即《君主论》第六章和第二十六章以及《李维史论》第一卷第一章。
②此处译文参照Machiavelli N,Burd L A.Ⅱ principe(Clarendon Press,1968)以及Machiavelli N.The Prince,Harvey C.Mansfield,Jr.tra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85.P.61,有所修正。
③根据纳杰米的考察,immaginazione一词很可能首先是由马基雅维里的朋友韦托里引入的,关于马基雅维里与韦托里的通信中immaginazione一词的起源,参见John Najemy,Machiavelli and Language,in:Niccolò Machiavelli's Prince 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5.P.98-99.
④但是根据巴隆回忆,马丁利在晚年最终放弃了这个观点。
⑤关于《君主论》最后一章与前二十五章之间的关系,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派为“断裂论”,一派为“统一论”。吉尔伯特的立场毫无疑问属于“断裂论”,而与老派的吉尔伯特的“断裂论”不同,近些年盛行的、以波考克和维罗里为代表的共和主义修正派倾向于认为《君主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最后一章并非某个与全书脱节的民族主义段落,同其他章节一样,最后一章仍旧是某种共和主义式的爱国主义情感的体现。但是,这种解释丝毫也不能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马基雅维里爱的究竟是哪一个国?佛罗伦萨还是意大利?为什么在《君主论》最后一章,马基雅维里的基本认同超出了佛罗伦萨的视野,而追求意大利的自由和解放?这不是一个共和主义所能够解答的疑难,而只能借助于民族主义的叙事。
⑥即《君主论》第六章和第二十六章以及《李维史论》第一卷第一章。
⑦当然,从字面上看,这里马基雅维里只是说,恩惠能够使人民感到安全,并且赢得人民的信任和爱戴。但事实上,对马基雅维里而言,任何一种合法性无非是一种靠恩惠关系维持的东西,合法性的丧失意味着旧的恩惠关系的瓦解,而重建合法性就意味着重建一种新的恩惠关系——这一点,可以从《君主论》中的多处文本得到支持。
⑧考虑到实际政治过程中的建国行为的复杂性,我们实际上很难在一个确定的时间节点上界定何为开端性的建国行为,到何种程度这个行为才算作完结,因此,那种一次性的暴力行为或者说唯独属于开端的原始暴力行为,几乎就是一个逻辑性的概念。
参考文献:
[1]A.H.Gilbert.Machiavelli's "Prince" and its Forerunners:"The Prince" as a Typical Book "de Regimine Principum"[M].Duke University Press,1938.
[2][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M].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Harvey Mansfield.Machiavelli's Virtu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4]Harvey Mansfield.Machiavelli's Enterprise,Machiavelli's Legacy:"The Prince" After Five Hundred Years[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5.
[5]Viroli M.Machiavelli's Realism[J].Constellations,2007,14(4).
[6]G.B.Mindle.Machiavelli's Realism[J].The Review of Politics,1985,47(02).
[7]Felix Gilbert.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Machiavelli's Discorsi[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14(1953).
[8]Felix Gilbert.The Concept of Nationalism in Machiavelli's Prince[J].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Vol.1(1954).
[9]Garrett Mattingly.Machiavelli's Prince:Political Science or Political Satire?[J].American Scholar 27(1958).
[10]Hans Baron.Machiavelli:the Republican Citizen and the Author of "The Prince"[J].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76(1961).
[11]M.Jurdjevic.A Great and Wretched City[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12]A.Moulakis.Republican Realism.in Renaissance Florence:Francesco Guicciardini's Discorso Di Logrogno[M].Rowman & Littlefield,1998.
[13]M.Gilmore.The World of Humanism,1453-1517[M].1962.
[14]Francesco De Sanctis.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M].Joan Redfern.Harcourt,New York,1931.
[15]Ernst Cassirer.The Myth of the State[M].Yale University Press,1946.
[16]N.Machiavelli.Bund L A.Ⅱ principe[M].Clarendon Press,1968.
[17]The Sweetness of Power:Machiavelli's "Discourses" and Guicciardini's "Considerations"[M].trans.James B.Atkinson and David Sices.Northern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2.
[18]David Hume.Of Civil Liberty[A].Hume.Political Essays[M].ed.Knud Haakonsse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19][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0][法]皮埃尔·莫内.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M].曹海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21][英]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22][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论李维[M].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23][美]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与创新(扩充版)[M].车亨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