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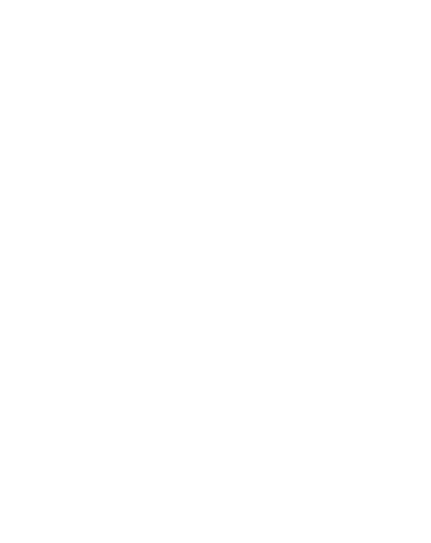
90年代中期我博士毕业留校后,做过几年教研室秘书。那些年,高校尚未“争世界一流”,事务不多,我这个秘书的主要任务,一是替教研室主任跑腿做活儿,二是替老师们报销发票。当时教研室的报销有两类,一类是系里的年终福利,一千、两千,每年一次,需用发票去报;二是教研室人头经费,每人每年有几百元,滚动累计,随时可报。那时钱少,因而这些事务,并不繁重。但是每一次报销,王老师都将大大小小的发票整理好,按财务报销的样式粘贴在纸上,并将合计金额用他特有的硕大的钢笔字写在空白处。此事原不足道,但年复一年,无论哪次报销,教研室老师中,惟王老师一人这样做,从不省略。其实,生活中的王富仁老师,似乎很有些粗枝大叶的,穿得随意、土气,吃不怎么讲究,写字用蘸水钢笔,不在意细节,不计较他人的态度;惟其如此,他一张一张将出租车票参差而整齐排列、粘好的这种细致,才格外令人感慨。在这些琐屑的小事中,你能感受到王老师出自本性的对他人的体贴与尊重。
王老师凡事替他人着想,无论巨细,事例很多。譬如,在他家聊天,如果你不主动告辞,他从来不会有任何表情暗示“今天是否到此为止?”只要来客没有走的意思,他会一直侃侃而谈下去。有人评价王老师健谈,可我总觉得这健谈当中,有古道热肠。记得有一次,我在王老师家客厅坐到中午12点了,而他谈性正浓,我不好意思打断,便继续听他高谈。客厅对着厨房,厨房那边传来炒菜声音。一忽儿,一个俊秀的男孩,微笑着在客厅门口露了一头,旋即不见。我知道那是王老师的大儿子肇磊,那时待业在家,负责做饭。谈话间,不知不觉,厨房声音停歇,除了客厅坐而论道的声音,阖宅安宁,似不食人间烟火处。那天好像聊到快一点了,我才告辞。出门时,瞥见肇磊从另一间屋闪出,微笑着快步进了厨房。就在我与王老师在门口道别时,厨房响起菜回锅的嗞啦声。我一边下楼,一边抱歉地想,王老师的忠厚、谦和,也传给了儿子。
有一次在中文系办公室,见王老师正在复印东西,原来是肇磊写的诗。他递给我几页,我带着好奇拿回家读,有一首题目大约叫《什么时候》,诗句多半忘却,但诗的意境和情绪,却都还记得:都市的夜晚,融不进的城市,走失的故乡,没有形状的孤独,渺远的爱情,还有,月亮一般浑圆的心……语言和情绪都单纯明净,有一丝不为人知的酸楚。我想起客厅门口一闪的那张男孩俊秀的面孔。后来隐约知道,王老师博士毕业留校后,师母带着两个儿子举家从山东迁来,肇磊那时大概已上小学,一口山东话,免不了受欺负。肇磊后来没考上大学,一边在家自学,一边做家务。下一次见到王老师,我说肇磊的诗很单纯,有点忧郁。他没说什么,只嘿嘿一笑。后来,每当王老师复印肇磊的诗,就会在信箱里给我放上一份。一位父亲对儿子厚重的爱,细腻的呵护,深沉的忧虑,都在这无声的交流中,被我领略到了。
我一直觉得,王老师的性情,与他的名字一样,富“仁”仗“义”,且此仁义似乎与生俱来,流淌在血液中。我自忖他这种性情,大约与齐鲁大地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有关,但王老师绝不认同。记得有一次又说起这话题,王老师狷介的一面立即显露。他说正因为儒家文化传统深厚,才导致山东人至今奴性十足,把山东人好好批了一通。他说山东人喜欢当官儿,惧怕当官儿的。一谈到儒家,他就回到了五四,样子都变得有几分像鲁迅了。这时,即便内心对他的言辞并不完全信服,却也难以辩驳。
和王老师请教、闲聊的时间不算少,他说过的话,大半记不清了。但他关于“人”的观念,一字一顿地说出“人!”这个字眼时的神态、语气,却始终栩栩如生。他在很多场合、很多谈话中,都强调“人”。这个“人”,是五四新文化“立人”之人,是独立思考、不依附、不盲从的特立独行的个人。他经常勉励我要做一个有独立思想和判断的知识分子。从80年代研究鲁迅,到90年代研究文化,“人”的观念,始终是他的价值立场。这一点,他与钱理群先生很相似,以鲁迅继承人自居,不遗余力地张扬人的个性,推崇人的价值,追求人的自由。
如果说“人”的观念,是王老师学术思想的一个价值核心,那么关于“爱”的论述,则是他为中国文化走出困境所设想的路径。这方面,没有宗教信仰的王富仁老师,往往显示出类似宗教信仰者的执著与热忱。
大约1997年,我先生请王老师前往其供职的中国工运学院(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做演讲。王老师讲的题目是《影响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几个现实问题》,这篇演讲后来在《战略与管理》发表。那天晚上,他一口气讲了四个钟头,忘记休息,忘记喝水。茶水凉了兑热,热了又凉,放在他眼前,他却浑然不觉,全身心沉浸在演讲中,就那样一口气讲下去,整整四个钟头,没喝一口水,没休息一分钟!他的殷切、真诚、忘我,以及深刻绵密的逻辑,征服了听众,也感动了听众。那天的演讲,最后一个问题是独生子女问题。王老师讲到,独生子女多在城市,他们对世界的观念建立在父母单方面的爱与保护中;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占据优厚的社会资源,但人格是脆弱的,感情是孤独的,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个人主义的。农村家庭则普遍有两个子女以上,一半是“黑孩”,从小生活在歧视、匮乏中。当生活境况、受教育程度、人生观迥然不同的一代人,成为下个世纪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时,社会可能发生巨大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导致社会动荡。那么,怎样避免冲突和悲剧呢?
“爱。”
我至今记得他一字一顿讲出“爱”这个字眼时,脸上凝重的表情。
多年亲炙教诲,聊的话题不少,很多时间是天马行空的坐而论“道”,有时也不免感到有些大而无当。但王老师的现实关怀,那种赤诚,却一直令人感动和敬重。就在前不久(3月底),他来北京第二次化疗,我去医院看望。看到他说话有些气喘,身体比以往虚弱,本不愿他多说话,便主动找些话题讲,可最终,还是他说得多,我说得少。我很内疚引他又说那么多话。离开医院时想,下次再看他,一定事先想好说一些他不了解的事,那样可以少让他费神。不想,仅仅一个月,那样一位永远在思考,永远在关怀,永远在谈话的,不屈服于命运的激情昂扬的王老师,怎么就永远消失了呢!每念至此,心中隐隐作痛。
然而,打开他的书,读着他的文字,回想着与他的谈话,他那带着浓厚乡音的,一字一顿的“人!”与“爱!”,那眉宇中间坚毅的神色,分明就在眼前。
无论死亡的话题多么令人沉痛,但死亡与王老师,始终不大能直接联系起来。我脑海中存留的,总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王老师,一个不倦思索、关爱他人、高谈阔论的王老师。他的生命,早已超越了物质的存在,永恒地活在精神的时空。
尊敬的畅言客户,您好。您所使用的网站评论功能已广告作弊被限制使用,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电话400-780-9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