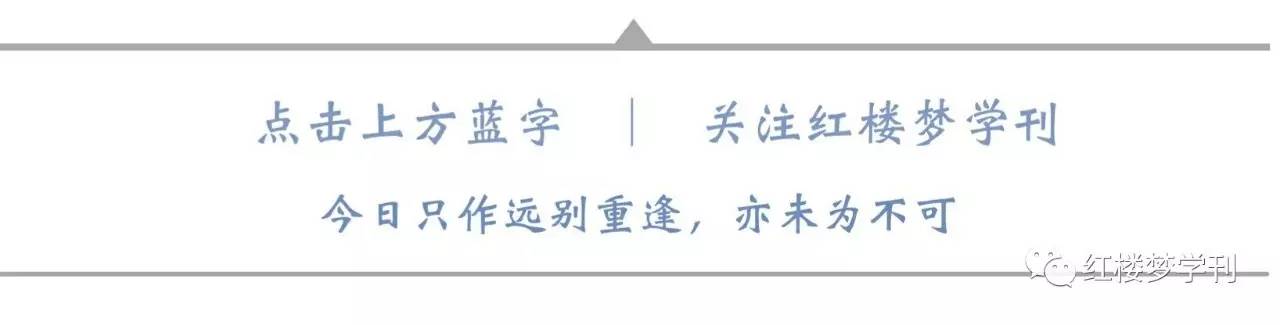

作者 刘中山
余秋雨先生在散文《废墟》中写道:“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只有屈原、杜甫、曹雪芹、孔尚任、鲁迅、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其实细细品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除了屈杜曹孔及其作品,具有悲剧精神和悲剧意味的作家作品还有很多,被誉为四大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所具有的许多共性之一,就是其故事内涵,都充满了悲剧色彩。所谓悲剧性,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别人看。换言之,就是在文学作品中一边创造真善美的形象,一边又无情地撕毁它。
一
《三国演义》贬曹褒刘,加重刘蜀在三国历史语境中的分量,大量的笔墨用于刘蜀一脉人物的刻画与塑造上。后人评三国人物形象塑造,有“智绝、义绝、奸绝”的“三绝”之论。然,终其一书,“义绝”身首异处,殒命疆场;“智绝”呕心沥血,未捷先死。诸葛亮的去世,成为继刘备崩殂后刘蜀由盛转衰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蜀终亡于魏后,刘备诸葛亮的人生悲剧,自然上升为家国悲剧。另一方面,小说里的反面角色,令《三国演义》的读者恨得牙痒痒的曹操,终成为乱世奸凶、治世能臣,占据整个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时天下无人可与之交锋,邪终压正,成为一段历史的隐痛。
两起悲剧的大潮次第退落,在唏嘘不已里,读者又看到一起更大的悲剧之潮扑天盖地而来,那就是曹魏不幸祸起萧墙,被司马氏暗算。可见,”义绝”“智绝”“奸绝”之悲剧,终究是人生悲剧,而曹魏之灭蜀吴,司马氏之篡魏,才是真正之大悲剧,也是《三国演义》这部书要表现的悲剧主题。这是个人、家国与时代相交织的政治悲剧,在这场大悲剧里,一切有价值的,一切无价值的,一切的一切,注定都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毁灭!
二
提到悲剧的毁灭性,那就必须提到《西游记》。尽管整本书取材于玄奘取经,但玄奘及其经历,已退居于线索地位。更多的笔墨集中于神魔世界,可以说其主旨更倾向于凡人(神魔)所面临的“一念即佛(神),一念即魔”的困境,这无疑有明显的教化意义。其实按佛家的观点“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执着于“神”与“魔”,都是着了相,故“是故所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孙悟空正经历了这样一个看似虚妄的观念世界的打压和围剿,才终究成为观念世界里的“佛”。孙悟空由魔成佛的经历,正是天性一点点被扼杀,人对自由的追求一点点萎缩,人对于不合理现实的反抗一点点被镇压,人对梦想的一点点远离与抛弃。从被压五行山到从师唐三藏,从诳戴紧箍到成为斗战胜佛,其在观念世界的身份越确定,其作为天地之灵的天性越削弱。
这是典型的个人悲剧,比突遭横祸式的生命悲剧更深刻,更具有普遍性;更重要的是,《西游记》把目光从政治舞台转移到人之天性上,是人之天性毁灭之悲剧!

三
《水浒传》与《红楼梦》的悲剧意义有相似的地方,就在于这两部小说所反映的基本是现实悲剧,远离了庙堂之上运筹帷幄的神秘和神魔世界变幻莫测的神圣,显得更接地气,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水浒传》反应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存悲剧,这种悲剧是特定时代特定历史环境里人如何才能生存的悲剧。具体而言,在这样的时代,要么放弃反抗等屠戮,要么通过反抗求生存,总之,《水浒传》是一部关于反抗的悲剧。
具体来说,《水浒传》所呈现的世界里,不反抗是死,譬如林冲,妻子被高衙内调戏,忍;被朋友陆安出卖,忍;被董超薛霸恶意烫脚,忍;可这一切忍却换不回一份平淡的安定的生活,在草料场虽未烧死,罪亦当诛;反抗亦是死,譬如江南方腊,占据江南,猛将如云,勇士无量,反抗的可谓彻底而坚决,虽然小说直接未提及此次起义的原因,但通过杨志等十制使押运花石岗亦暗暗指出,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激发了此次反抗行动,但这次反抗终究还是被梁山人马给镇压;反抗后受招安亦是死,譬如宋江,与方腊同样是官逼民反,却费尽心思走上了受招安之路,与之互相厮杀,两败俱伤,更加悲怆的是,获胜者宋江最终被高俅等人阴谋下毒而死,令招安之路亦成为死路。被反抗者呢,则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拉拢和屠杀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但纵观一部书,发现这些被反抗者亦没有什么出路,顺我者可能会死于逆我者之手,譬如蔡九,譬如高廉;那些高高在上暂时的得势者们,亦逃不脱历史的惩罚(徽宗蔡京之类),与他们的惩罚同时到来的,还有整个国家所受的惩罚(历史维度)。
四
当然,从悲剧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讲,《水浒传》还远远未能达到《红楼梦》的境界。《红楼梦》虽表现的也是人的悲剧,但这种悲剧意味远远超过了生存层面。《红楼梦》里的人物大多不会有生存层面的的危机,因为生存是寻求物质保障和生命安全,刘姥姥那样的赤贫人家显然不是小说要着力刻画的人物。四大家族占据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都是显赫一时。这样的大富人家该是当时社会里贫寒家族所奋斗的目标,譬如家族已经没落的贾雨村。
在这样的家族里,往往“一荣俱荣,一损即损”,习惯上我们这八个字用来评价四个大家庭,但事实上也代表了一个大家族内部的的生存境况。家庭是由家庭成员构成的,家族的兴衰离不开家族的每个成员的人生故事,可以说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家族命运系系相关,正如纪伯伦说:“假如一棵树来写自传,那也会像一个民族的历史。”我们查看《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的子弟的生存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大家族成员内部精神的危机,显然超过了生存的意义。
许多论者的目光仅停留在《红楼梦》浅层次的即生存层面的悲剧意味上,譬如宝黛爱情的悲剧,归因为社会环境(贾家家长)所不允许。事实上,从宝黛相恋的过程来看,二人已经从大时代里以貌取人以家庭门第取人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走进各自的心灵世界,共同构建出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独立于世俗世界的一个理想世界。这个世界并不遥远,它就存在于此时此刻。同时,这份感情也从现实存在的男女关系即皮肤淫滥中挣脱了出来,自然、纯洁而异彩纷呈。婚姻绝非这份情感的终极目的,这种灵魂伴侣和精神知己本就存在于当下。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内在于两人的心灵世界,不像是李逵恼了提板斧砍人那样具有可操作性。如鲁迅所言,他们始终面临的是一个无物之阵,他们找不到敌手,但始终被团团围绕的敌手的阴影所笼罩。这就涉及到了他们所生活的国度、时代、文化、礼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个人与国度、时代、文化、礼俗即整个生存大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突,令这份追求本身就如飞蛾扑火一般,意味着牺牲和死亡。这是一份早于这个时代产生,却在这个时代灭亡之后还不一定产生的感情。因此这种感情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悲剧,就像莲盛放于严冬,雪怒飞于盛夏,美丽的诱惑与死亡的威胁同在。
再比如,一些论者认为贾府由盛转衰的悲剧是《红楼梦》主要表现的悲剧,且列举了许多导致衰落的原因,其实这些原因细究起来,更像是大家庭衰落时家族成员的表现,比如铺张奢侈,比如道德败坏,比如争权夺利,等等,这种种表现,孙绍振先生归结为贾府男性接班人的精神危机。这种精神危机表现为“既没有道德,又没能耐,更没有责任感”。这种理解显然更加深刻,可是说到底,贾府接班人的精神危机何以产生却仍然没能点明。
如果说宝黛爱情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太超前,超越当时的时代,那么贾府产生衰败的危机的原因,则是由于合府上下人等沉湎于现实的富有,从而丧失掉了生存的危机感,用孟子的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小说所写的时代正是贾府走向鼎盛的时代,安逸享乐成为整个大家庭的主旋律。这个时代的贾府就是一锅温水,温水里挤满了享乐的青蛙。
先看主子们,贾敬一心当神仙,贾珍父子一味高乐;贾赦虽袭官,却终年在家,嗜好收藏小妾和古董;至于贾政,第四回有如下文字:
虽然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则族大人多,照管不到这些;二则现任族长乃是贾珍,彼乃宁府长孙,又现袭职,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则公私冗杂,且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余事多不介意。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此人〝治家有法〞徒有虚名,家中诸事根本不管也无能力可管。
主子们的精神意志的衰退,与家业的逐渐兴隆密切相关,这种生活态度自然也传递给奴才们,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贾府虽屡屡禁止下人们赌酒耍钱,但下人们赌酒耍钱的行为却屡禁不止。所以会出现这种原因就在于,在主子们最好的时代,也是下人们最好的时代,主子有资财享受生活,奴才也有资财耍钱取乐――这样的时代,享受生活似乎成为一种共识,花钱如流水恰恰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贾府的衰败只是表象,贾府合府上下精神的萎缩腐朽和没落才是作者要着力表现的内容。
从这种意义上讲,贾府的兴衰的悲剧性就具有样本意义,它已经超越了小说中的贾府,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切大家族的一个缩影。〝月满则亏,水满则盈〞,这本是自然规律,然而中国历史上一切大家族何以总会走向〝登高必跌重〞的老路?曹雪芹明智地绕开了前三部名著对外在世界完全的否定和批判,而是把目光明锐地投入到人的精神世界。他深刻地察觉到伴随着物质世界的衰落过程,在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在发生着生动而细致的变化:一方面是精神世界的萎缩腐朽没落,另一方面是新的精神萌芽的生发。曹雪芹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浮冰之下深邃的人的心灵世界,完成了对前三部名著从外在世界索取生存价值的超越。因此,《红楼梦》的深刻不仅仅停留在社会哲学的层次,更指向于构成这样的大家庭的每一成员的心灵深处,重在探究人的精神世界颓塌的根本原因。
综上可知,《红楼梦》的悲剧性超越了前三部名著所表现的形而下的〞人的悲剧〞,即从重在表现人对物质世界的追求中产生的困境和悲情,上升为一种对精神世界的病态现实的探询,亦即人的精神力量何以在物质世界萎缩与何以从物质世界超越的问题,从而具有了普遍性的哲学意义。
四大名著所表现出来的悲剧,各具风貌,各具特色。四部书所涉及的内容,由个人而家国,由人生而政治,由个体而群体,由江湖而庙堂,由黎民而奸凶,由凡人而神魔,由现实而神话,由物质而精神……可以说涉及到了我国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深深浅浅,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人民命运的悲怆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