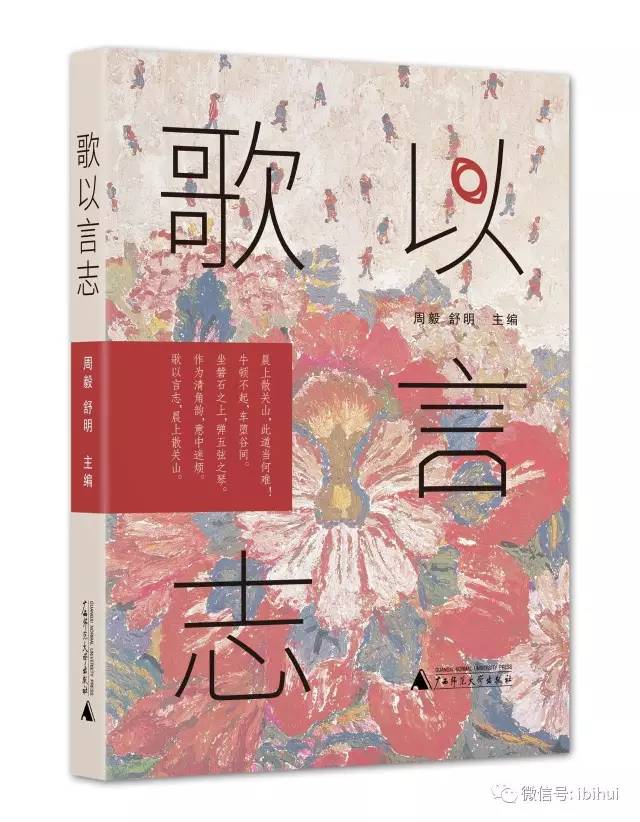| 他好像很不喜欢沈曾植,在日记中说他,“肮脏之气溢面”,他形容说,沈曾植说话声音很大,犹如壮年人,“说话间不断在唾壶吐痰”,这使得释宗演和他的随从觉得,沈曾植像一个粗野的乡下人,绝不像一个名满天下身居高位的名士。
井上円了的欧美考察
日本善于模仿和学习,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是,在隋唐宋元时期日本多次派遣僧人来中国学习。不过,自从十三世纪后期“蒙古袭来”或者叫做“元寇”的事件之后,情况略有变化。尤其是,经历了明清之际“华夷变态”,为了防止切支丹影响而成“锁国时代”,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当明治维新后日本由“锁国”而重新“开国”,他们的模仿和学习却转了一个身,从东方转向了西方。当然,无论学中国还是学西方,他们都是一样执著,一样热情,一样专注,也一样有成效。
关于明治之后日本佛教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我以前为了写《西潮却自东瀛来》一文,曾经花了很多时间,专门看日本佛教徒留学欧美的若干记录。这次为了讨论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之后,中国与日本佛教应对西潮的不同,所以,又仔细看了看著名的井上円了《欧美各国政教日记》(收入《井上円了·世界旅行记》,东京:柏书房,2003),这部日记记载明治二十二年(1889)他对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考察。
这一年,他乘船经旧金山横穿美国,又从纽约渡海到达英国,在欧洲考察之后,再经由印度洋回国。
井上円了(1858-1919)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学者,对中国影响很大,现在东京的东洋大学就是他创立的。当年,蔡元培就翻译过他的“妖怪学”著作,鲁迅和周作人当年也曾对他的“妖怪学”很有兴趣。不过,在这部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和政治有密切关系,卷入维新大潮的日本佛教学者,他所关注的问题,其实,倒是一些影响后来日本国家与宗教发展的重要要素。
第一,传统宗教在现代国家中有什么作用?在对西方各国政教考察之后,他下了一个断语说,“国家的根本是精神”,而不是“军力、商业、金钱或学术”。井上认定,现代文明不仅仅是有形的文明,而且是通过教育塑造的无形的文明,这种无形文明是竞争中淘汰的结果。他以基督教为例,说基督教能够经历变化,仍旧是欧洲普遍信奉的宗教,这是它自身经过十字军东征、新大陆发现、印度洋航海、接触阿拉伯和印度新文化,并且能“新旧相合并酿成文明新元素”(25页)。所以,从这一点出发,他也期待日本佛教能够成为这样的宗教,介入现代国家,成为国家的信仰核心。而这一点,恰恰正是近代中国佛教所缺,却是近代日本佛教着力的方向。
第二,毕竟他是日本佛教的信仰者。这一立场使他认定,西方文明虽然有用,但不能就这样用在日本,正如美国的共和政体适用于美国,俄国的国教适用于俄国,因而这些制度和宗教,未必适用于日本一样。他相信,社会如同生物,要把外来的东西消化吸收,才能成为自己的原质(27页)。他认为,日本的“皇统一系”(天皇制)国家与“僧统一系”的(本愿寺)佛教,这两者正好就是互相适应的。这一点绝非偶然,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日本人重血统,所以,“皇统”与“僧统”一系,自然成为人民自然拥戴之文化(27页)。
第三,他出访欧美,也刺激了他思考一个日本佛教如何应对世界变化的问题。他认为,一个国家要独立,必须有语言、历史和宗教的独立。日本佛教虽然从外传来,但自从弘法大师提倡“神佛调和”论以来,外来信仰与本土资源彼此协调,所以成为日本精神的来源,而其他宗教都不适合日本人民。但是,他也看到,自基督教从欧洲和俄国传来,就对日本宗教作为日本国家的精神支柱产生冲击。所以,他考察世界,正是为了了解远西之国,在巨变时代如何保护自国的宗教(31页)。
第四,欧美的现状也刺激他重新思考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他说,“所有的人必须兼明两件事情,只见其一,则会是偏见。政治家要了解政治上的保守与改革两种主义,哲学家也要了解哲学里面的理论与实践两种派别。”(22页),而政治与宗教之间,有表里两方面的关系,也就是彼此冲突,也彼此依赖。因为尽管西方世界强调政教分离,不允许神圣宗教干预世俗政治,但是,政府既要通过制度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幸福,但也需要通过宗教使得人民安心。
考察了欧美各国之后,井上円了总结世界政教关系的三种类型:一是有“国教”,政教合一;二是有“公认教”,但政教分离,三是“齐民教”,政教绝不混同。他说,明治日本是第二种,虽然理论上政教分离,但是宗教却在社会上有“公认教”之事实,而在制度上无“公认教”之名义。所以,他始终注意观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各种情况,为日本佛教寻找应对现代世界的策略。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所注意的,是寺院与人口、宗教的心理疗法、教会何以衰落、教堂如何维持礼拜等传教方式、教会对英雄的表彰、教会的会议制度等等,甚至连基督教教会的收入分配与教士的收入多少,他都看得十分仔细,并且不断以此与日本佛教对比。比如,他比较了西方基督教与日本佛教的仪式,包括(a)内部的装饰,包括偶像、偶像之光明、神像前的礼坛、花瓶、供奉物品;(b)礼拜的仪式、法衣、珠数、合掌跪坐、焚香诵经、铃与钟;(c)僧侣生活,是否带妻、外出穿着法衣、祭日断肉、寺院寄宿、有男女僧尼、法王、教正统辖教士等等(62-64页)。此外,他也考察了欧美宗教大学的设置、慈善会和布教会的活动,以及西方宗教对于婚姻与丧葬的处理。
考察欧美的时候,他时时想到的是日本。在日记的最后,他说到“哲学馆”的改良,他认为,国家之独立,端赖语言、历史和宗教之研究教育,而大学就是这样的研究和教育机构,目的是(一)大学应当爱护和教育日本固有学问,以文学、历史和宗教学为主,振兴日本之学问,保存日本人心和维护独立精神;(二)大学要分西洋和东洋两部,东洋部分要包括中国与印度,因为日本的学问中有很多是从印度和中国来的,可是要清楚地知道,“经过千余年,这些外来的文物已经形成了日本的性格,外来的元素已经化成一种固有的国风民风,与印度与中国大为不同”(148页);(三)他提出的理想是“日本主义”,“一方面维持本国的独立,一方面爱护日本固有的学问”,而东洋部中有关日本固有的学问,即神佛儒三道以及我国固有的文史哲(148页)。这显示了明治日本佛教的入世雄心,但是回头看看中国,在1889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大清帝国的佛教徒,却仍然还在睡梦之中,难怪寄禅说,“嘉道而还,禅河渐涸,法幢将摧;咸同之际,鱼山辍梵,狮座蒙尘”,连佛教内部都腐败和衰落得不成样子,更不要说管国家大事,也更不要说去睁开眼睛看世界了。
顺便记上一笔。此书之《西航日录》(井上円了的明治三十五年环球航行记录,亦收入《井上円了·世界旅行记》,东京:柏书房,2003)中记载,河口慧海,也就是写下著名的《西藏三年》的那个日本人,将取道印度进藏,他在印度见到康有为,康有为曾赋诗赠河口慧海:“禅僧凿空寻西藏,白马驮经又再来。阿褥达池三宿住,金刚宝土四年回。异书多半出三藏,法海应今起大雷。更向泥巴求古本,神山宗教见新开。”我没有去查书,不知道现在的《康有为全集》中有无此诗,姑记于此(168页)。
释宗演的中国日记
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很瞧不起中国人,尤其是甲午一战之后,那种鄙夷心理似乎表现得格外明显,连日本佛教也对中国佛教很轻蔑,觉得中国一蹶不振。所以,从东本愿寺一系到中国开教的僧人起,就存了一个用日本佛教反过来拯救中国人的心思,所以,释宗演这本记载他到中国访问的日记《支那巡锡记》(收于《释宗演全集》第九卷,东京:平凡社,1929)前面,著名日本思想家德富苏峰(猪一郎)写的序文中就公然说,“禹域之文华,至此时糜烂极矣,盖由宗教之衰,民志绥也耳。今(宗演)提斯法,拯四亿之溺俗。”(5页,撰于大正七年1918)

释宗演
释宗演是日本禅宗的著名僧人,他的学生铃木大拙更是赫赫有名。他到中国来是为了用日本禅宗来拯救中国人心吗?这一点暂且不必管它,倒是这部日记中有一些好玩的记载,让我们知道一些民初的学林掌故。
据日记记载,1917年9月,释宗演乘坐火轮船,经日本濑户内海的下关,越过对马到韩国釜山,然后,从韩国由陆路进入中国,9月下旬到达北京。在北京的时候,他拜访了好多政府要人,像总统冯国璋、总理段祺瑞、财政部长梁启超、外交部长汪大燮、教育部长范源濂、交通总长曹汝霖等,里面有一些谈话,也许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有用(如收在《随行日志》81-83页中与梁、汪的谈话要点),但我没有太大兴趣,倒是注意到一条,曹汝霖曾经提醒释宗演,日本佛教若想要在中国传教,要注意中国人对日本僧人“食肉带妻”的嫌恶。曹汝霖为什么要提醒他这一点?似乎可以好好琢磨。
这部日记(以及随行人员的《随行日志》)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下面这一段。这一年的11月11日,释宗演在上海与僧侣座谈之后,被姚文藻拉去见沈曾植(日记印刷本中“沈子培”误作“陈子培”),通过翻译和沈曾植交谈。释宗演也知道沈曾植是中国学界重要人物,“(沈)氏,孔门学者而复辟派领袖”,又是“上海有力量的佛教信仰者”,但他好像很不喜欢沈曾植,尽管他说,沈曾植“确实是热心佛教者,对佛教衰颓非常感叹”,可是在日记中又说他,“肮脏之气溢面”,他形容说,沈曾植说话声音很大,犹如壮年人,“说话间不断在唾壶吐痰”,这使得释宗演和他的随从觉得,沈曾植像一个粗野的乡下人,绝不像一个名满天下身居高位的名士。他甚至给了沈曾植两句评语,说他“余一寸白发,近七十岁顽固老人”,谈话“殊无趣味”(292-293页)。
很多日本学者像内藤湖南等,都对沈曾植佩服得一塌糊涂,可释宗演对于沈曾植的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有点儿意外。
本文刊于2017年8月5日《文汇报 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