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人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都有着各自的“病”。只是这种病并不是心理诊所意义上的心理疾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些人“有病”,很多意义上是这些人有幸或不幸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中,但大多数人对这个变化并不自觉,任凭环境将自己裹挟其中。因而,他们除了跟随这个环境起起伏伏,跟随这个环境的“超现实”搞不清自己是谁之外,也就只有指责这个好像和自己无关的环境的能力了。《无名指》里的“心理诊所”,所要处理的心理问题,正是在一个“物”的飞速变迁中,“物我”关系会因为没有得以及时调试、认真反观而产生的种种困顿;““我”的心灵,“我”的精神世界,也就会常常处于某种半坍塌状态。
”

城市:包裹我们生活的皮肤
——小说《无名指》中的北京与北京人

陶庆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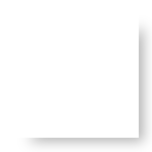
翻开《无名指》的开篇,我非常惊讶于李陀上来就用两节、约4000字的篇幅,写了发生在主人公杨博奇心理诊所也就只有几分钟的场景。这样一个几分钟的场景,竟然是如电影画面一般运动着的:雷雨夜,闪电般的富豪金兆山来访,闪电般地金兆山手下王颐闯进,闪电般的一个湿漉漉的女人冲进诊所猛扇王颐的耳光……那场景,还带着各种声响——雷雨的,打耳光的,带有东北口音的话音,女人一时间刺耳的尖叫……而这一混杂着各种声响的场景,又在倏忽之间复归宁静,复归到开篇处寂静雨夜里菲兹杰拉德的歌声,以及,杨博奇诊所里吃剩下的肯德基鸡翅的香味。
各种感官居然在阅读文字的过程中被激活!这4000字篇幅的运动场景,初看上去,似乎在回归 “写实”;但仔细阅读下来,此写实非彼写实,其实它已经对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写实”动了大手脚——经由这手术,“写实”在21世纪的今天越过20世纪直接回到了19世纪。这是一次挑战,不但是对读者阅读习惯的挑战,也是对批评家的挑战——我们赖以进行文学批评的某些语词与概念,比如写实,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无名指》中,如果我们放纵被文字激活的感官,就可以无比畅快地进入到李陀用文字/书面语创造出的一个带着颜色、带着味道、带着声响、带着质感一个以“北京”为“原型”的现代大型城市中。不管是主人公杨博奇流浪般地在城市里行走过的南长街、日坛公园、景山前街、世贸天阶,三里屯village、五道口……还是主人公杨博奇与他的女朋友周樱点评之中的城市景观——“一盆带有香港土豪味儿的脏水”的东方广场……这,都是一个既带有强烈共性的大型城市,又是有着独特的烟灰色调、飘荡着槐花香气味的大型城市。
这样一个以运动着、敞开着的姿态,融汇着记忆与当下、躁动与宁静、贫穷与富贵,小清新与脏乱差……的现代城市,是一个我未曾在其他文艺作品中阅读过的城市。
我们日常生活于其中而有些不自觉的城市场景,李陀用文字语言赋予了读者感官上的体验。比如,那个如“巨型人工钻石”的三里屯Village,在“每一个棱角、每一个斜度、每一个折面”的“破碎晶面里,都活动着一群群凌乱的人影,在吃、在喝、在买、在高谈、在阔论,在笑语,在喧哗,在引诱,在蛊惑……”,比如,在雕刻时光咖啡厅里“眼见一列车奔驰而来,又倏忽消失在视野之外”,比如,瑞金俱乐部迎宾小姐的脸冰冷到整个屋子都不用制冷,比如,南长街暗红墙壁的树影以及浮动的槐花香……而李陀用文字写下的还不仅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而且,还有随着环境剧烈变化着的人的衣食住行。他关心着这些人在穿着什么衣服——冯筝为着约会刻意穿的是紫色宽条纹针织衫、叠穿了宽松的烟灰色短袖T恤与鹅黄色紧身七分裤,金兆山穿着的是一件红色英文字母R、A、V、i、J、z、h、L、H个个都被绷得紧紧的好像长在皮肤上的LV黑T;他还关心这些人吃着什么样的食物——苒苒亲手做的吃着能“在嘴里唱歌”的笋干扣肉,杨博奇为周樱在大雪夜里用大衣裹着从“嘉禾”打包的野菜粥小笼包;他甚至还关心这些年这些人都长成了什么样子:“线条和轮廓都有一种女性味道”的小白脸王颐;“脸部的轮廓软塌塌的,不够硬朗”的祥子,在唱歌的时候眼睛光芒凌厉,连一双招风耳都很张扬……,还有,不仅如此,他还关心我们在城市的咖啡厅里偶尔听到的叽叽喳喳:“粉条”老师的交响乐广告,新婚之夜跑回家吃馄饨的新郎……一个城市的物质面貌,就随着杨博奇的游走而绚烂起来;而在他笔下游走着的杨博奇,也就不会如同许多小说的主角一样只生活在他自己情节的环境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绚烂的生活场景中。
李陀是非常认真、非常刻意地去以白描(对不起,当“写实”回到19世纪,当下的文学理论的语词实当然也是需要再造的)——写下这个城市几十年中被一股强大力量重新塑造的每个街角、每个景观。李陀是以他对19世纪写实的理解,用21世纪的文字/书面语与语言节奏,创造了一个鲜明的物的世界;在这个鲜明的物的世界中,我们的感官经验重新苏醒。也正是在这个重新苏醒的过程中,我隐约觉得某种与我们的身体紧密粘结在一起的环境,逐渐与身体剥离,变得透明、可视起来。这不是“陌生化”——它一点也不陌生,一点也不疏离;但读者借助这种文字的力量,获得的却是超越日常经验、反观生活环境的一种视线。
对不起,在这时候,我痛感文学理论的贫乏与批评语言的词不达意。
这是一种带着鲜明中国审美经验的物我关系。物与我并不分离;但经由某种视线,物与我却可以获得某种相对独立的位置,“我”才可以看到“物”的本来面貌,也才有可能看到“我”与“物”的关联。也就是在这种视线之中,我们也才可以重新审视那个一直以来紧紧包裹着我们身体的环境——而且,恐怕到这时我们才会惊觉,我们喜欢也罢,憎恶也罢的环境,是这几十年来经过我们的意识与无意识,共同创造出的一个全新的物的世界;也只有在这个视线之中,我们才能重新审视一下与环境裹在一起的全新的自己。《无名指》以“写实”创造的,正是一种重新认识现实的能力。
在《无名指》中,我还发现这样的生活场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不管是金兆山在三间房为自己打造了就缺俩黑人的非洲海滩,还是苒苒家分别用黑、白大理石打造出的一点“不懂得谦虚”的洗手间,不管是半夜里灯火辉煌如同海市蜃楼般的金鼎轩,还是“发疯”一般能将欲望变成味道声音颜色光彩的三里屯……在李陀精细的白描中,他越“写实”,现实就越发地呈现出超现实的一面——不是手法的超现实,而是现实本身在“超现实”。你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人们,在这短短的三十多年的时间,以什么样的想象力、以什么样的精神动力、以什么样不屈不挠的斗志,将自身的生活场景塑造的如此——“超现实”?
《无名指》的人物就是在这样一个现实/超现实的环境中摇曳多姿地登场的。
在《无名指》里登场的人物,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成长起来的、带有不同阶级身份的个体。他们中既有有着深刻官场背景又有着艰难创业史的金兆山家族,也有着北漂民工王大海及他的同伴;当然,这中间登场最多的人物,可能是李陀最感兴趣的广大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他们的阶级属性固然不同,但他们的来处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在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经过漫长的时间与变化的空间改造的个体。
李陀用心理诊所作为“无名指”的核心场域,某种程度上当然是有着隐喻的色彩——这些人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都有着各自的“病”。只是这种病并不是心理诊所意义上的心理疾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些人“有病”,很多意义上是这些人有幸或不幸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中,但大多数人对这个变化并不自觉,任凭环境将自己裹挟其中。因而,他们除了跟随这个环境起起伏伏,跟随这个环境的“超现实”搞不清自己是谁之外,也就只有指责这个好像和自己无关的环境的能力了。《无名指》里的“心理诊所”,所要处理的心理问题,正是在一个“物”的飞速变迁中,“物我”关系会因为没有得以及时调试、认真反观而产生的种种困顿;““我”的心灵,“我”的精神世界,也就会常常处于某种半坍塌状态。
虽说是写心理问题,但李陀更多是以对话的方式来处理人的心理与精神问题。这,的确是如李陀所说 “向曹雪芹学习”,也是在今天的文学创作中,创造一种重新捕捉生活的写实方式。《无名指》的对话,对话的结构方式以及每一小节的安排方式,都值得单篇文章去梳理,我在这儿并不细谈了。一个很显然的成果是,李陀通过结构对话创造出的人物,都是那样清晰地带着与环境之间的关联——而在这样清晰的关联中,人的内心与精神世界,又都有着不同类型的波澜壮阔。这些人,有无视环境变迁随波逐流的,比如那个自作聪明混迹于学界/商界之间主人公的好哥们儿华森;也有在环境变迁中“迎风而上”不困顿不纠结的:比如长了张俊秀面孔但不择手段的王颐博士,比如那个从形象到语言都完全不回避自己是个“坏人”的金兆山的四弟——但即使这样一个纯粹的“坏人”,李陀居然给他留了张照片,记录下他在苦难童年中的动情笑脸。
当然,《无名指》中不是所有人物都如此彻底地不思考环境为什么会变,不思考外界变化中的“物我”关系——他们当中有人对于“物我”分离有着明确感受而非常痛苦。比如,那个总是 “化繁为简”的石头,可是,李陀索性就“安排”他在身体上就是个残疾;而那个总纠结“为什么想的和做的不一样”的苒苒、在李陀笔下无所不能的苒苒,也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
李陀没有为这些“病人”提供出口。
在《无名指》的所有人物中,工人王大海带着“凛然不可欺的严厉”的出场,是最有分量的,但李陀非常现实地让他去山西挖煤去了;杨博奇送给王大海女儿的夏加尔画册,可能是知识分子对这一阶层最温暖的同情与最无奈的关怀了。李陀也没有让自己的主人公杨博奇找到出路。到最后,杨博奇在因他而被KTV开除的员工仇恨的目光中被击倒,在路边昏迷,在昏迷中逃跑——就如同他一次次在情感关系中逃跑一样。不能如金兆山、王颐们一样与这个时代搏击或者苟且,逃跑与回避几乎就是一种本能吧。
《无名指》也就差不多书写了春末夏初到夏末秋初的一个片段时光里的城市生活。没有答案、没有出路大概也是必然的。但在这样一段与杨博奇共度的夏日时光中,我们也许对于石头近乎固执的追究,对于苒苒有些绝望的孤独,对于冯筝幼稚但明快的理想……能多一点的理解吧。
读完李陀的《无名指》,我会有些为没有出口的生活而惆怅。但想想,谁规定的小说就得给人一个出口呢?就如同李陀说他要学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哪篇小说不都是在心灵的纠缠,在意识与下意识的互不妥协中,一步步地追问人为什么要选择善、人又为什么会那么恶?也许,出口就是我在《无名指》这儿看到的一个隐含的动机——李陀在不断地追问这些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或者,想到哪里去?
持之以恒、毫不妥协的追问,就是寻找出口的唯一路径。
END
本文首发于收获(harvest1957)8月5日推送(见下方“阅读原文”),此处刊发的是陶庆梅老师的最终改定版,与《收获》版略有不同,还请读者留意。感谢陶庆梅老师对活字文化的支持!

《无名指》(李陀)
主人公杨博奇,中文系出身,在海外又拿了社会学和艺术史的硕士学位,为了从“人的内部”理解人的秘密,又修了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以心理医生为职业在北京谋生。这个职业使他见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人,有大老板,有公务员,有家境丰裕而内心迷茫的家庭妇女……经济在不断发展,而人的内心却无处安放,自己个性不羁的女友突然宣布分手,至交朋友历史学教授出轨,朋友聪明绝顶的妻子要出家。深研过文学和心理学的博士在光怪陆离的现实面前也失去了判断力,仅仅在不是自己病人的那些打工者身上看到了些许微光。

李陀:《雪崩何处》
活字文化策划,“视野丛书”
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
视野丛书(6册)由北岛发起、主编并作总序推荐,张承志、徐冰、李零、韩少功、汪晖、李陀等集体呼应,集合了六位中国当代活跃在文艺领域的至为重要的作家、批评家、艺术家,由他们梳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思考脉络,精选出足以体现这六位作者数十年来思想精髓的代表作。视野丛书高度浓缩地呈现了当代中国极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宝库。视野丛书文字可读性强,面向普通读者,让他们得以循着文化思想的脉络,追踪当代中国的种种问题,获得思考的乐趣。
李陀从80年代至今,一直是文学评论界的重量级人物,也是中国当代文艺变迁的深度参与者。本书收入其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不同阶段的评论文章,从中清晰可见一条中国当代文化流变的线索。作为对文化与时代的思考成果的记录,作者的观察与批评具有宽阔的视野和理论的功力,其中有许多如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的犀利意见。
转载请联系后台 | 入群请加微信:dask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