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买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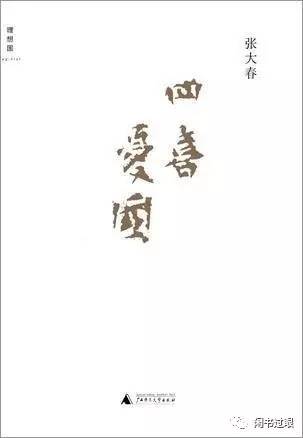
《四喜忧国》;张大春著;北京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大春在文体上是多样的。他自己讲过“多彩胡须”的故事,明人笔记《耳新》中记载有奇人张幼于,银髯如戟,喜欢随身带五色假胡须,经常更换,以博路人惊艳。张大春说这个故事,是为了阐明自己在小说文体上求新求变之心。
文体只是小说的一部分,张大春尽管文体多变,但并非来自独创,仍有传承可循。台湾那一代作家,具有丰富的国际视野,早在大陆“先锋派”勃兴之前(其实很多先锋派,最后或多或少都减少了试验性质的文字游戏),台湾那一代作者就开始在形式上有意吸纳西方的经验了。张大春在整个台湾作家现代派的序列里,尚属后来者,在运用的纯熟浑化上却后来居上。遍观《四喜忧国》,多部短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每种风格的运用皆有妙谛,不难发现其中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借鉴与发扬。比如《长发之假面》急转直下的故事结构,《饥饿》荒诞中的隐喻,《如果林秀雄》中虚实相生的层层递进,《自莽林跃出》中的异域魔幻,《悬荡》中的意识流,都不难在西方找到对应的作品。
不必逐个分析《四喜忧国》中每个故事采取的手法了,张大春在技巧上的游刃有余已彰显无遗。我欣赏张大春的地方却不在他文体的多样性,反在其幻化跳跃背后,叙事中对人生和世界的敏锐观察。其实任何修饰、装扮,不管新潮或复古,只为了承托衣装下的人。小说的叙事、人物,才是灵魂。
张大春的故事有时故作崇高中含嘲弄,有时幽默中隐伤感,乃至温情中闪出残酷。比如《四喜忧国》中的朱四喜,相信道德沦丧,国运衰微,皆因缺少了老总统振聋发聩的声音。所以他要不顾自己认识字有限的困难,一遍遍拟定《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可见理想不一定是伟大的,反而常常是滑稽的。但可笑之中,朱四喜的形象又使人悲悯。《如果林秀雄》描绘人生无限的可能,却恰恰用这种可能映衬出人生残酷的本来面目。《再见阿郎再见》,一个原本可能无比香艳的故事,最后为死亡的火焰吞噬,素描一样的笔触,写出人行为后的心理状态,黑色结局又令人感伤。
可能是太在意文体上的新鲜感了,有时技巧的闪光反而妨碍了小说的深度,乃至文笔的顺畅。太过炫技,消解了读者的注意,更分散了作者笔下的力道。《如果林秀雄》精妙的结构,却在人物命运描述上太过随意。《饥饿》和《最后的先知》不但故事间有连续性,也可看作一体之两面,但张大春在一味铺陈荒诞时,能放而不能收,故事略显沉闷。技巧固然重要,文字所能触及的灵魂才是小说真正的深度,在深度的开掘,与韵味的悠长方面,张大春道行尚浅。
好在以张大春流露出的才气,尚可弥补他的不足。在炫目的形式背后,还能透出对人物、对文字的掌控力。《咱俩一块去》这种看来文体较平实的作品,其实有着扎实的技巧,更显张大春功力。《新闻锁》里对一件小事细微刻画,看似平实,但内里的荒诞,人物对体制对抗的孤绝,却有着深刻韵味。
张大春为《四喜忧国》做了一篇万言长序,名为《偶然之必要》,在里面他说:“我徒然学会了抗拒热闹,却来不及透悟真正的冷清。”这中间有自谦的成分,但能够留在时间里的小说,真要抗拒热闹,透悟冷清才行。
尊敬的畅言客户,您好。您所使用的网站评论功能已广告作弊被限制使用,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电话400-780-9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