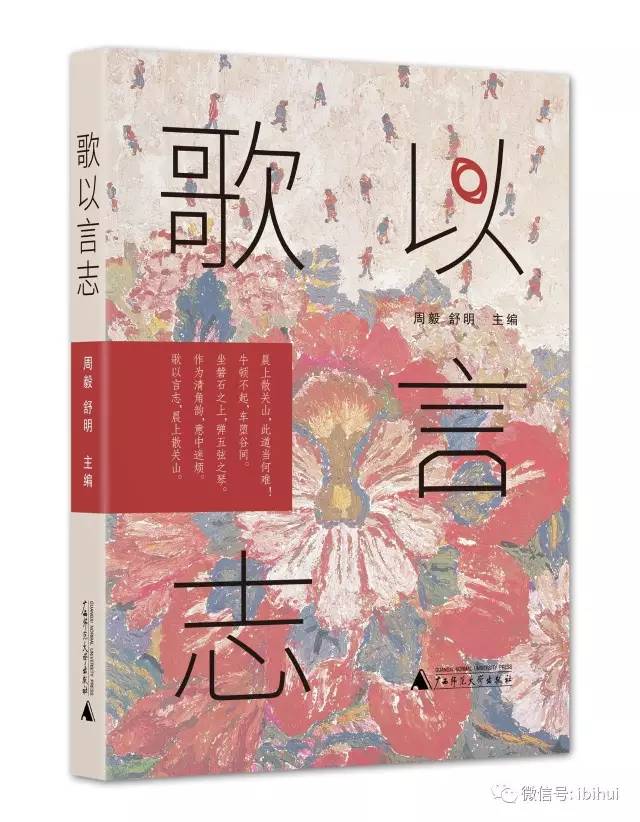7月3日早上,一打开手机,猛然跳出在剑桥做博士后的妹妹留言:Johns(我在剑桥做访问学者时结识的房东先生,下文写作“约翰斯”)去世了,听说是从花园梯子上摔了下来……一时不知所以,眼前不由浮现出两年前那个夜晚:女儿在他家练琴,巴赫的主题变奏曲,有些难。不巧,正是约翰斯因病住院刚从医院回家的第二天,他的声音很低沉,还嘶哑着,可他的耳朵,不能容忍半个错音出现——他禁不住就坐到琴边,指导女儿。一小节一小节地过,出一个错,就要从头开始。饭端上来好一阵子了,他仿佛没看见。珍姐(朋友们对他太太的习称)提醒他,他说过会儿。再催,就不高兴了:Stop fussing! (别再唠叨了!)旁边的我,坐立不安,忍不住还是轻轻请求了一下,他很客气地回答:有微波炉,过会儿加热下即可。我只有暗暗期盼,能听到约翰斯那声肯定的 “That’s it”,而不是“揪心”的“From the beginning”,这样他就可以尽快吃上晚饭,女儿和我也舒一口气。终于,基本过关,女儿被准许从琴凳上下来了,看看表,已近十点。约翰斯还微笑说:我没问题的,就是小孩子恐怕要休息了。
那以后,我们尽量挑约翰斯不在家时练琴。其实,十岁的女儿也明白,有约翰斯指导她受益不浅,可是,他实在太投入了,我们怕影响他的身体恢复。他是因心脏问题叫了救护车入的院,不到一周就出院了。珍姐说,是他自己要求回家的,理由是“如果不让我弹琴,还不如死掉!”
是的,约翰斯,是视钢琴如生命的人。机缘巧合,友人介绍我们住到了他们家——一栋临街两层小楼西侧一楼的一个房间。这栋楼有相连的东西两座,中间一道约一人高的长长树篱隔开房东与租户,门前则有一扇小铁门相通。没过几天,我们发现一个规律,每到傍晚七点,雷打不动,隔壁就传来琴声,或沉郁或飞扬。循声而去,隔着玻璃门看到约翰斯的身影——弹琴时,他总是换上正装,白色长袖衬衣配黑色西裤,躬身专注于琴键。隔壁的我们,每日晚饭时美妙琴声入耳,如行云流水“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的确让听众幸福至极。终于,女儿禁不住手痒去弹了两首拿手曲子,约翰斯称赞她弹得不错,手指很有力度,一定要继续学习,不要中断。不多久女儿入学后,幸运地找到了老师,约翰斯听说后忙不迭转身到他拥挤的书房,挑选出两本琴谱,供女儿使用。
对他的这份投入,我不由当面表达由衷钦佩之情。约翰斯没多说,只说他小时候,不管走到哪儿都有琴弹(即便到欧洲大陆度假时),因此他可以不间断练琴。他并未在专业音乐学校深造过,但是,他热爱钢琴。他现在用的这架普通原木色雅马哈立式钢琴,是他工作以后自己赚钱买的,很有些年头了。琴凳右侧,一只小方柜,放置练习用的一摞琴谱。他的话让我想起,有一次,他跪在地上,穿着工装裤给家里的木门挨扇上油漆的情景,我惊讶他是多面手,他却淡淡地说:因为我是“二战 ”后出生的一代,所以必须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的。
约翰斯是内心世界丰富的人,虽然,表面上他不爱言辞。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的《云雀高飞》(The Lark Ascending),我在剑桥大学音乐系的一次音乐会上偶然听到,由一位年轻的韩裔女小提琴手独奏,感动不已。跟约翰斯谈起来,他接着就说,噢,沃恩,他的音乐养分很多汲取自英国的民间音乐,他是我们最后的最伟大的音乐家。他又建议我听贝多芬的Pastoral(《田园交响曲》),大概他感觉我偏爱田园风格吧。他很乐意回答我诸多问题,甚至连为什么乐谱符号都很不“英文”这样的低级问题,他也谦和地告诉我:因为它们都源自意大利,因而都是意大利文。他脸上的笑意,略带兴奋的表情,似乎都在说:涉及到艺术文学一类喜欢的话题,他是可以并且享受侃侃而谈的。那时我只恨自己音乐修养太浅,不能跟他有更多深入的交流。
约翰斯有一个习惯,不良习惯——吃饭看书。好多次遇到这样的场景:冬日的夜晚,橘黄色灯光下,房间里安静温暖,珍姐外出,约翰斯一个人在餐桌前,眼前有食物在白色西餐盘里,视线则朝向左前侧的折叠式木质书挡——他津津有味地看着书,不急不慢地夹着食物。来客进入家里,他亦浑然不觉。他读哈代的《远离尘嚣》,也读巴尔扎克法文原著……
说到餐食,约翰斯不怎么爱中餐,倒是偏爱炒鸡蛋,另外红酒一杯每餐必配。珍姐呢,则大盘小碟,汤汤水水的中国菜。他们多年相处之道,拿珍姐的话来说就是:互不干涉,互相给予对方充分自由。约翰斯不会烧饭,洗碗是他的“专项”。倘若听到热烈奔放的歌剧绕梁,那一定是他在厨房劳动——听到过他唱《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欢快喜庆,让你不会太boring(枯燥乏味),约翰斯这么说。
音乐之外,对约翰斯来说,不可或缺的另一项活动是“做花园”。这是珍姐的英粤夹杂式叫法,珍姐祖籍广东佛山,她的父亲年轻时在上海学医,后行医越南,并在那里娶妻生子。珍姐的普通话,是跟家里的中国租客学来的,日常够用,谈不上标准。都说英国园艺水平世界第一,英国人视花园为自己的第二生命,事关颜面。此言非虚,约翰斯就是这样。珍姐说过,打理花园,都是老公做,听起来很浪漫,但实际很费气力,很花时间。看看花园里的工具,推车、铁锹、水管,一应俱全,再看看着工装推起一车土往花园深处走去的约翰斯,就明白了。

他们家的大花园,长约百米,宽约五十米,约翰斯打理得井井有条,四季有花,美轮美奂。花园中央,有三四株三十多年树龄的苹果树,从开花到结果,到七、八月份硕果累累压弯枝头,很多来不及摘就落了地。珍姐送我一大袋,拌沙拉熬果酱,让我忆起小时候的苹果味道。花园远处一角,有小菜园,种了南瓜、上海青等绿叶菜,或许是借此慰藉珍姐的乡愁吧。当然,更多的是各种美丽的花,春日里的黄水仙白水仙、粉的紫的大瓣罂粟花(观赏品种)、大红的明黄的玫瑰和郁金香,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错落有致,装点着花园,真是美不胜收。
每个礼拜日,约翰斯都去市中心圣约翰学院旁一家小教堂弹管风琴。想来,弹琴与侍弄花园,是他生命中须臾不可离的组成部分。而他的生命,在半生悉心守护的精美花园戛然而止,或也是最恰当慰人的归处吧。
在一般世俗眼光看来,约翰斯不属于“成功人士”,他不过是当过英文老师——他们夫妇即相识于同租住于一栋公寓时,因约翰斯辅导珍姐英文结缘,兼职教堂风琴师。然而,他属于英格兰。他身上有真正的英格兰精神: 做事专注而严谨,热爱生活,坚守自我。他不用手机,外出就打工作电话,没有其他可能。手机不在他的世界,他不怕“与世隔绝”。他似乎“过了时”,像上个世纪的人。可谁又能说,他的世界不是充盈而饱满?
本文刊于2017年8月8日《文汇报 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