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十部长篇新作
观江西文学气象
不久前,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作家出版社、江西省作协合作实施的“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结出硕果——10部江西优秀长篇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引发了媒体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今天,我们请到几位嘉宾,来聊聊这十部小说中所呈现和兆示的江西文学气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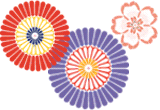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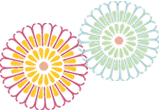

主持人:李滇敏
嘉 宾:
江 子江西省作协驻会副主席
宋清海《白骏马》作者
温燕霞《珠玑巷》作者
阿 袁《上邪》作者
丁伯刚《斜岭路三号》作者
王 芸《对花》作者
杨 帆《锦绣的城》作者
樊健军《诛金记》作者
贺贞喜《鸳鸯茶》作者
白 勺《姑妈的沧海》作者
刘建华《立春秋》作者


“四世同堂”的
江西小说方阵
主持人:
对一个省一种专门的文体创作、出版进行扶持,这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历史上尚属首次。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关注到江西这片文学土壤?
江子:
2015年5月,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到江西开展文学专题调研。通过调研,何建明认为,江西有着璀璨的历史文明,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江西文学创作资源极其丰富,如绿色山水、景德镇瓷器、革命历史等,都是具有独异性的文学资源;江西的生态资源也非常好,这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性的文学主题。江西文学的发展需要与全国文学资源对接,需要提升江西作家的影响力。经中国作协党组研究,决定重点支持江西长篇小说创作,为江西作家出版和推介10部优秀长篇小说。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更多的江西作家,深入到生活的富矿中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促进江西长篇小说创作以及江西文学的整体繁荣。
“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从2015年开始,由江西省作协组织江西作家创作10部长篇小说,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作家出版社)出资133万元,进行出版和推介。小说内容不拘,力求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能代表江西近年来最好的长篇创作水平,有面向中国文坛推广的价值。
活动开始前,省作协就组织召开了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开展重点作品选题的征稿活动,鼓励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确定重点扶持项目等,全面掌握了我省长篇小说创作的“家底”。征稿通知发出后,74位作家提交了选题。经省作协组织专家初选和资格认定,67个选题成为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第一阶段评审的备选选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组织专家对67个选题进行评审,评出15个选题。
之后,经过多次作品改稿会,2016年11月初,评审委员会对入选作家完成的作品进行评选,最终评出阿袁《上邪》、宋清海《白骏马》、温燕霞《珠玑巷》、王芸《对花》、杨帆《锦绣的城》、丁伯刚《斜岭路三号》、樊健军《诛金记》、贺贞喜《鸳鸯茶》、白勺《姑妈的沧海》、刘建华《立春秋》,共10部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入围作品。
主持人:
这些作品能否反映江西长篇小说创作甚至江西文学的发展生态?
江子:
我是这么看的,首先它体现了江西的文化特点和题材类型:一是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份榜单中占有重要位置。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一直被称为江西文学的富矿,也是构成江西文学新传统的重要源泉,在10部长篇中,这一江西文学创作母题有了重要体现。宋清海的《白骏马》,写的是方志敏。
二是江西传统文化的反思主题在这份榜单中十分醒目。王芸的《对花》,是对本土戏曲传承中人的命运和情感的书写;刘建华的《立春秋》,是对辛亥革命时期江西乡村嬗变的记录;贺贞喜的《鸳鸯茶》,在江西茶文化的背景下展开人物冲突及命运轨迹;温燕霞的《珠玑巷》,追溯客家民系的历史,刻画客家民系的精神。
三是从这份榜单看,对现实的关照和记录已经成为江西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阿袁的《上邪》,杨帆的《锦绣的城》,丁伯刚的《斜岭路三号》,樊健军的《诛金记》,白勺的《姑妈的沧海》,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或揭示当今时代对物质追逐过程中迸发出的人性张力及导致的人性迷失,或表达对女性命运的思考,或探索人性 救赎的可能,或展示当下知识分子的困境与人文精神的失落……
主持人:
我们也惊喜地发现,这是一份“四世同堂”的名单。
江子:
是的,这份作者名单真实反映了江西文学队伍梯次形态。其中,既有曾经以《馕神小传》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上世纪40年代后期出生的老将宋清海,也有成为江西文坛中坚的60后 作家,如获得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红翻天》《夜如年》等长篇小说的温燕霞,在《收获》《当代》等发表大量中篇小说的丁伯刚,曾多次获《十月》《小说月报》文学奖、以高校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精神为题材的阿袁,以长篇小说《天宝往事》在江西长篇小说征集评选中获奖的刘建华,在《北京文学》《大家》等 发表中篇小说的白勺;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这份名单中亦有相当大的比重,王芸、杨帆、樊健军都以较为丰硕的文学创作成果占据了江西文学的高地。作为唯一的80后作家,贺贞喜已经有多部长篇小说出版。

对革命历史题材
进行深度挖掘



主持人:
正如江子所说,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一直是江西文学的富矿,也是构成江西文学新传统的重要源泉。但是如何在富矿里“炼金”,把资源优势变成写作优势,写出与富矿相对称的精品力作,仍是江西作家必须面对的课题和努力的方向。宋老师您怎么会想到写方志敏?
宋清海:
我对方志敏的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限于他的狱中遗著《可爱的中国》。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方志敏及红十军被国民党军围困于怀玉山、红十军团全军覆没以及方志敏被俘的故事,又因为这个故事产生了了解方志敏创建赣东北根据地的历史的强烈愿望。于是,我了解到党史、革命史和民间口传历史中的方志敏。将这三者合一,便是我所写的方志敏的文学形象。
虽然《白骏马》中方志敏的形象来源于党史、革命史和民间口传历史,但我并不“戏说”方志敏,只在“虚实”二字上下功夫。“虚”是指人物内心世界,“实”是指当时的实史。史实不虚,是方志敏故事的坚实舞台。人物内心世界的“虚”不同于虚构,是对人物内心的深入开掘,这开掘又指向人物的精神内核,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使史实焕发新的认知光彩,使人的精神成为历史永存的价值。
当然,从构想到实现总是有距离的。其实,我的走出并未有多远。
主持人:
几年前我读到过您写的《石瑛传》,今天又读到了《白骏马》,前者写的是辛亥革命元勋、国民党元老石瑛;后者写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方志敏,您怎样处理这种“跨越”?
宋清海:
历史的是非最终都升华为文化的价值,历史人物的行为、思想最终都升华为精神的价值,历史的不朽之光总是人的精神。在此意义上,石瑛和方志敏在精神文化传统上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石瑛在清末中举后不去考进士而去西方留学,学习振业救国的新学,方志敏在失学后参加国民革命;石瑛在海外追随孙中山组建同盟会,回国后遭袁世凯通缉,逃亡西方再留学,方志敏在大革命失败后逃回家乡创建根据地;石瑛的清廉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方志敏的清贫情操与他的《清贫》一样不朽……
总之,石瑛和方志敏在文化精神上是一致的,都具有强烈的传统士大夫风骨,他们的精神其实都滋养于中华传统文化。表现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作品,若不能发现其超越的文化精神价值,在思想意义上终是个失败。


在传统文化里
挖出深深的井
主持人:
江西有红色文化,也有很多别具特色的“古色”文化。10部作品中,有4部体现了对本土文化的关注。这也是江西作家近些年在传统文化里“挖井”的收获。这其中,王芸的《对花》非常敏锐地关注到了地方戏曲的命运。
王芸:
为了创作这部小说,我花了一年多时间跟访了南昌县采茶剧团从排演到演出传统剧目《南瓜记》的全过程,采访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昌采茶戏的代表性传承人、采茶戏名角魏小妹(魏筱妹),和剧团的老演员、年轻演员聊天,我通过镜头记录他们不自觉的神态和瞬间,通过笔记录他们的经历和感受。通过采访,我了解了采茶戏和采茶戏演员的真实境况。
戏曲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极富魅力的、应该被珍视和传承的部分,之中隐藏着我们精神生活的线索和依据。近些年,国家不断加大对传统文化的扶持力度,就是旨在存续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因子。



主持人:
你的目标是“不只是写出那些戏曲表演者对艺术的痴迷与执着,还有他们在时代流变中面临一个个人生路口时做出的选择,于中展现出的复杂而微妙的人性”。
王芸: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微观的探测。宏观是指50年的跨度,对两代采茶戏演员所代表的一个群体,在时代变迁中的复杂命运的表现;微观是指对人性中明暗凸凹、跌宕起伏的准确细切的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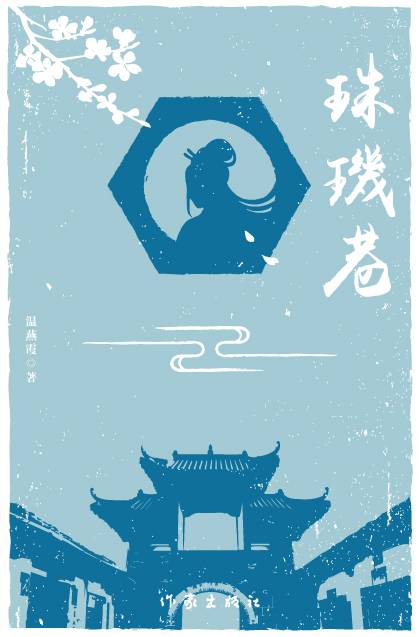

主持人:
擅长写赣南客家题材的温燕霞,这次把笔触延伸到了赣南以南的珠玑巷。
温燕霞:
小时候,我家隔壁住了一个南雄籍的阿叔,从阿叔那里,我晓得了古时候曾有100多姓人从珠玑巷迁往广州一带开基立业,便对珠玑巷生出几分神往来。在2002年到2008年间,我利用节假日先后5次前往珠玑巷探寻历史足迹,感受作为广府人姓氏发源地和客家人中转站的珠玑巷的脉动与呼吸。后来,我在长篇散文《我的客家》中抒发了我对珠玑巷的感受。珠玑巷知我心事,渐渐地将自己修炼成一颗镶嵌在我的记忆中熠熠发光的珍珠,让我无法漠视和忘怀。
小说《珠玑巷》的创作缘于朋友傅菲的一个电话。他问我愿不愿意写一部反映珠玑巷历史的小说,我说珠玑巷我很熟悉啊。正巧不久后又逢珠玑巷召开第二届姓氏文化节,我受邀前往,目睹了珠玑巷作为广府人姓氏文化发源地而享有的威望,也看到八方游子寻宗敬祖的崇敬与渴盼之心。在南雄市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我再次参观了古村、贵妃塔、姓氏祠堂等地,其间听闻了胡贵妃南逃珠玑巷和罗贵率众南迁的传说。现时的珠玑巷与800多年前的珠玑巷在我脑海中碰撞出铿然的回音。我知道,那是创作灵感的召唤、是先祖灵魂神秘的呼喊:我虽非广府人,可珠玑巷也是客家人的中转地之一,况且,随罗贵南迁的33个姓氏中也有温姓族人!于是,就有了小说《珠玑巷》的创作。



主持人:
贺贞喜的《鸳鸯茶》以民国初期一个封闭的乡村为背景,“展示了辛亥革命后清新空气的拂入和封建传统社会的瓦解”。让我吃惊的是,作为一名80后作家,她给自己的作品赋予如此深刻复杂的意蕴。
贺贞喜:
开始并没有想太多,只是有一次到沈家大院旧址听闻了一些老故事,迸发了灵感,于是慢慢构思。时间背景的设定也是再三修改,最后选在五四时期,有些隐喻的意味。我没有特意去挑战,但是思考的过程确实很长。



主持人:
我想,对于贺贞喜,《鸳鸯茶》的被认可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她通过这部作品的写作完成了网络小说作家向纯文学作家的转型。这是否也给了更多网络作家一个启示,年轻作家要想艺术之树常青,最终还是要更多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和灵感。
赣西小县宜丰是刘建华的“奥克斯福”,从几年前的《天宝往事》到《立春秋》,她的笔从没离开过那片土地。
刘建华:
我对“本土”的迷恋来源于对过去一些大家族的了解和研究。我的上代祖先炼世公拥有“鸦飞不过”的田庄、山林,土纸产业遍布湘鄂赣三省,产出的土纸曾经支撑洛阳纸市半壁江山。但他非常节俭。传说有一天,炼世公在垃圾池发现一个几近完整的熟鸡蛋壳,竟然拄着拐杖骂了半天。他生气的是家族里出现了某个人独吃一个鸡蛋的现象——不然怎么会有一个完整的蛋壳扔在垃圾里呢?据说老人家就是从这个鸡蛋壳里,看出了家族衰败的征兆:不要小看一个鸡蛋,鸡蛋原是孕育盘古的!
诸如此类的家族往事不胜枚举,作为一名写作者,我能从中发现通往小说的路径——根本用不着虚构,因为往事本身早已自成皇皇巨著。只要顺着这样的细节群追寻下去,你看见的是一个个横空出世、开天辟地的盘古——这不是小说是什么?

当代题材的创作
有了长足进步



主持人:
当代现实题材的写作既考验作家解读社会与时代的能力,也考验作家直面现实与人性的勇气。近些年,随着阿袁的小说在各大文学期刊频频以头条方式亮相并获得读者的广泛共鸣,丁伯刚的中篇小说不断在《收获》等重量级期刊推出,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上,江西小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
《上邪》中,阿袁延续了她擅长的题材——大学校园里知识分子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这是阿袁小说的“招牌菜”,她写的是爱情,也是人在爱情博弈中的丰富人性。
阿袁:
世上最美的,莫过于风花雪月。但如果这世上有比风花雪月更美的东西,那就是爱情——也只有爱情,我以为。
看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那真是一个美妙无比的过程,比芙蓉初开更美,比白雪轻舞更美,看一辈子,也看不厌。
这是我写《上邪》的缘由。
乐府《上邪》里的爱情,本来是“长命无绝衰”的,而《上邪》里孟渔对朱茱的爱情,一下子就衰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篇祭文,祭奠现代人早夭的爱情。
马尔克思在《霍乱时期的爱情》结尾说:原来是生命,而不是死亡,才是永恒的。也就是说,爱情的每一次衰败,都是另一次初生。



主持人:
丁伯刚是个经典意识很强,因而惜墨如金的实力小说家。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他通过《斜岭路三号》的写作、出版完成了从中篇到首部长篇的跨越。
正如评论家张定浩对丁伯刚的印象:在写作《斜岭路三号》之前,“丁伯刚一直致力写他的中篇,在三到五万字的篇幅里,他如春蚕吐丝般,缓慢而结实地营造出赣皖交界处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世界。这些世界谈不上迷人,却真实可触。”“假使以音乐为喻,丁伯刚的音域并不宽阔,但他对于这个狭窄而有局限的音域本身有着惊人的敏感。”在《斜岭路三号》中,丁伯刚通过陈青石这个人物把自己的人性探索延伸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丁伯刚:
因为所读书籍的影响,一段时间里,我的写作围绕着两个主题展开:第一个,拜伦式英雄,比如此前所写的中篇《天杀》。后来,人成熟了些,对现实的感受也更真实强烈些,不知不觉间进入另一个主题,受难式英雄。人世的苦难无处不在,但是对苦难的强烈感受和反应,往往更多存在于某种敏感者身上。在小说中,我非常愿意选取这样一些敏感者,比如底层读书人、知识分子作为书写对象。他们地位卑下,虚弱不堪,感受力却最强,心灵处于最佳敞开流动状态,与现实与周围的世界息息相通。他们才是真正的承担者,是一种被选定。他们就是我所以为的受难英雄。
至于《斜岭路三号》,在具体展开受难英雄这个主题时,多少发生了一些偏离和变异。主人公陈青石并不像我一般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是苦难的体现者、承担者,他无意之中被拖入更深的苦难之中,反倒以救助者的面目出现了。有一度陈青石也为自己无意中获得的新身份而激动,真的想扮演好这个角色。我一点也不知道,施救与被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不知道在人类潜意识里,施救者到底又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这样一种身份,到底又具备一种什么样的魔力?



主持人:
《锦绣的城》里,杨帆提出了一个“清洁”的主题,并给读者一个“奇迹”的想象。
杨帆:
我想写一些失意的人,或者说失败的人。他们处在社会边缘,没有地位、没有话语权、没有牢靠的保障,有的没有正当职业,比如这部小说里的小偷牛丽。这种失败是通常观念里的定义,道德评判也将他们划入人性的废墟里。假如连旁观者、读者、甚至作家都这样认定,那么他们当然处在巨大的精神困境中。这里面包括社会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对人生遭遇的态度,以及他们的抉择和重建,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疑难和挣扎。
事实上,我们同他们是一样的人。甚至我不如他们,在谋生技能这一块,我肯定比不上他们的勇气、智慧和花样。
除了小偷,我还写了大学生、教授、生意人。这些人各有自己的隐疾、痛处,各有各的困境,是什么造成了奇迹的发生?抢劫犯爱上大学生,小偷成为大众明星,失去童贞的女生走上朝圣之旅,种种奇迹,看似不可能、实则是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的存在。我在这部书里企图呈现的,与冒险有关,废墟里开出的花朵,沙砾掩埋的珍珠,雨水里的彩虹,这些又是这世上再平常不过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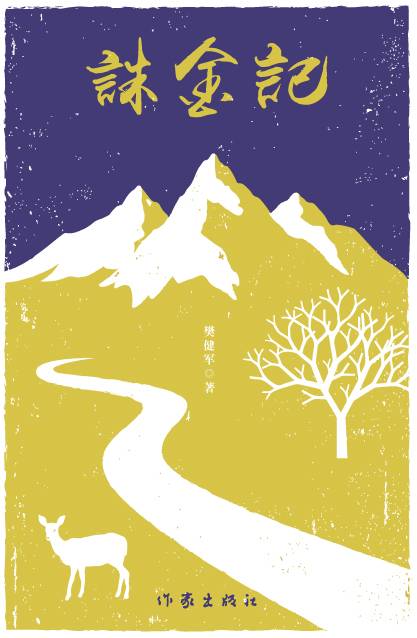

主持人:
《诛金记》讲述了一个关于黄金财富的荒诞故事,让读者很容易联想到我们所处的当下,人们对财富无节制的崇拜和追逐。
樊健军:
我的老家是幕阜山腹地的王桥村,依傍着一座叫土龙山的大山,长江的一根细小支流穿村而过。河流及其沿岸的田地中藏有沉积金,王桥村及邻近河流的村庄素有淘采沉积金的历史,当地流传着许多淘金的故事。我就在黄金的神奇的传说中长大。
1986年的秋天,土龙山发现了金矿,后来在王桥村周边的许多山头上都发现了类似的金脉带。淘金的狂潮席卷了我的家乡。
我有过三段在土龙山上淘金的经历,见证过淘金场面的疯狂,也目睹过塌方夺走人命的惨状。我遭遇过一次塌方,碎石埋住了我的身体,幸好同伴们抢救及时,才逃脱一劫。可是,有不少淘金客,由于无知和缺少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落下了矽肺病,老家所在的那个乡镇曾一度被外界称为“寡妇乡”。他们最后的呻吟令我悲悯、颤栗,而又绝望。
这段经历成为梦魇,我逃无可逃。2013年,我终于鼓起勇气面对困扰我的那些梦境。于是有了《诛金记》。



主持人:
《姑妈的沧海》也写了爱情,写了那个时代一群女子的情感和命运。
白勺:
在这个跨度为个人半生的复杂叙述里,我想表达一群人在命运面前无计可施。当他们走进那个时代,命运便击中了他们,使他们颤抖、错乱和窒息,而且无一幸免。命运把他们抛来抛去,还嬉笑不止。在这里,我又想表达对爱的执拗和坚守。这种爱,现在看来也许荒诞可笑,这如被压在巨石下面的种子,它会绕过压迫想方设法站立起来,让我们看到它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当然,我还想表达泪水的咸度,表达某种担忧,表达人性里暖暖的体温,表达原谅的美,表达绝望之中的一丝亮光等等。

到生活中去
到人民中去
主持人:
这样的一个文学扶持工程对江西文学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江子:
一是,江西作家的努力及江西作协近年来在扶持长篇小说创作上所花的功夫没有白费,江西长篇小说创作得到了整个文坛的关注;二是,江西长篇小说创作水平得到了整体提升。通过实施这一工程,以及举办评审会、改稿会、研讨会等活动,我们的作家与优秀的有影响的文学编辑、评论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们的作品也在一次次对话中进行了修改,质量的提升肯定是明显的,而且这种对话,将会使作家们长久受惠,从而会对我省长篇小说创作产生深远影响。三是,这一工程的成功实施会进一步优化我省的文学创作氛围,鼓舞我省从事其他文学门类的写作者,心怀更大目标,向着中国文坛发起冲击;四是,会进一步鼓励我省作家把目光投向本土文化资源,并且饱含现实关怀,写出具有时代洞察力与文化情怀的作品。
主持人:
文学创作源自作家自觉,也需要各级文学主管和服务部门的扶持和引导。相信通过更多类似的扶持和引导,广大江西作家一定会以更饱满的热情地投入到生活中去,扎根到人民中去,努力写出既具有江西气质,又具有广阔视野的精品力作,实现江西文学的整体突破,形成令人瞩目的文学气象。
(转自江西日报文化赣鄱微信公众号)
尊敬的畅言客户,您好。您所使用的网站评论功能已广告作弊被限制使用,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电话400-780-9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