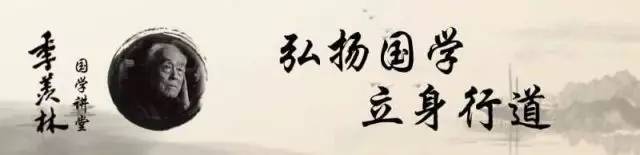

今天是2017年8月9日,是饶宗颐先生一百周岁的生日。饶宗颐先生与季羡林先生相识相知几十载,并称“南饶北季”。今天我们向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季羡林先生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写的序言,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好地了解饶宗颐先生的治学为人,同时借这篇文章向饶宗颐先生的生日献上真挚的祝贺!
《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
季羡林 | 文
饶宗颐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台湾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
几年以前,饶先生把自己的大著《选堂集林•史林》三巨册寄给了我。我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文章,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大陆的同行中,我也许是读饶先生的学术论著比较多的。因此,由我来介绍一下饶先生的生平和学术造诣,可能是比较恰当的。中国有一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使我不介绍,饶先生的学术成果,一旦在大陆刊布,自然会得到知音。但是,介绍一下难道不会比不介绍更好一点吗?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不避佛头着粪之讥,就毅然答应写这一篇序言。

饶宗颐先生
饶宗颐,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安人,幼承家学,自学成家。自十八岁起,即崭然见头角。此后在将近五十年的漫长的岁月中,在学术探讨的许多领域里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至今不衰。饶先生的著作涉及的面很广。根据饶先生自己的归纳,分为八个门类:
一 敦煌学
二 甲骨学
三 词学
四 史学
五 目录学
六 楚辞学
七 考古学、金石学
八 书画
饶宗颐教授的学术研究涉及范围之广,真可以说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想对这样浩瀚的著作排比归纳,提要钩玄,加以评价,确非易事,实为我能力所不逮。因此,我只能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饶宗颐与季羡林2000年在北大合影
从世界各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进行学术探讨,决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是必须随时应用新观点,使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摸索新方法。只有这样,学术研究这一条长河才能流动不息,永远奔流向前。讨论饶先生的学术论著,我就想从这个观点出发。
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大转变时期,一个空前的大繁荣时期。处在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学者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投身于其中。陈寅恪先生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寅恪先生是季羡林的老师
陈先生借用的佛教名词“预流”,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名词。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王静安先生是得到预流果的,陈援庵先生是得到预流果的,陈寅恪先生也是得到预流果的,近代许多中国学者都得到了预流果。从饶宗颐先生的全部学术论著来看,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也已得到预流果。
谈到对饶先生学术成就的具体阐述和细致分析,我想再借用陈寅恪先生对王静安先生学术评价的几句话。陈先生将王静安先生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归纳为“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先生列举的三目,我看,都可以应用到饶先生身上。

一位学养深厚的老人
一、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
饶宗颐教授在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他对中国的纸上遗文非常熟悉,了解得既深且广。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国内的考古发掘工作。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简直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地下发掘出来的死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往往变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再加上他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挥若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术刊物,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而饶先生则无不注意。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饶宗颐先生在作画
二、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
饶宗颐教授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一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中外关系的研究基本上也属于这一类。在饶先生的著作中,中外关系的论文占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尤以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更为突出。如在《安荼论与吴晋间之宇宙观》一文中,饶先生从三国晋初学者,特别是吴地学者的“天如鸡子”之说,联想到印度古代婆罗门典籍中之金胎说,并推想二者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
除了中印文化关系以外,饶先生还论述到中国在历史上同许多亚洲国家的关系。《早期中日书法之交流》这一篇论文,讲的是中日在书法方面的交流关系。《说诏》一文讲的是中缅文化关系。《阮荷亭〈往津日记〉钞本跋》则讲的是中越文化关系。

饶宗颐先生书画作品
三、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
我在这里讲的外来观念是指比较文学,固有材料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饶宗颐教授应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源流,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有很多启发。
在《〈天问〉文体的源流》一文中,饶先生使用了一个新词“发问文学”,表示一个新的概念。他指出,在中国,从战国以来,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天”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有些学者对于宇宙现象的形成怀有疑问。屈原的《天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出来的。在《天问》以后,“发问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支流,历代几乎都有摹拟《天问》的文学作品。饶先生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种“发问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经典中都可以找到这种文学作品。他引用印度最古经典《梨俱吠陀》中的一些诗歌,还从古伊朗的Avesta和《旧约》中引用了一些类似的诗歌,以证实他的看法。饶先生在这一方面的探讨,是有意义的,有启发的,值得我们认真注意的。

2000年北大学术商讨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周一良、季羡林、饶宗颐、任继愈。
饶先生治学方面之广,应用材料之博,提出问题之新颖,论证方法之细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归纳起来说一说的话,我们从饶宗颐教授的学术论著中究竟得到些什么启发、学习些什么东西呢?我在本文的第一部份首先提出来一个重要的问题:进行学术探讨,决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必须随时接受新东西。我还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预流果”这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在这里再强调一遍:对任何时代任何人来说,“预流”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预流,换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预流,就会落伍,就会停滞,就会倒退。能预流,就能前进,就能创新,就能生动活泼,就能逸兴遄飞。饶宗颐先生是能预流的,我们首先应该学习他这一点。

“南饶北季”世纪会面
预流之后,还有一个掌握材料、运用材料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进行学术研究,掌握材料,越多越好。材料越多,在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方法的指导下,从中抽绎出来的结论便越可靠,越接近真理。材料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往往囿于旧习,片面强调书本材料,文献材料。这样从材料中抽绎出来的结论,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与狭隘性。我们应该像韩愈《进学解》中所说的那样:“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畜,待用无遗。”我在上面已经多次指出,饶先生掌握材料和运用材料,方面很广,种类很多。一些人们容易忽略的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都被派上了用场,有时甚至能给人以化腐朽为神奇之感。这一点,我认为,也是我们应该向饶先生学习的。

饶宗颐到301医院看望季羡林
中国从前有一句老话:“学海无涯苦作舟。”如果古时候就是这样的话,到了今天,我们更会感到,学海确实是无涯的。从时间上来看,人类历史越来越长,积累的历史资料越来越多。从空间上来看,世界上国与国越来越接近,需要我们学习、研究、探讨、解释的问题越来越多。专就文、史、考古等学科来看,现在真正是地不爱宝,新发现日新月异,新领域层出不穷。今天这里发现新壁画,明天那里发现新洞窟。大片的古墓群,许多地方都有发现。我们研究工作者应接不暇,学术的长河奔流不息。再加上新的科技成果也风起云涌。如今电子计算机已经不仅仅限于科技领域,而是已经闯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藩篱。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再也不能因循守旧,只抓住旧典籍、旧材料不放。我们必须扫除积习,开阔视野,随时掌握新材料,随时吸收新观点,放眼世界,胸怀全球;前进,前进,再前进;创新,创新,再创新。愿与海内外志同道合者共勉之。
1984年9月10日
时为旧历中秋,诵东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句,不禁神驰南天。
(节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