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都希望生活是充满爱和善的。但似乎随便哪一天点开新闻,事实就会告诉我们绝非如此。
比如,杭州保姆纵火案中的几位受害人,是那么的无辜,却遭此噩运失去了生命;比如,近几天刚刚宣判的中国留学生李洋洁在德国被害案,让人惊悚于看似安全平和的国度里,有如此穷凶极恶的凶手……
更可怕的,是我们无法预知到这样的恶的发生,也通常没有办法为它们找到“理由”。出于对一种“公正世界”的想象,有些人会设想受害人曾做错了什么才会有之后的遭遇——这是为了维护自己心中脆弱的安全感。
所以,什么是恶?人性中本身就有恶的成分吗?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恶?许多年来,人们都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同样,在文学中,作家们也试图表现和深度剖析这一问题。
今天书评君去文学中寻找人性之恶的存在和存在方式。毕竟,恶太难直面了,文学用虚构建立一道屏障,也许反倒能帮我们触及更本质的真实。
撰文 | 宫子
离经叛道,未必是邪恶
罪恶,堕落,邪性,这些主题在文学中经常出现,这类作品一反读者对经典作品“崇高优雅”的认知,转而表现人类社会的黑暗角落。但大多数以“恶”的形式所塑造的作品,都有些“色厉内荏”的感觉,尽管它们形式上的离经叛道让社会恐慌不安,仿佛一本本“罪恶教科书”,这些涉及堕落、吸毒、性交、谋杀的作品都曾遭遇过封禁,被视为伤风败俗的洪水猛兽,可实际上,它们却是假邪恶,真崇高。艺术家大刀阔斧的革新表现,让人性雕塑的切面极为丰富地展现出来。
这其中,比较经典的一本书是《猜火车》。单从生活内容来看,《猜火车》里的小伙子们几乎毫无理想可言,每天吸毒、抢劫、做爱,生活极为泥泞,有时候在卫生间的马桶里翻搅半天就为了找到掉落的毒品,晚上喝高了直接在床单上呕吐排泄,浑身屎尿——欧文·威尔士用大幅笔墨渲染这种肮脏污浊的环境,如果说凯鲁亚克的散文化语言还有浓厚诗意的话,威尔士的作品则俚语遍布,线条粗犷。

《猜火车》
作者:[英] 欧文·威尔士
译者:石一枫
版本:重庆出版社 2012年12月
他给人物依次取了“屎霸”“变态男”“卑鄙”这样的名字,整个故事也极为混乱,互相欺骗,抢劫,背叛,搞毒品,最后各自分散。从这群不良青年的故事中我们读不到任何有积极启示的东西,它看起来就是一本引诱青年堕落的教科书,大量段落读起来还会产生感官不适……但他们属于人性深处的那种邪恶吗?恐怕无论是否喜爱这本小说,人们都不会用邪恶来形容这群不良少年,读者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失控的激情,打破日常秩序的放浪不羁。这种激情渲染本身就如同一针兴奋剂,让《猜火车》的众多粉丝感受着生命的强劲冲击。
欧文·威尔士的风格还是偏向现实的。相比之下,安吉拉·卡特则把黑暗与邪恶的题材发挥到极致,糅合了魔幻、潜意识、超现实、童话等元素,每一篇小说都笼罩着浓郁的黑色烟雾,读者想在其中寻觅一盏微弱的路灯,却发现那灯光明灭不定,使小说的道德氛围更加恐怖。从《焚舟纪》到《爱》,从《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到《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包括她收集改编的《精怪故事集》,都一改传统民间故事讲给小孩子听的定位,充斥着血腥,恐怖,粗俗。她是个会用“玻璃镖射入人的眼球”来描写阳光的哥特作家。但在黑暗与血腥之外,安吉拉·卡特的小说离真正的邪恶似乎差得很远,即使有大量阴森恐怖的段落,象征邪恶的符号,她的小说也只是一场迷幻的噩梦。合上书,万物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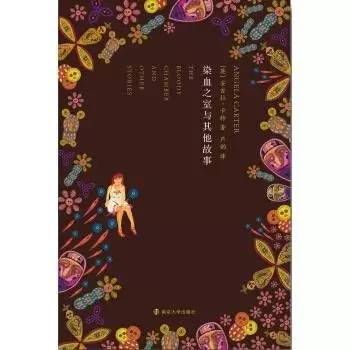
《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
作者:[英] 安吉拉·卡特
译者:严韵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侦探小说里,邪恶的“创伤根源”
荒诞阴郁的小说虽然情节叛逆,但只是营造形式上的邪恶感,而侦探小说则追溯邪恶的创伤根源。
每个侦探小说家在刻画五花八门罪行的同时,也致力于揭示罪恶的迷雾,小说的精彩程度便取决于真相大白时二者的张力。在侦探小说中,借助心理分析,邪恶开始从形式走向精神内核。
爱尔兰小说家约翰·康奈利属于冷硬派作者,在《无耻之徒》中,他塑造了一批真正的杀人狂,几个匪徒帮助首领摩洛克越狱,接着沿路随意杀人,毫无动机,有时直接用刀砍下路边司机的头颅;最后小说依然回溯到了这些疯狂罪行的根源——摩洛克长途跋涉只是为了找一个女人复仇,其他“路障”都不重要。他在这个女人身上受到创伤,于是也把这种创伤施加给他人。

《无耻之徒》
作者:(爱尔兰)约翰·康奈利
译者:杨俊峰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3年5月
侦探小说为我们提供一条了思考邪恶的线索:从罪恶的结果(凶杀)开始回溯,让整个故事形成完整的链条,即使侦探没有抓到最后的凶手,但必须经由回溯让故事圆满地体现。在回溯后,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罪犯都有着“创伤心理”,在没有沦为“邪恶之徒”的时候他们也是普通人。这类精神创伤来源各异,但都没有得到及时的关注与解决,而是作为仇恨的种子埋在人的内心,渐渐酝酿邪恶。
不久之前,杭州发生了一起保姆纵火案。鲁斯·伦德尔曾经写过一个因由不同但结局相似的小说,《女管家的心事》,在小说最后,女管家尤妮斯杀掉了一家四口,而原因只是因为她是文盲,不认字,所以在生活中感到处处皆是隔阂与歧视;当然,在雇主的家庭里,这一切都被平静的水面所掩饰,他们每天照样说话,吃饭,打扫房间,但背后一切都充满恨意。缺乏交流,彼此互不信任,隔阂,忽视,这些都成为滋生邪恶的土壤。

《女管家的心事》
作者:(英)鲁斯·伦德尔
译者:郭金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2年5月
所以,更深邃的邪恶往往潜伏在平静的生活里。看似离经叛道的作品只是由激情和狂欢组成的言语,它们更像是单纯的审美;而当它不再依靠声响效果的时候,作品从“刺激性的邪恶”转向了“平静的邪恶”,人们才触摸到了最深邃的“人性恶”。而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是不要忽视,要小心平静水面下的暗流漩涡,很多时候我们身处其中,却并不自知。
最深的“人性恶”,往往藏于平静的生活
比利时作家乔治·西默农虽然也有一个侦探小说家的头衔,但他数量庞大的作品很难简单用“侦探悬疑”来概括,他其实是个描写生活随处可见的平庸之恶的小说家。如果说侦探小说是回溯型的精神分析,那么西默农就是在叙述邪恶的演变之源。
《黑球》描写了一种很常见的伤害:一个外来的男人搬入小镇,日夜辛勤工作,就是想要加入当地的乡村俱乐部,拥有一份平等的生活;但每次都被一个黑球(即反对票)拒之门外,因为是不记名投票,主人公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最后一次偶然,发现每年投放黑球的人居然是最亲密的朋友,他在酒吧用乡巴佬的语调讥讽自己。瞬间,主人公受到侮辱,所有生活期待都瞬间崩溃,他感到村镇的敌意与邪恶,并且,很难说不会采取相应的邪恶进行报复。

《侮辱》(收有《黑球》)
作者:[比利时] 乔治·西默农
译者: 徐健
版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6月
这类恶行大多时候是不经意的。我们在生活中能看到很多这类“排外”的例子,很多时候排异的人本身并非有意敌视,他们只是借助排异的手段来确立自身的安全感,例如,通过歧视他人并非本地人,来树立“我是个本地人”这样的概念;整个过程,他们从不感觉自己是“邪恶”的,这最多算个戏谑或玩笑。却没有意识到或许已经种下了邪恶的种子。
因为邪恶的平庸化,它就很可能成为群体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在其中的人便更不会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过错。美国小说家雪莉·杰克逊的《摸彩》就描述了令人屏气凝息的氛围。小说里的村镇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祥和安谧的气氛,村民用轻松又满怀期待的语气聊天,仿佛在准备一场庆典。最后,村子里各家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一起,大家进行一项名为“摸彩”的类似抽彩票的游戏,而“幸运儿”则被村民推出,绑在柱子上,被村子里的人用小石块活活砸死。整篇小说,到处可以听见村民的欢声笑语,即使在最后,村民们依然心情愉悦,认为这项仪式能成功给他们带来好运。

《摸彩》
作者:[美] 雪莉·杰克逊
译者:孙仲旭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1月
在《摸彩》中,邪恶不仅进入日常生活的范畴,它还被仪式化,成为一种信仰或价值信条。为了完成这个价值信仰,可以像萨特那样“脏手”,可以取途邪恶。在今天这个相对和平的年代,价值信仰之争便往往将事情带向邪恶,而非神圣。这个价值信仰可以包括民族,宗教,甚至正义——总之,任何未经反思或考量的价值观进入头脑都有可能导致邪恶。以宗教圣战为例,从中世纪到现代,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是正义而神圣的,然而,历史证明这些战争没有一场能够称得上“不邪恶”。恐怖分子也从来不会认为自己在做邪恶的事情,他们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去完成内心的信仰,自然,也不吝惜别人的生命;他们劫机撞击大楼的时候也从来不会想到死掉的是活生生的、同等的人,他们会认为自己在撞击“邪恶”。
所以,在邪恶的表现中,能看到它成型的蛛丝马迹。在邪恶行动者的眼中事物大多只有一种身份,人的多重性也被取消。在文学中,我们尚有理解罪犯的可能,因为作者会用几十万字的书来讲述。但小说外,我们只能通过千字左右的新闻报道来了解罪犯;想要在单薄的新闻中找到丰富的人性层次,去洞察人性恶,非常困难。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小说便在新闻事件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人性恶的内里。欧茨的许多小说,中等篇幅,不长,都改编自社会媒体的热点事件。通过大量搜集资料、调查,欧茨给单纯的媒体事件增添了丰富的张力。
《黑水》改编自美国政坛丑闻“查帕奎迪克岛事件”,一个参议员开车带着26岁的少女,结果发生车祸后他自己踩着少女的身体爬了出来,少女则死在车中。可以说,如果没有欧茨的改编,那么这起事件只会沦为一个丑闻,短期发酵,成为舆论热点,然后再也无人问津。但文学改编赋予了事件更丰富的层次,《黑水》阐述了很多对“人性恶”的思考,如车祸发生的一刹那参议员在想什么?他的行为到底算是生死抉择的本能还是人性本恶的反映?他属于单纯的虚伪,还是邪恶?这是一场永不停止的审判。

《黑水》
作者:[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译者:刘玉红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1月
所以,邪恶的复杂性就在于,我们只能无休止地讨论它,研究它,却无法给它作出定论或者设计一个杜绝邪恶的方案。因为邪恶的形态总是在变化,它可能惊世骇俗,也可能平庸无常,简单地去定义什么是邪恶会陷入历史上宗教审判的怪圈,以正义审判的态度制造另一种邪恶。
最深的邪恶需要敏锐的观察,也需要直视的勇气。它不像奇幻小说里弗兰肯斯坦,妖怪身躯,明目张胆;在现实中,我们也很难去做一个侦探,日夜追踪,能从头到尾解释一个罪行的来源与精神创伤;更多时候,邪恶就潜藏在生活的皮囊之下,寂静无声。文学中表现的各种邪恶,便是通过洞察与直观,向读者提供理解的可能;这种人文的关怀或许是抵御邪恶的唯一途径。关于“性善”和“性恶”的纷争,中国古代也早已有之,但比起把希望寄托于“性善”,我宁愿把邪恶视为体内天生的寄生虫,并时刻警惕它的一举一动。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宫子;编辑:小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
尊敬的畅言客户,您好。您所使用的网站评论功能已广告作弊被限制使用,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电话400-780-9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