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山小传
吴为山,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院长,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62年1月生于江苏东台。198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并留校任教。1990年至1991年在北京大学研修。1996年为欧洲陶艺工作中心高级访问学者。1997年至1998年为美国华盛顿大学美术学院高级访问学者,1998年回国任南京大学教授,创建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为宗教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三个方向的硕士生导师。2000年任香港科技大学文化讲座教授,获得首位“包玉刚杰出艺术家”荣誉。2002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获“龚雪因杰出学人”。2003年创建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并任首任院长。2007年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塑院院长、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主任。2009年文化部任命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曾获攀格林奖洛克菲勒首届中国艺术年度人物大奖。韩国仁济大学名誉哲学博士。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成员,英国皇家肖像雕塑家协会会员。2014年9月调任中国美术馆馆长。
“叩问天意”与“裹卷人气”
余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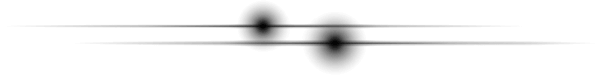
一
我初次与吴为山先生的雕塑相遇,是在哪里?很奇怪,不在北京,不在上海,不在南京,也不在苏州,居然在遥远的北方,山西大同。但似乎,这是冥冥之中的一个隆重安排。
大同有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其中最重要的五个洞窟是由一位叫昙曜的僧人主持开凿的,历来被人们称之为“昙曜五窟”。昙曜为千古云冈带来了最伟大的雕塑群,今天的云冈很想为他本人立一个雕塑,以雕塑褒奖雕塑,合情合理。然而遗憾的是,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没有留下有关他形象的点滴记载,只知道他是一位来自克什米尔地区的西域僧人。西域僧人?那就更加无法想象他长得什么样了。要为他立像,只能写意,也必须写意。因此,云冈呼唤了吴为山。
吴为山雕塑的昙曜,从前额、眉弓、鼻梁可以约略看出是西域人士,但显然又是充分汉化了的一位高僧。微微下垂的眼皮,表现出他的谦和坚贞,让人想到他在太武帝灭佛期间潜迹民间又不弃法衣的定力。但是,佛教又给了他通体超逸的风范,这一点也被吴为山表现出来了。
由昙曜的雕像我立即明白了写意雕塑的一大特性,那就是猜测。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猜测伟大。

猜测可能要借助于一些资料凭据,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动手雕塑的那个人。任何资料都不是作品本身,而且那些资料也带有传说的成分。只有当那个创造者的手动起来了,事情才正式开始。因此,我很重视“写意雕塑”的第一个字“写”。这个字,拉出了创造者本身,是他在“写”,像诗人写诗一样写出自己的猜测。“写意雕塑”常常被称之为“新意象雕塑”,我就不太赞成,因为那个最能体现个人创作主观性的“写”字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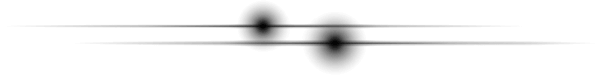
二
吴为山到云冈创作“写意雕塑”,实在是适得其所。因为,云冈是中国雕塑的圣地,却又不仅仅如此。
我说过,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千好万好,却不能按照他们的思路创建一个世界级的大唐。此间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家,都不知道除华夏文明之外,世界上还有别的文明。这个重大缺陷,由魏晋时代来弥补了,弥补的一个主要课堂,就是云冈。请看“昙曜五窟”和其他石窟中的巨大雕塑,集中传扬了来自华夏文化之外的佛教。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佛教的引入,使中国从“中国的中国”变成了“亚洲的中国”。
但是,梁启超先生不清楚的是,“亚洲的中国”中也包含着欧洲。这事需要绕远一点讲。
中国的佛教雕塑,主要来自于现在位于巴基斯坦的犍陀罗。在犍陀罗之前,印度的佛教很少有人物形象的雕塑。还是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的东征,给东方带来了希腊的雕塑艺术。他的浩荡军队里,夹杂着一些“文化军人”,那就是希腊雕塑家。于是,犍陀罗成了希腊雕塑和佛教经典融合之地。
说到这里,我请大家稍稍停顿一下,一起思考一个大问题。希腊哲学要传到东方,多么艰难,于是亚历山大让雕塑开路;印度佛教要转入中国,多么艰深,于是西域僧人让雕塑开路。雕塑,雕塑,它实在是移动的哲学、沉默的灵魂、无言的大师、先行的文明。以此来反观云冈,人们发现,那里的洞窟有希腊廊柱的堂皇门面,那里的佛像有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特征。再仔细看,希腊文明东征沿途上的其他文明,也一起捎带过来了,例如石窟里分明还有巴比伦文明和波斯文明的物件和图案。这也就是说,仅仅是云冈石窟里的雕塑,就汇聚了当时世界上各个重大文明的精粹。于是,华夏文明的边界打破了,诸子百家的局限超越了。因此,我要说,它既是雕塑圣地,也是精神圣地。
我在“昙曜五窟”西南面山坡上刻写了一则碑文:“中国由此迈向大唐”。这个石碑刻得很好,代表我日日夜夜表达着无限的崇敬。
我读到过不少美术论文,极言历史上中国雕塑的地位之低。我一读总是哑然失笑。心想这些评论家的目光不知出了什么问题。除了青铜器、三星堆、兵马俑、霍去病墓之外,雕塑,还曾经是中华文明大规模接受其他文明的最宏大、最直观的实体,也是最雄辩、最坚硬的见证。我觉得,一切雕塑家都应该去朝拜一下云冈,那里有你们最神圣的坐标。同时,也要顺便看一看吴为山雕塑的昙曜,那里有一条横贯几千年的文化缆索,蜿蜒在山坡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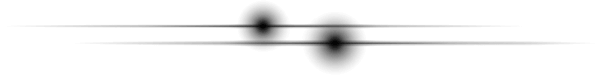
三
大同市出于对吴为山雕塑昙曜的信任,也引进了他雕塑的孔子和老子。
这两位先师,是我前面所说的不知道世界其他文明的诸子百家的领头人。虽然不知道其他文明,但他们把华夏文明的最高意蕴挖掘出来了。吴为山对孔子和老子的雕塑,远近皆知,比他对昙曜的雕塑出名多了。昙曜在云冈补充了他们,但他们自己也来到了云冈,因为他们毕竟是真正的老主人。
吴为山把雕塑孔子和老子,当作自己此生的首要文化使命。他雕塑的孔子和老子,又符合我对“写意雕塑”的概括:猜测伟大。
历史留下了孔子外貌的一些记述,但都简约、抽象,我觉得比较可信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他个儿比较高,身体不错。对于老子,则全是想象。
其实,后代人们对于孔子和老子的印象,全是精神性的,只是偶尔会衍生出一些“合理意态”,却并不追索太具体的形象。对于精神性的伟大,真实的具体形象反而会是一种遗憾,因为与常人无异的五官身躯及种种缺点会成为人们接受伟大精神的束缚和障碍。

在这方面,即使很像“写实”的古希腊哲学家的雕像,包括后来米开朗琪罗、罗丹等人对历史重大人物的雕塑,看似逼真,其实也是出于猜测。只不过,他们把这种猜测引向了模式化赋形,让雕塑对象成了一种哲学家、艺术家的模本,连发式、胡须、肌肉、衣袍都归入了一系列模型。佛像雕塑也走了近似的路,即让猜测走向模式化赋形。这样的雕塑,对于精神表达,很有局限。
对此,西方现代主义作出了大胆突破。现代主义雕塑不在乎逼真,更不在乎模式,只是竭力追求在抽象造型中的结构力度。这一来,逼真的外形也就框不住精神体量了,而抽象造型的结构力度反而会推动精神洪流的决堤奔放。
但是,吴为山站在孔子和老子的思维路线上,不主张“决堤”。他把现代主义的奔放之力,安置在近似写实的造型能力上,因此我们看到了笑容可掬的孔子和老子。但是,从线条的洒脱自由,到材质的强力呈示,都在提醒我们:这是一种暂歇于人体中的大意态、大风貌、大神采。
这里就出现了“写意雕塑”的另一个特性:意念越浩大,形象也越抽象,渐近“天意”。由此,“猜测伟大”,也就上升为“摹写天意”。
吴为山雕塑孔子和老子,就是在“摹写天意”。这样,“写意”二字也就不再仅仅在说一种风格,而是直逼艺术创造的极致状态,即“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中间的“人”,既是雕塑的对象,也是雕塑家自己。
出于“天人合一”的境界,在孔子和老子的造型中,就有大量自然元素介入。例如,从脸部到身体再到衣着,处处如山岩,如瀑布,如藤葛,如溪流。自然元素的不规整、不圆熟、不直拙等等特征,就这样生愣愣地闯入了造型,使造型更近于自然,更融入自然,毛毛糙糙,浑然天成。于是,孔子和老子也就成了苍茫自然的一部分,这也符合他们自己的终极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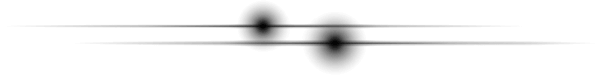
四
不错,吴为山是一个“叩问天意”的人。但是,仅此一面,还不是完整的他。他还有重要的一面,叫作“裹卷人气”。把“叩问天意”与“裹卷人气”加在一起,才是吴为山。
吴为山的家学渊源和诗文修养,使他常常孤独地思考着长天大地,但是,他并不是隐士、游侠。当他忧郁的眼神从长天大地收回,转一个身,便能满脸笑容地面对热闹街市、多姿人间。他是一个与现代生活深深溶在一起的人,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陌生人群的喜怒哀乐、举手投足,他都能感应。
因此,他的雕塑也拓展出了另外一番风光。
他的裹卷人气的雕塑,让青铜泥石也浸润着最浓郁的人气。于是,真实人物的具体形象也成了他的基本素材。但是,与茫茫世间的芸芸众生不同,这些真实人物的具体形象一旦到了他手上,就出现了绝不寻常的神采。这就是他的“另类写意”,仍然属于“写意雕塑”的范畴。
“另类写意”写什么“意”?那就是着重刻画雕塑对象不同寻常的意气、意志、意念、意向、意趣、意态。总之,全在“意”中。
首先成为标本的,是一群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画家、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成了吴为山的模特儿,真是幸运,因为他们在青铜泥石中再度复活,或再度年轻,而且将一直这样活下去。
这些现代名人,文化品级高低不同,按古代“立像入史”的标准,其中很多人未必符合。原来,借助于现代照相技术和公共传媒,这些人的形象、表情已经广为人知,但一经吴为山的手,他们居然全都生动起来,人们就明白何谓雕塑上的“写意”魔法了。
我发现,吴为山的魔法,是努力抓住这些人物的“神情之要”,并把它夸张成一种具有感染力和冲击力的造型关键,而把其他不重要的造型素材都模糊、省俭。结果,只让“神情之要”直逼观众,逃也逃不掉。
观众对这样的雕塑,反应热烈。我读了一些他们的谈话记录,觉得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说得最好。杨先生看了吴为山雕塑的费孝通后,觉得比费孝通本人更像。这个说法很有趣,却以一个大科学家的高度断言,写意比写实更有力,也更真实。我相信,这会让很多写意艺术家兴奋。此外,杨振宁先生还说,吴为山雕塑中,往往是模糊之处最动人。模糊,是因为有意态渲润,神情波荡。只要在这种模糊之外有了过多的真实细节,反而成为障碍。

吴为山凭借着真实人物的具体形象所施行的“写意”魔法,就发生在写实主义的近旁,因此也可以看作是“近距离挑战”,但吴为山并不与写实主义作对,最多,他只是开了一个“咫尺之间的玩笑”。我想,这对于庞大的写实主义雕塑队伍,有一种温和的提示作用。通体逼真没有那么重要,人之为人,在于那口气,在于那股神,只需点到穴位,全盘皆活。因此,写意之笔,也就是点睛之笔,删略之笔,也是救生之笔,回神之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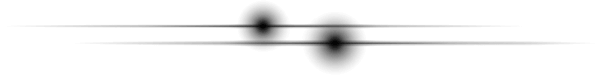
五
吴为山裹卷人气的雕塑中,还有一路,那就是让表情模糊化,着重于点化人的形体。
这显然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即借结构设计来实现最优化的形体力度。而这个形体力度,又恰恰与观众内心的心理结构深度呼应,从而产生超乎预期的感动。
吴为山雕塑中有两个内容相反的系列,在心理效果上却同样惊人,那就是“人间温暖”系列和“战争暴虐”系列。对这两个系列,请允许我不作具体分析了,我只想说,雕塑造型有可能给人类带来大善大恶的终极性冲击,其力度几乎达到了宗教境界。
无言、无声、无笑、无哭、无呐喊、无申诉、无激励,仅仅是人物的造型,包括模糊的表情造型和强烈的形体造型,却展现了真正的地狱和真正的天堂。

总之,从云冈开始的对话,是说不尽的。大至天宇,小到眉眼,全都凝聚到了铜铁泥石之间,成了人类学的课本。在现今不断出土的上古遗址中,已经可以看到遥远的祖先所做的最原始的雕塑,其中,多半也是“写意雕塑”。此后,雕塑几乎与人类的命运不分不离、休戚与共,每一个重大关节都没有错过。
羡慕吴为山先生,能日日夜夜安静地用雕塑与天地灵魂对话,并把自己的生命与众生的生命,留存得那么壮丽。多少年后,当厚厚典籍和滔滔言词都成了过眼烟云,唯有那些雕塑还在。而且,不管人类的语言文字发生了多大变化,它们还在默默发言,并让所有的发现者立即懂得。人类因雕塑而贯通,并非虚言。
(余秋雨,文化学者、理论家、散文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
为潘天寿先生塑像
潘公凯
2006年,杭州西湖区相关领导建议,把画家潘天寿和黄宾虹的墓都迁到超山。我赞成这个方案,并希望在潘天寿墓前摆放其雕塑。潘天寿的塑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做过几次,但是因为大小不太合适,所以这次打算重塑。
我希望把潘天寿的塑像做得比较生动,能够把老先生的精神面貌体现出来,但是,这个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西方的雕塑艺术传入中国时间不太长,尤其是西方经典的、写实性的雕塑。对于中国雕塑界来说,还是很难达到西方经典写实雕塑的水准,我为这个问题踌躇了好久。
我曾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上偶然看到过几座吴为山雕塑的文化名人像,看了其个展之后,为山兄的作品让我眼前一亮,他的雕塑风格正是我想要的。他的雕塑风格是一种大写意的语言,显得很空灵,形态、姿势特别生动,对于刻画对象的精神特征、文化性格十分敏锐。于是,我对吴为山的雕塑作品发生了兴趣,还留意看了他的画册和更多作品。
吴为山在塑造人物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特征方面,有特殊的敏锐性,而且他做这类雕塑显得很轻松,手法非常熟练。于是,我就去找吴为山,特地委托他在杭州超山为潘天寿先生塑像。
当然,这对于吴为山来说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潘天寿的照片很有限,有几张比较清晰的都是正面,侧面或者半侧面的很少。虽然资料有限,但他没有二话就开始了构思和创作。
不久吴为山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做了,叫我去看看。到工作室一看,他已经把大的形体用黏土给堆出来了,正在做细部塑造。他在宽大的工作室内快速地移动脚步,远远近近地把握着大关系。他的手法大刀阔斧,对于形态、姿势,包括微小的动态的把握都显得果断快捷、十分敏锐。
我总共去了两次,只有几天他基本上就定稿了,这个速度让我颇为惊讶,觉得为山兄的基本功真是很棒。因为这一类带有生动的写意语言类雕塑,其实是挺不容易的。这一类的雕塑是以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几个大的雕塑家为代表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罗丹。这种写意性的雕塑对形体把握的敏感性和准确性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达到眼、手、心的一致性。同时,还需要雕塑家对于表现对象的文化特色、性格特色有深切的理解能力和独特的风格性的表现力。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实践经验和对于形体、空间、情绪的综合把握能力,以及对于夸张性艺术语言的运用,要达到这样突出的艺术性效果都是不可能的。
不久,吴为山翻制的铜像就运到了杭州,因为我们事先做好了基座,铜像摆上去以后,对这个墓园大为增色。当时,看到的人都说好,大家觉得潘老先生的精神状态表达得比较充分,主要的特点是作品很生动,没有那种板滞的、教条的感觉。我个人觉得,这是为山兄比较成功的代表作。

吴为山这种具有写意性的,带有夸张的、诗意的雕塑语言,在目前的中国雕塑界不太多。而这种语言对于表达现实的具体的人,即有名有姓的具体的人特别合适。这方面的探索,我不仅认为非常必要,而且认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个人觉得,在近些年,中国的抽象雕塑发展得很快,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出色成果,但是写实的、写意的,和既带有诗意的手法又能准确表现特定人物的特定精神状态的这样一种写实雕塑,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甚至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雕塑教学当中,像这样一类具象写实,是需要加强的,因为有社会需求。
吴为山是中国写意性、诗意性人像雕塑的出色代表。从传承脉络上讲,我想他一定是深受罗丹的影响,而且加上了对中国传统的热爱和感悟。这二者的结合,使他的作品既有罗丹式的敏锐生动,又有中国文人的潇洒恣肆,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在中国雕塑界独树一帜,这也正是我请他做潘天寿塑像的由来。
有意思的是,以上的小故事还有后半截。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母亲还在世,有一次刘开渠先生来杭州,到我家看望她,因为两家是老同事、老朋友,开渠先生从美术馆馆长的角度说起,馆藏中有多幅潘老先生的作品,但多是中等尺幅的、竖幅的作品,最好再有一幅横幅的大作品,希望我母亲捐一幅大画给美术馆。我母亲随即答应了,将大横幅巨作《记写雁荡山花》捐给了中国美术馆。刘先生特别高兴地说:“太好了!这样吧,我回去给潘老做个雕塑铜像,放在美术馆院子里,作为感谢吧。”刘先生也很豪爽。
然而,开渠先生回北京后,估计是忙,一时没有动手做,也可能是时间一长忘记了。总之,做铜像之事没了下文。我母亲去世后,连我也忘了这事。这次在文化部纪念潘天寿诞辰120周年之际,我忽然记起来还有这么一件事,顺便就向吴为山馆长提出:“能不能就趁这次纪念活动的机会,你作为后任馆长替前任馆长完成那个三十多年前的心愿,将你做的潘天寿坐像再翻制一个,放在美术馆院子里呢?”他一听,说:“啊?有这事儿!那个承诺当然应该兑现呀!”于是,现在的中国美术馆东南角的草坪上就有了一座潘天寿的坐像。
每天太阳西下,穿过树叶的阳光洒在铜像上,熠熠生辉,院子里的许多雕塑都在绿树丛中点缀着中国美术馆,显得那么静穆辉煌。
(潘公凯,潘天寿之子,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馆员。)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
文字:余中先
制作:姚晓丹 王长江
你还会喜欢:
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