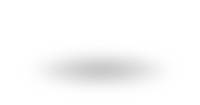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
8月10日
星期四
农历六月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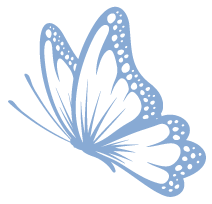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0日,星期四,农历闰六月十八。在本期微播报中,由作家张翎为大家带来她的最新抗战长篇小说《劳燕》中的一个片段。
劳燕(节选)
文|张翎
鼻涕虫的尸首,是第二天傍晚送回到营地的。
日本人包围住鼻涕虫时,他还剩下一口气。他把汤姆森枪扔进了水里,用左轮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这才是最后致命的一击。日本人把他捞上岸后,砍了头,将他的头颅挂在城墙上示众。后来是队长的哥哥买通了一个日本军曹,用十个大洋的代价换回了鼻涕虫的尸身。
鼻涕虫的尸身抬进村的时候,军号奏出了一长串低音,那声音像是泉眼被石头堵住时发出的呜咽。还没见着人,光听见这调子,村里的狗就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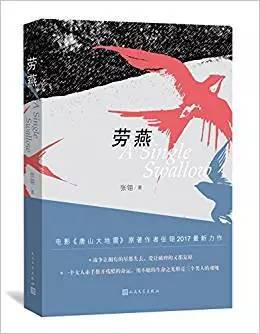
训练营的中国学员和美国教官在路边排成两列队伍,立正敬礼,向他们倒下的战友致意。他们在这个姿势上站立了很久,一直等到人从村口抬进了中国学员宿舍的院门。几天以后他们在毕业典礼上见到他们的最高统帅时,阵势也不过如此。
伊恩在自己的国度里见过阵亡将士遗骸归来的情景,他们的棺材上覆盖的是星条旗,而这具尸体上裹着的,却是一床破旧不堪的草席。
队长和刘兆虎用毛巾揩拭了鼻涕虫身上、脖子上和头颅上的血迹,给他换了一身干净的制服。衣裳终于遮挡住了他那个被子弹打得如米筛般的躯体,只是他们怎么也遮不住他头颅上的弹洞——这是他用左轮朝自己开的那一枪。子弹的入口并不惹眼,边缘清晰地朝里凹陷进去,干干净净的像是瓜果皮上的一个大蛀孔。真正惹眼的是出口。子弹在鼻涕虫的脑壳里憋足了劲,不顾一切地踹出了一条出路,留下一个边角模糊的窟窿,血肉和脑浆已经封上了那个洞口。鼻涕虫该有多想活啊,这么多发子弹都没能叫他咽下那口他不想咽下的气。

终于洗濯干净穿戴整齐,鼻涕虫的眼睛却依旧半睁着,刘兆虎用手抹了几回也抹不下去。那眼神与其说是不甘,倒不如说是嘲讽。他的嘴角微微朝上拐着,露出一丝吊儿郎当的笑意,仿佛刚刚讲完一个阴损的笑话,正不耐烦地等待着别人迟迟不来的起哄。刘兆虎问身旁的人讨了一只角子,要压眼睛,队长叹了一口气,说算了,他活着也是这副德性,由他去吧。
两人抬起鼻涕虫的尸身,正要往棺材里放,就听见大门外有人喊了一声“等一等”,接着便是一阵自行车倒骑着刹车时发出的嘎吱声。不用回头,众人便知道来人是牧师比利。这一带除了牧师比利,没有第二个人拥有自行车。
牧师比利停下车子,后座上跳下一个手里挽着个白布包袱的年轻女子。牧师比利指了指跟在他身后进了院门的那个女子,对队长说:你放心,我不是来祷告的,我只是带斯塔拉过来,她要送他一送。

那个被牧师比利叫作斯塔拉的女子走到鼻涕虫的尸体跟前,两腿一矮,膝盖就触到了地上。众人都以为她要下跪,可是她没有,她只是将身子朝后一仰坐在了自己的脚后跟上。坐稳妥了,她就慢慢地拖过鼻涕虫的躯体,枕在了自己的腿上。女孩小心翼翼地捧起鼻涕虫那颗已经和身子分了家的头颅,安放在自己的腿窝里。她捧着那颗头颅时的神情,就像捧着一个装满了金元宝的脆瓷瓶。
然后她打开了随身带来的那个白布包袱,找出一卷粗线,又从一个布囊上取下一根插在上面的大针,仰着脸,眯着眼睛,对着已经稀薄的日光穿起针来。穿完针,她俯下身来,把鼻涕虫的下巴对准了制服上的那个中缝,瞄了一眼,然后在鼻涕虫的颈脖上扎下了一针。
围看的人群“啊”地一声惊叫了起来,他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女孩要把鼻涕虫的头缝回到身子上去。

女孩每一次下针之前,都有些犹豫,像是怕扎疼了手下的那个人。可是每次真下针的时候,却又很是决绝,手指沉稳有力,丝毫没有颤抖。鼻涕虫本来就瘦小,流完血之后的身体又缩了一大圈,衣袖和裤腿卷了好几卷,才露出手脚来。鼻涕虫枕靠在女孩腿上的样子,看起来像个赖在大人身上不肯起床的半大孩子,而女孩脸上那个温存而耐心的笑容,则像是一个在哄淘气的孩子入睡的小母亲。
在漫长的犹豫和决绝之间,女孩终于把那具支离破碎的尸身缝成了一个整体。她把那颗重新连接到躯体上的头颅捧起来,远远地望了一眼,仿佛在欣赏一副精心完成的绣品。然后她取下扎在辫子上的手绢,在鼻涕虫的颈脖上围了一圈,遮住了那条缝痕。
伊恩看着女孩从容不迫地走出院门,扎实的脚步嚯嚯地扫开路上的灰尘,松散开来的头发随着她的步子在她的背上簌簌颤动,心里突然生出些感慨来。这个女孩,让他这一辈子认识的所有女人,包括母亲,包括妹妹,包括女友,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今日主播: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现定居多伦多市。九十年代开始写作,代表作有《流年物语》《金山》《雁过藻溪》等。小说被译成多国语言在国际发表。
2. 读《汪曾祺的迷人细节》
文字编辑 | 丛子钰
网络编辑 | 周 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