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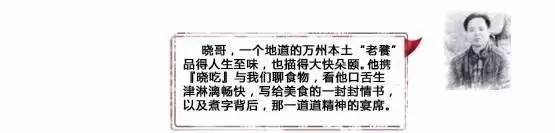
我记忆中的万县老县城,白日耀眼的阳光下,班驳破旧的楼房中,有蛛网般的电线缠绕。所以我不喜欢老城的白天,喜欢它在夜色里的温柔,美食在空气里窜动的味道。
那些年,在万县老县老城阑珊的灯光下,万县大桥街边有一家卖猪蹄花汤的铺子,店铺主人是一个身材肥胖的老太太,食客们都叫她“胖子妈”。“胖子妈”总是笑眯眯的面相,慈祥安宁,我觉得,她就是县城平民生活里那个每天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母亲代言人。“胖子妈”炖的蹄花汤,在炉子里一般要用好几个小时。一碗雪白的蹄花汤,总让我想起丰腴少妇的乳汁。青花瓷碗里,汤里漂浮着细碎葱花,炖得软软的猪蹄子,用筷子轻轻翻转,骨肉相连的雪白中夹着一层粉嫩的红,那是瘦肉部分。把软烂的猪蹄子夹入嘴里,卷动的舌头上来亲昵拥抱,还没等牙齿前来相助,从骨头滑落的肉早已顺着喉咙下了肚,再喝一口奶汁般的蹄花芸豆汤,舒服得漫向身体的四脉八方。
我在万县城东游西逛的年代,这家卖蹄花汤的馆子,就是县城的何诗人带我去的。何诗人说,他与“胖子妈”就住在一条街上,知道“胖子妈”拖扯着几个孩子长大,同他一样,也是苦出身。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何诗人:“你的身世真那么苦?”何诗人一碗蹄花汤喝下去,泪水也簌簌而落,他抱住头哭了:“我7岁死了妈,12岁时爸出了车祸造成瘫痪,14岁那年死了姐……”后来再读何诗人的那些诗,确实感觉有黄连的味道。
也是在这家馆子里,我通过何诗人,走进了县城文人们的圈子。俗话说,文人相轻,不过我倒没觉得。或许是一碗蹄花汤,让骄横自私的心也变得温软通泰。每次在这里见面,喝了蹄花汤后,文人们差不多都是经久不绝地相互赞扬。
后来,何诗人调到了省城。临行前的一天晚上,我邀约了几个人为他饯行,何诗人确实人缘好,他还把县上一个领导喊来了,领导平易近人,说话也没有会议腔。那天大家吃喝得无拘无束,“胖子妈”得知何诗人要离开县城了,还端来了几个凉菜让我们喝酒。等我去结账时,“胖子妈”挥舞着锅铲爽朗地说:“这顿饭,我请了!县城里调走了一个诗人,多大的损失哎!”
何诗人调走以后,我还是隔三岔五到“胖子妈”的馆子里去喝上一碗蹄花汤,尤其喜欢在夜里去一趟。这样一趟行程,几乎就穿过了大半个老城。有时我看着煤炭灶里火球滚动,“胖子妈”在锅边挥汗如雨,我就想起乡下的母亲,她在稻田里匍匐着瘦弱的身子,汗珠滚落,突然明白了一粒大米为什么那么白,原来是经历了风雨雷电的洗礼,也有着农人们汗水的浸透。
我之所以喜欢在夜里去“胖子妈”的店铺里喝一碗蹄花汤,一方面是那时我还在废寝忘食地写诗,诗一旦绞尽脑汁写累了,现实生活中就容易疲倦颓废。我常觉得自己的人格有些变形,比如在文字里抒情,可实际面目常露丑态,而老城夜晚里的一碗蹄花汤喝下后润了心肠,我又袅袅飘起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雾岚了。还有一个原因,城里一个女子,白衣白裙,面容娇好,肤如凝脂,深夜里常从某个小巷神秘地飘来,在那里端坐着,喝上一碗蹄花汤就离开,让我恍惚中以为那女子是从蒲松龄的“聊斋”里而来。细看她的面相,还和那些年的大众“女神”长得很相似。我去那里喝上一碗蹄花汤,和那女子似乎是一种接头暗号。
后来我陷入很深,才知道是暗恋上她了,却从来没有开口说上一句话。等有天夜里,一个驾驶摩托车的男子来接她,她坐在男子后面紧搂住他的腰,还发出哈哈大笑,摩托车“突突突”绝尘而去,消失在昏沉沉的夜色里。我踉踉跄跄起身离开,如遭雷击。那一次“魂断蓝桥”的单恋,没想到是在深夜里无数次抚慰过我身心的蹄花汤馆中发生,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这馆子一回。而今“胖子妈”馆子,早已在老城拆迁中消失,在我记忆里有时也缥缈如宋朝夜市上的灯光。
但那一碗香浓暖胃的雪白蹄花汤,它还在我的血液里住着。尤其是在深夜里,我隐隐约约听见了血脉里的流淌声。
作者:李晓 图片:网络
编辑:何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