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屈原,实在是没什么故事可讲,但他在历史上又是如此出名,且慢,真是在历史上很出名么?他只是近几十年来一个全民造神的结果。时代需要偶象,于是,一个故纸堆中单薄的愤青,变成了一个我们熟得不能再熟的陌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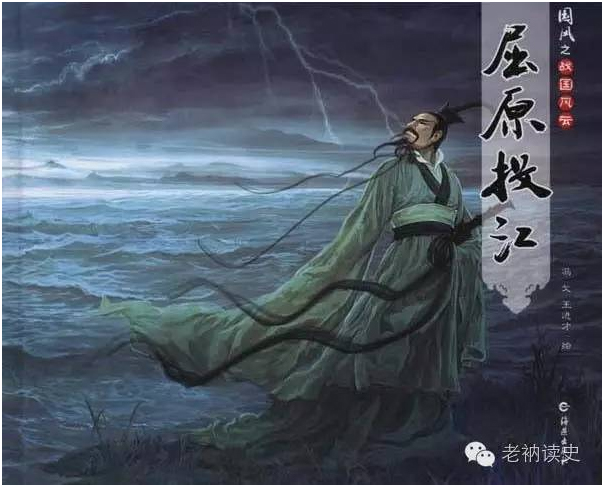
说起屈原,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粽子节呀,不管你爱不爱吃粽子,端午好歹还放一天假,东挪挪西凑凑,也是一个“小黄金”,可以让你稍喘一口气了。
感谢楚国、感谢湖北、感谢荆州、感谢屈原。
就这?当然不,屈原身上的标签可不仅仅是粽子和端午节。下面这些有关屈原的资料,基本出自《史记》,也有一点是“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郭沫若整理出来的,大致的内容大家可能都知道,但还是得先说一说。
屈原,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诗人,芈(mǐ)姓屈氏,名平,字原,楚国丹阳(现湖北秭归)人,他的生卒年各家推算不一,按郭沫若的说法,在公元前340—前277年,享年62岁。
屈原的出身,与楚王同宗(楚王的祖先姓芈,但这个姓又分为几个氏,楚王一支为熊氏,另外还有屈、景、昭等氏,这些氏就相当于现在的姓),家族已经没落,但还算是贵族,有机会接受教育并入朝为官。屈原青年时曾任怀王的左徒。他“博文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深得怀王的信任。
屈原受命起草“宪令”,还只打了一个草稿,就被上官大夫靳尚瞄到了,靳尚觉得屈原写得真是太好了,就跟屈原打商量:小屈啊,你看你弄这个东东也累了,你克休息一哈咧,这个“宪令”,让我来帮你誊正吧。
屈原不傻啊,这一交给靳尚,最后的成果就成了靳尚的了。屈原不干,坚决要求自己独立完成,以捍卫他的著作权。
靳尚见屈原不上当,心中老大不痛快,愤愤地跑到楚怀王那里告状:大王啊,您让那个屈原制定法律,每次法律公布的时候,屈原就在外面给自己评功摆好,说除了他,别人都弄不出来。
于是,楚怀王就生气了,就不再信任屈原了,就开始疏远屈原了,就把屈原的官职给免了。按史记后文一笔带过的说法,此后的十来年中,屈原可能在楚国的外交部做一个小小的外交官员,因为他被罢官后还出使过齐国。
再后来,楚怀王被秦昭王骗到秦国去软禁了起来,死了。顷襄王继位,这时小小的芝麻官屈原写了一篇什么,讽剌楚王和靳尚及宰相子兰。子兰听说了不高兴,让靳尚去向楚王说屈原的坏话,这个新上台的楚王也生气了,两次流放屈原,一次比一次更偏远。
在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时,他经过湖南的汩罗江,碰到了一个渔夫,他对渔夫说:世人都是混浊的,就只有我一个是清白的,世人都是昏醉的,只有我一个人是清醒的。渔夫听了教训他说:你为么事要这么固执咧?你就不懂得权变一哈?你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唦。
屈原听了大怒,抱着一块石头就跳到汩罗江里淹死了。据说这一天是五月初五,端午节。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老衲努力地想多写一点关于屈原的英雄事迹出来,可惜,史记上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找了很多资料,但也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没有更多。
有一种说法,说楚国根本就没有屈原这个人,因为在《史记》之前,没有任何史料上出现过关于屈原的只言片语,所谓屈原,只是司马迁杜撰出来的一个人,借这个人来抒发心中的怨气,表达对汉武帝的不满。
司马迁把屈原捧得很高,可惜,他讲述的关于屈原的事情却很没有说服力。
首先,屈原的才华体现在哪里?只有论点:“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论据就只有很简单的几笔:上官大夫想夺署名权,再就是劝楚怀王杀张仪(失败),劝阻楚怀王入秦(还是失败)。
这实在是太单薄了,根本没办法体现出屈原的优秀、杰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人,在战国时期实在是太多了,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比如苏秦、张仪、苏代(苏秦的弟弟)、陈轸(也是楚国人)、甘茂、虞卿、范睢、蔺相如、鲁仲连等等等等,司马迁在他们的列传中,也不厌其烦地记下他们上书的表章、与相关人物的辩论,或者实施的计谋、推行的政令,让人一看就觉得他们厉害。倒是司马迁无限推崇的屈原,除了引用几句屈原的“楚辞”证明他的精神高洁外,实在没有办法能让人相信屈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精英,反而会觉得屈原此人过于偏激、固执、孤傲,很难相处。
其次,关于屈原的官职。史记开始说他是“左徒”,后面讲到他和渔夫相遇的时候,顺带提起他担任过“三闾大夫”。这两个官职都是楚国特有的。
先说“左徒”,这倒底是一个什么官,现在也说不清楚,有很多人考证过,一部分人为了证明屈原是一个有非凡能力的人,认为“左徒”是仅次于“令尹”(即楚国宰相)的大官,相当于上大夫一级,只要稍微加把劲就可以升为令尹了,这就能配得上《史记》中说的“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左徒”其实是一个小官,相当于后来唐代的“左右拾遗”中的左拾遗,而且,与后世左比右大不同,楚国时尊右,右比左大。那么唐代的左拾遗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呢?拾遗,顾名思义,就是捡起(领导)遗漏的东西,实质上就是一个言官,有点类似现在的监察部门,他们的工作就是挑皇帝的毛病。这个官职不算大,大概居于七、八品左右。杜甫就当过左拾遗。也有人说“左徒”主要是负责外交事务,兼掌一定内政(主要是法律文书)方面的工作。总而言之,屈原因为是王室宗亲,又写得一手好“辞”,所以和当时的楚怀王走得有点近,但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屈原被免“左徒”后,还担任过“三闾大夫”。“三闾大夫”就更加是一个虚职了。所谓“三闾”,就是楚国芈姓中,除了熊氏之外另外的三氏——屈氏、景氏、昭氏——的宗族人员,“三闾大夫”就是这三家宗族的管家,负责宗庙祭祀和教育工作,屈原有学问,写得一手好“辞”,看来这个工作是蛮适合他的。
最后再说说楚辞。百度上面是这么介绍楚辞的:《楚辞》是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和骚体类文章的总集,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
也就是说,楚辞基本上就是屈原的个人作品集,另外点缀一点宋玉、刘向等人的篇目。近代一些学者如胡适等人,说屈原只是传说中的人物,世上并无此人,但是《楚辞》的存在(1977年出土过《楚辞》的残片),证明历史上是有屈原这个人的。但是近代文学史家朱东润又认为,除了《离骚》是屈原的作品外,其他的都不是的,因为西汉初年,包括汉武帝在内的几个皇帝都喜欢楚辞,于是有很多人就模仿《离骚》写了不少,假托是屈原的作品进献给皇帝,以此寻一个进身之阶。
且不管这些吧,单说楚辞本身,老衲就很是不喜欢。当然,老衲只是自己不喜欢,不妨碍您去喜欢。老衲觉得楚辞佶屈聱牙,相比诗经的朗朗上口,楚辞兮来兮去的像绕口令,还有好多字让人不认得不懂是什么意思,揣摩半天,兴味索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当上下而求索”这句话,估计是里面最通俗的了,但除了这个,一般的中国人还记得哪句?老衲只是一个俗人,可以背上几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却实在是望楚辞而却步。
写到这里,已经不是在讲故事,反倒像是一篇议论文。对于屈原,实在是没什么故事可讲,但他在历史上又是如此出名,且慢,真是在历史上很出名么?非也,司马迁之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学史上偶有提及屈原之外,把他当作一个“爱国主义”名人来谈的,好像还真找不出什么东西来。
屈原的出名,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1942年,拜“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郭沫若所赐。1942年正是抗战步入低谷的时候,国共两党也因为“皖南事变”而关系紧张。为了激励民众的抗日决心,更为了讽刺国民政府,郭沫若便写了历史剧《屈原》,于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副刊上连载。《屈原》一剧在重庆公演后,民间反响很大,共产党方面更是给予极高评价,屈原的“事迹”由此发掘出来,此后经过不断地修饰、论证、拔高,屈原的光辉形象越发不可收拾,最终成了现在的“全民偶象”。六七十年的耳濡目染,几代人的灌输,躲也躲不掉啊。
据说,毛泽东就很喜欢楚辞,特别喜欢宋玉的作品,像《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对楚王问》以及《九辩》等,毛泽东都读得很熟,还多次将《风赋》、《登徒子好色赋》推荐给高级干部们阅读。
宋玉据说是屈原的弟子,屈原的很多作品都是宋玉帮忙整理的(郭沫若的《屈原》中,把宋玉描绘成一个叛徒、小人,这是没有史料依据的)。最高领导人喜欢屈原的弟子,屈原本身又有着高尚伟大的形象,唉,不红也难啊。全民造神的结果,就是把这一个故纸堆中单薄的愤青,变成了一个我们熟得不能再熟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