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道隣,民国著名法律人士,国民政府官员
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
一九五四年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
一 、写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不易
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粱任公先生曾指出过,在材料方面。其困难之点有三:(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现存之史料,可谓极丰富,独惜散在群籍。非费极大之劳力,不能搜集完备。非有锐敏的观察力,时复交臂失之”。(二),“资料审择,又为治国故者一种困难之业。因古来伪书甚多。若不细加甄别,必致滥引而失真......至时代背景与思想系统完全混乱,而史之作用全失”。(三)“不惟伪书而已。即真书中所记古事古言……大半只能认为著书者之思想,而不能尽认为所指述之人之思想……即诸经诸史中资料,亦当加审慎……盖史迹由后人追述,如水经沙滤必变其质,重以文章家善为恢诡詄荡之辞,失真愈甚……惟有参征他种资料,略规定各时代背景之标准,其不大缪于此标准者,则信之而已”。(先秦政治思想史﹝民国十一年﹞,页九至十)在作者主观方面,其困难有二:(一)“社会事项,最易惹起吾人主观的爱憎。一为情感所蔽,非惟批评远于正鹄,且并资料之取舍,亦减其确实性……政治上理论,出入主奴之见少甚。中国唐宋以后学者……之论嚣然,而斯学愈不可复理。……吾侪宜保持极冷静的头脑,专务忠实介绍古人思想之真相,而不以丝毫自己之好恶夹杂其间。”(二)“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质言之,吾侪所持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决……虽然,吾侪忠于史者,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吾侪所最宜深戒也。”然而这两种态度,就是任公先生自己,也自病其“能言之而不能躬践之”。他说:“吾少作犯此屡矣。今虽力自振拔,而结习殊不易尽。”(同上,页十二,十三)以学术修养如任公先生的人,尚有此叹,那么其他的人更可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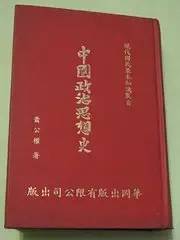
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
钱宾四先生指出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另外两种困难。(一)“我族传统政治思想,都渗透包会于各家思想之全体系……种种哲学思想上之本体问题,与其政治思想息息相关,水乳难分。非于哲学有专诣者,难于胜任而愉快。”(二)“中国政治思想,随时于制度中具体实现。思想之表达,实际已不在文字著作,而在当代之法令,历朝之兴革,名臣之奏议。举凡兵刑礼乐,户役赋税,所谓托之空言,不如寄之行事之深切而著明。非于治史有专精,尤难抉发其底事。”见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
但是,写中国政治思想史,除掉上面所说的以外,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因为对于过去有关政治问题的思考,作一项历史性的观察——就是说,从历史的立场上予以观察,也就是说,研究这些思想在时间顺序上的演变,和它们与时代背景的交互影响——完全是近代西方学术的观点(所以在和西方学术接触以前,两千多年,我们从来没有这一类的著作。而在西方也是比较晚近的事)。所以要作这一门学问,一种适当的现代西方学术的训练——最重要的,即所谓一个有科学训练的头脑scientifically trained mind——是一个起码的条件,而且必须对于西方的政治思想,也有足够的认识,才能够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作比较正确的评价。不然的话,只是在故纸堆中打滚,而想在顾亭林,王船山诸人之后,在这一方面,再如何重要的贡献,恐怕就很难了。但是有了西方学术训练,还必须在国学方面,先打好了比较深厚的基础才行。近来若干作家,有的对于训诂学问太生疏,有的在材料评价上太外行,因而制造了不少的笑话,都是国学修养太差的缘故。也就是说,要作这一门学问,必须在西方现代学术,和中国国学方面,同样的有比较高深的修养,才能望其成功。这一点困难确实是很大的。而也就因为这一项困难很大,所以在这一方面工作的人非常的少,因之可以利用的现代材料,也非常缺乏;不但关于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不多,就是关于某一个时代或者某一个思想家的比较现代的著述,也异常稀少,所以要作这一门的研究,差不多处处都要从处理原始材料开始。(西洋人作同样学问的,在五六十年以前,就已经有很多整理好的材料,可资利用。)而中国人之从事政治思考,已经两千多年,时间是如此之长,人数是如此之众,要作全部的整理和探讨,真是谈何容易!于是努力的缺少,和问题的艰难,益发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二、本书的优点
萧公权先生是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研究政治学的。在民国二十六年,他用英文发表了一本《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这是讨论西方当代政治理论的一部出色的著作,这一点说明了他对于西方学问的修养。但是在二十七、八年前,我曾经看到他翻译的几十首英文诗,一律填成阴阳四声十分严格的中国“词”,这一点至少说明了他国学的深厚根柢;和他好学深思的精神。以他这样西学和国学的优良基础,来研究中国政治思想,从基本条件上讲,就已经胜人一筹了。

英文版《政治多元论》
萧先生这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单从内容的范围来看,就在这一类的著作中占第一位。全书六册,约七十三万字,从孔子起,到辛亥革命(关于国父的一章,尚待完成)。所包含的时间,上下两千五百多年。其中经过比较详细叙述的,约有六十多人,内容可以说是相当完备。所以在今天研究这门学问,不管教学用也好,参考用也好,萧先生这部书,是不能缺少的。
现在再试就质的方面,举出它的几项优点:
1、高度的系统思考
以现代学术方法整理国故,其和古人不同,因之比较可能超过古人者,主要的是因为现代人的思考,比较有系统systematic之故。所谓“有系统”者,就是能“分析”analysis。而这个分析,包括两方面,一是种类的分辨,即所谓“分类”classification 是也;一是价值的分辨,即所谓“评价”evaluation是也。过去中国人读书,多半长于领会(所谓“心领神会”),而不长于作系统性的探索。所以虽然也谈到“条理”,而不知道注重“分类”,也谈到“要领”,而不知道利用“比较法”。可是他们十分相信自己有“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天赋能力,因而惯于下“以意逆志”的工夫,以为“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于是人人都自以为可以和周公孔子直接交通,而过去一两千年的学者,一个个全都大错特错。
一个善于作系统思考者,可以从古人一堆散漫的材料中,整理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他举出一个思想家的几项主要观念,而他的其他许多观念,就都成了这几项主要观念的推行和说明,而这几项主要观念本身,不但不彼此冲突重复,而且彼此间相互发明,相互支持,而形成了这一个思想体系的主要骨干。有了这种系统观念,再去读古人的原始著作,好像拿着一幅地图,去游览城市,胸中有一个全体的和方向的观念存在,不致于为斜街曲巷所迷。当然,一位后人,替一位前人整理思想,他所钩画出来的,不一定是惟一可能的体系。另外一个人,可能整理出另外一套体系来。再多的人,可能整理出再多的不同体系来。那么哪一个人整理出来的是最正确,最适当,那就要有待于读者多数意见的公断了。
萧先生对于古人思想的系统整理,有若干处,是十分成功的。例如书中对于孔子的叙述,说他“学术的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页五三)。他的政治思想的起点,是要恢复周礼(盛周时代的全部社会制度)(页五八),而“植本”于他所发明的“仁”的观念(即推自爱之心以爱人)页五九。他的“治术有三,曰养,曰教,曰治。养教之工具,为‘德’‘礼’,治之工具,为‘政’‘刑’。德礼为主,政刑为辅,而教化又为孔子所最重之中心政策”(页六一)。对于孟子之叙述,萧先生特别举出三点:一、以人民为政治主体的“民为贵”的理论(页八九);二、立新政权以恢复旧制度(页九四);三、一治一乱的历史观(页九七)。对于墨子的学说,书中分就下列六点叙述:兼爱(页一二九),尚同(页一三三),明鬼(页一三七),尚贤(页一四○),节用(页一四三),非攻(页一四七)。以上三例,从三位大思想家广泛复杂的学说中,简单明了的指出它们少数几个中心思想,于是我们很快的就能切实的掌握住他们思想系统的主要骨干。再看书中对于三家思想所分析出的项目,或简或繁,其综合成一个项目的,不可强予割离;分别成个别项目的,不容强予归并,凡此种种,处处都是作者高度系统思考的优美表现。
2、立论的谨严和精辟
在近年来治国故的学者们中间,似乎流行着一种喜欢发新奇议论的风气,他们常常根据一点点不太靠得住的材料,就作十分大胆的,但是并不能满足逻辑条件的推论。于是乎许多“创见”和“发现”,不但丝毫不帮助我们对于古代事物的了解,而只是凭空的又多制造出若干笑话和麻烦。例如有人主张孟子的性善论,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有人说从汉唐到清末,政权治权的重心,都在臣民,“皇帝几一画诺之虚号”,有人说,照唐律的规定,“丈夫对其妻,有告诉、骂詈、殴打、折伤、及骂詈并殴打其父母祖父母之自由”。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萧先生在他书中,很少提出与众不同的个人见解——内中也有我不大同意的少数几项,将在后面提出讨论。一般说来,在这方面,他是趋向于保守的。我们与其说他缺乏个人见解,不如说他态度谨严。而这正是在时下风气中难见的美态。
萧先生的态度虽然趋向于谨严,然而这个仍不妨碍他在若干地方作十分肯定的,非常精辟的论断。例如他指出宋后儒者每以臣下效忠君国为绝对义务,实则并非孔子之教(页六六),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页九一)。道法二家思想之相近者皮毛,其根本则迥不相同(页二四六);先秦之法家思想,实专制思想之误称。若干条目,似与法治有关,实则皆失法律之平,为近代法治之所不许(页二六七)。以上数端,都是十分有份量的论断。
3、功力精深
如果把中国政治思想史当作一宗浩大的工程,则萧先生所表现的“不惜工本”的伟大精神,着实是可惊的。他所准备的材料极为丰富,工作十分仔细和考究。他不躲避任何复杂或艰深的问题,忽略任何和问题有关的著作,他如果把所参考过的书籍列一清单,一定是非常可观的。他书中每章正文后的小注,少的百节左右,多的一百八、九十节。占全书篇幅将近五分之二。内容包括古今中外,有考证,有议论,有比铰,有引申。最足以说明作者学问的渊博,用心的细密,和态度的谨严。读本书不细读小注,不容易看出他功力之深。
4、责任交代清楚
书中对于采用别人意见的时候,无不一一交代清楚,例如指出孔子设教授徒,遂打破阶级的界限,是章太炎之说(页五三),诗经尚书中极少见“仁”字,是梁任公说过的(页七九,注五四);“墨之本在兼爱”,乃张惠言所举出(页一二九),叙墨家团体组织,曾参考过方授楚之书(页一五四注二九)等等。凡此种种,不掠他人之美,不代他人受过,本是作学问者应有的态度,乃近来似乎常常为作家们所忽略,还有书中引用二手second hand材料时,从不忽略把它明白叙述出来。这些也本是学者们应有的交代,但是现在的作家们多不肯如此做,所以我要在这里特别予以表扬。
5、态度谦虚
读萧先生这部书,予人最深的印象,是他那彻底谦虚的态度。在他叙述他个人的见解时,所用的语句,常常是“如我人所解,尚非大误,则……似乎…”;驳斥他人时,则说“或不足为完全持平之论欤”等等。甚至于有时候未免谦虚的过甚一点,例如“吾人之解释如不误,则严格言之,孔子思想中未尝有近代之民族观念”(页七二),等等,好像一个人过于揖让频繁,反倒有点像故意做作似的。但是和时下若干时髦作家那种自认为了不起的神气对照起来,却又只觉其难得而可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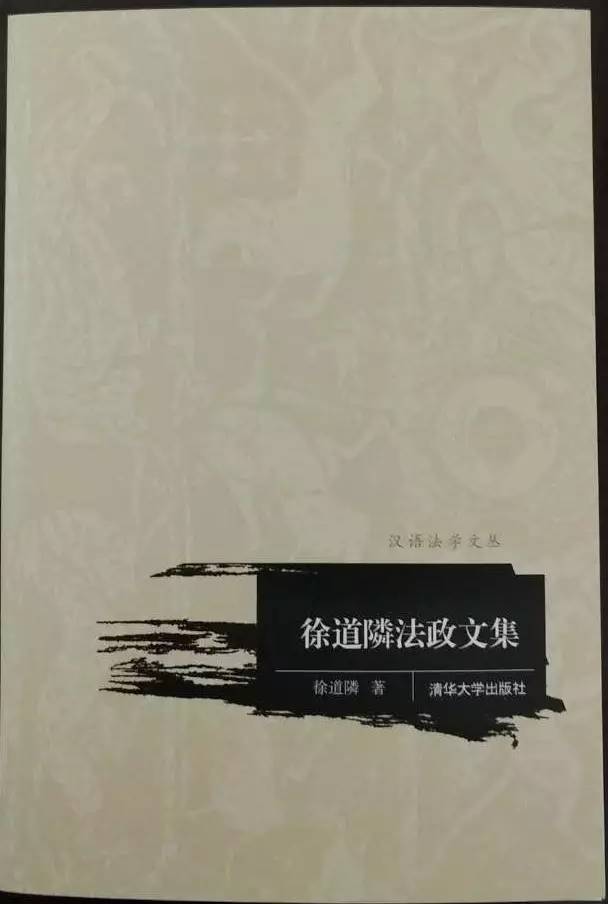
“汉语法学文丛”第四辑《徐道隣法政文集》
陈新宇、刘猛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本文收入“汉语法学文丛”第四辑《徐道隣法政文集》,陈新宇、刘猛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如您观文后有所感悟,欢迎关注并分享“三会学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