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生命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王立秋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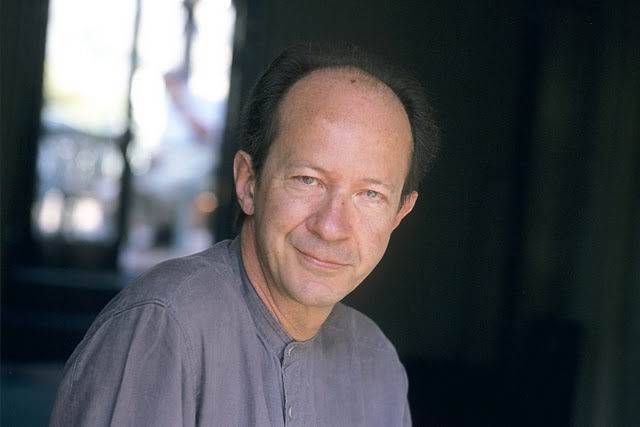
古希腊用不只一个术语来表达我们今天用生命(life)一词来意指的那种东西。他们用的是两个在语义上和形态上泾渭分明的两个术语:zoe,表达的是为一切有生存在(动物,人,或神)所共有的简单的生活事实;以及bios,指的是为单一个体或群体所特有的生活方式或生活形式。在现代语言中这种对立在词典中逐渐消失(只在生物学和动物学中保留的那种区分也失去了实质上的差异);(用来表达生命的)只有一个术语——该术语的不透明性与其指涉对象的神圣化同比例增长——一个指示赤裸的、预设的共有元素的术语,而从任何一种生命形式(生命形式数目众多)中剥离出这种共有元素,(在现代人看来则)总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通过形式生命(form-of-life)这个术语,我意指的,是一种永不能与其形式分离的生命,在这种生命中,要剥离出某种类似赤裸生命的东西是绝无可能的。
不能与其形式分离的生命是这样一种生命,对它来说,在它的生活方式中,至关重要的是生活本身。这种表达意味着什么?它定义了一种生命——人类的生命——在这种生命中,单个(个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行动和生活过程绝非一些简单的事实而已,相反,它们永远且首先是生命的可能性,永远且首先是权力。[1]人类生活的每种行为和形式都不能被规定为一种特定的动物天性(biological vocation,生物学意义上的使命),也不能为任何一种必要性所指定;相反,无论多么合乎习俗,经过了多少次的重复,也无论存在多大的社会强制力,它总是保持着某种可能性的特性;也就是说,它总是涉及生活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作为一种权力的存在,作为他有能力做也有能力不做,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以自我丧失也可以找到自我的存在——是一种唯一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幸福总是涉及生活本身,其生命无可挽回地、痛苦地指向幸福。但这种不可挽回构成了作为政治生命的形式生命。“Civitatem…communitatem esse institutam propter vivere et bene vivere hominum in ea”[国家是为生活其中的人的生活和美好生活而建立的]。[2]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的政治权力则总是把自己——在最终的意义上——建立在赤裸生命的领域与形式生命的语境的分离之上。在罗马法中,vita[生命]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相反它指的是生活的简单事实或某种特定的生命方式。只有一次,只有转化为名副其实的terminus technicus(技术名词),也即,只是在vitae necisque potestas(生杀权)这个表达中,生命这个术语才获得了司法上的意义,而所谓生杀权,指的是家长(pater’s)对男性子嗣的生杀权力。扬·多玛(Yan Thomas)已经指出,在这个表达中,que只有分离性(disjunctive)的功能,而vita不过是nex(死亡)的必然结果,即杀戮的权力。[3]
因此,生命原只是以威胁死亡的权力作用相当的形式在法律中出现的。但对于家长的生杀权来说,有法律效力的,更适用于主权权力/君主权力(imperium),前者正构成这种权力最初的细胞。因此,在霍布斯的主权奠基中,自然状态中的生命仅仅为其无条件暴露于死亡威胁(一切人对一切事物无限的权利)的存在所界定,而政治生命——也就是说,在利维坦的保护下展露的生命——不过就是这同一个永远暴露在威胁之下的生命罢了,只不过现在威胁只来自于主权者/君王之手。用来定义国家权力的puissance absolute et perpétuelle(绝对而永恒的权力)并非建立在——在最终的意义上——某种政治意志而是建立在赤裸生命(naked life)之上的,这种生命仅在服从于主权(或法律)的生杀权时才是安全和受保护的。(这恰是形容词sacer[神圣的]被用来形容人类生命时的原意。)例外状态,每次无一例外地由主权决定的例外状态,正是在赤裸生命——在正常情况下赤裸生命看起来与社会生命的多种形式融合在一起——明显受到质疑或被废除政治权力根基的时候发生的。需要同时变成例外又被包含在城邦之中的主体永远是赤裸生命。
“被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谓‘紧急状态’并不是什么例外,而是一种常规。我们必须获得这样一种努力与此洞见保持一致的历史的概念。”[4]瓦尔特·本雅明的诊断,距今已有五十年之远了,但仍然没有失去一丁点的(时代)关联性。之所以如此,并不真的是因为也不仅仅是因为今天权力除紧急状况外不再有其他的合法化形式,也因为权力到处且不断地在回指、诉诸紧急状况的同时秘密地致力于生产这种紧急状况。(我们怎么可能不想到这点:一个除[基于]处在紧急状况外就根本不能起作用的系统怎会对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这种紧急状况毫无兴趣呢?)这也是因为而且首先是因为赤裸生命——已变成规范的例外状态下的赤裸生命——是在一切语境中把生命的诸形式从它们共同的粘合(这种粘合形成了形式生命)中分离出来的赤裸生命。人与公民之间马克思式的分裂因此也就为赤裸生命(主权终极的、不透明的承载者)与多种多样的生命形式——这些生命形式被抽象地重新编码为基于赤裸生命的社会-司法的认同/同一性(选民,供认,记者,学生,但也包括艾滋病患者,异装癖者,AV女优,老人,父母,女性)——之间的区分所取代。(把这种在落魄中与其形式分离的赤裸生命和一种更高级的原则——主权或神圣者——混为一谈是巴塔耶思想的局限,这个局限使这种思想对我们无用。)
在这个意义上说,福柯的命题——根据这个命题,“今天处在危险之中的是生命”,因此政治学也就变成了生命政治学——实质上是正确的。无论如何,理解这一转变意义的方式才是决定性的。事实上,在当代关于生物伦理学和生命政治学的辩论中未被触及的,正是理应在一切讨论之前被询问的,也即,生命的生物学概念。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设想了两种对称对立的生命模式:一方面是,是科学家的实验生命[5],他患上血癌并把自己的生命变成无限研究和实验的试验场;另一方面,则是以生命神圣性之名,触动个体伦理和技术科学之间自相矛盾的那种生命。然而,这两种模式都没有意识到它们同属赤裸生命的概念之下。这个概念——在今天,它把自己隐藏在科学观念的伪装之下——实际上是一个世俗化了的政治概念。(从严格科学的观点来看,生命的概念根本就没有意义。彼得·梅德沃和让·梅德沃[Peter and Jean]告诉我们,在生物学中,关于生命与死亡等词意义的讨论是低层次对话的象征。这些词并没有本质的意义,因此,这样的意义也不可能在更深刻更细致的研究中得到澄清。)[6]
这就是权力系统内医学-科学意识形态功能(这种功能一般不被察觉但确实决定性的)以及伪科学概念日渐广泛的使用(为终结政治统治)之根源。过去,(只有)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主权才有能力从生命形式中提取赤裸生命的景象,现在,同样的景象则大规模地为——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身体、疾病和健康的伪科学表述,以及不断扩大的生命领域和个体想象的“医学化(medicalization)”所提取。[7]因此,生物学的生命,亦即共享赤裸生命之不可表达性(unutterability)与不可穿透性(impenetrability)的赤裸生命的世俗化形式,也就把生命的真实形式构建成生存形式(forms of survival):生物学的生命在这种形式中不受侵害,故而模糊的威胁能够突然在暴力、异物(extraneousness)、疾病和意外中实化(actualize itself)。在权势者——他们,无论是否对此有所意识,以主权的名义统治着我们——愚蠢的面具后注视着我们的,正是这看不见的主权。
政治生命,亦即被导向幸福理念、与形式生命粘合在一起的那种生命,只有从这个区分中解放出来、撤离一切主权——一旦出走便不再回头——并以此作为起点,才是可思议的。关于非国家政治可能性的问题必然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今天是否可能存在像形式生命——对于这种生命来说,生活本身就在自己的生活中受到了威胁——那样的东西?今天,权力的生活(a life of power)是否可用?
我称思想为在形式生命这个不可分离的语境中建构生命形式的联结(nexus)。我的意思不是通过这种器官(organ)或心灵技巧(psychic faculty)的个体运作(来进行建构),(这里说的)毋宁是一种经验,一种把生命和人类理智的潜在特征作为对象的实验(experimentum)。思考并不意味着只为这样或那样的事物所影响,或只被这样或那样的被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影响,相反,它同时受某人自己的接受和对每个以及一切事物的经验——后者被设想为思考的纯粹力量——的影响。(“当思想以这样的方式——实际上知道的人被说如此言说——变成一切事物的时候……它的条件仍然是潜力之一……因此思想也就有了思考自己的能力。”)[8]
只要我还没有被表达出来,还没有被唯一地表达出来,而是被交付给可能性或力量,只要每次我生活、计划(intend)和理解(apprehend)的时候生活、计划和理解本身尚处在危险之中——换言之,只要有思想存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生命形式才能在其事实性(factness)和物性(thingness)上变成形式生命,而在形式生命中,把像赤裸生命那样的东西隔离出来是永不可能的。
这里谈论的思想经验总是对某种共同权力的经验。共同体和权力不留余地地使一与他同一,因为共同体原则对一切权力的继承(内在于共同体原则的一切权力),是为任何共同体所必需的潜在特性的一种功能。在那些总是已经得到表述的存在,总是这样或那样事物、这样或那样身份/认同的存在,以及那些总是已经在这些事物和身份/认同中竭尽其力量的存在之间——在这些存在之间,除巧合和事实上的分离外不可能存在任何共同体。只有通过我们身上——以及他者身上——那尚为潜力(仍然潜在)之物,我们才能与他者交流,而任何交流(如本雅明在语言那里觉察到的那样)首先并不是共通物的交流,而是可交流性(communicability)本身。毕竟,倘若有且只有一个存在,那它必然是绝对无力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神学家们要确认上帝无中生有[ex nihilo]地创造世界,换言之,也即绝对不使用任何力量来进行创造。)在我有能力的地方,我们总是作为众人而存在的(就像在,如果有语言也即言说之力存在时,不可能有且仅有一个说这种语言的存在)。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政治哲学并非始于把沉思和沉思生活(bios theoreticos)变成一种分立的、单独的活动性(“从单一者到单一者的放逐”)的古典思想,而是从阿威罗伊学说开始的,也就是说,现代政治哲学,始于为一切人类所共有的单一且唯一可能的理智,并经过了但丁——在《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中——对内在于群体内部的思想能力的确证:
显然,人的基本能力在于理智的潜力或能力。因为这种能力不可能在个人或上文提到的那些特定人类共同体中得到彻底的实现,人类中就必然存在这样一个群体,通过它,理智的能力能够完全实现……从整体来看,人类的本职工作也就是不断地——首先,是在理论问题上,其次,作为理论的扩展,在实践上——锻炼理智成长的整体能力。[9]
我所说的那种扩散的知性(intellectuality)与马克思“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10]的观念只有在这种经验的视角内才有意义。他们如此命名天赋思想能力的繁多(multitudo)。知性和思想并非生命形式之一——在这些生命形式中生命和社会生产得以自我表达——毋宁说它们是把多样的生命形式建构为形式生命的那种归一的力量。在只能通过在一切语境中把赤裸生命与其形式分离来证实自己的国家主权面前,知性和思想是不间断地重聚生命与其形式或者说防止生命与其形式脱离的力量。在社会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纯粹的、大众的铭刻(一种作为当前资本主义阶段,景观社会特征的铭刻)与作为对抗性力量和形式生命的知性之间作出区分的行动——这种行动经历并完成了这种粘合与不可分离性的经验。思想就是形式生命,不可与其形式隔离的生命;这种不可分的生命出现的地方——它在身体进程的物质性中出现且以不是在理论中才有的生命的惯常形式出现——在且只在那里,才有思想。而这种思想,这种形式生命,这种使赤裸生命浸入“人”和“公民”——后者临时性地对之加以覆盖并用“人”或“公民”“权利”加以表征——的思想,必须成为未来政治学的指导思想和单一的中心。
(1993)
注释
*译自Gio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London: Minneapolis, 2000, pp.3-12。
[1] 英语的权力(power)一词在意大利语中对应于两个有区别的术语,potenza和potere(也大致地分别对应于法语的puissance和pouvoir,德语的Macht和Vermögen,拉丁语的potentia和potestas)。Potenza常令人想起潜力(potentiality)的含义和强力和力量的去中心化的或大众化的概念。另一方面,Potere指的是已经结构化或中心化的能力(capacity,身份)——通常是一种像国家那样的体制化装置——所具备的权威。
[2] 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和平的保卫者》(The Defensor of Peace),trans. Alan Gewirth(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6), p.15; 译文有变动。
[3] 参见扬·多玛:《生杀权:父亲,城邦与死亡》(“Vita necisque potestas: Le père, la cité, la mort”),载《论城邦中的惩罚:古典时代的身体酷刑和死刑》(Du châtiment dans la cité: Supplices coporels et peine de mort dans le monde antique)(Rome: L’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84)。
[4]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载《启迪》(Illuminations),trans. Harry Zohn(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9), p. 257。在意大利译本中,“紧急状态”被译作了“例外状态”,而这正是阿甘本在本文前半部分使用的术语,在阿甘本的其他著作——包括本论文集——中,这是一个关键的叠句(refrain)。
[5] 实验生命(“experimental life”)原文即英文。
[6] 例见彼得•梅德沃和让•梅德沃:《从亚里士多德到动物园:生物学的哲学辞典》(Aristotle to Zoo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pp. 66-67。
[7] 原文使用的术语与银行业务术语是一样的(因此这里的“赤裸生命”就是现金,被储存在像“生命形式”那样的账户之中)。
[8]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On the Soul),载《亚里士多德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vol. 1, ed. Jonathan Barne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682-83。
[9] 但丁:《论世界帝国》(On World-Government),trans. Herbert W. Schneider (Indianapolis: Liberal Arts, 1957), pp.6-7;译文有变动。
[10] 英文原文如此。该术语出自马克斯的一条注释,在这条注释中他用的是英文。见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trans. Martin Nicolaus(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p. 706。
本文转载自豆瓣阿甘本小组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2070586/
如您观文后有所感悟,欢迎关注并分享“三会学坊”。
尊敬的畅言客户,您好。您所使用的网站评论功能已广告作弊被限制使用,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电话400-780-9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