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保罗·柯文
翻译:张隆志
这篇新版序言是改写自我数年前为论文集China Unbound所撰写的导言。将该书结集出版是一次难得的挑战。一方面是重新回顾我数十年前的旧作品,提醒自己作为历史学者的求知甘苦历程。另一方面则给予我反思自己历史研究的机会,发掘若干我的老师史华慈所说的深层预设(underlying persistent preoccupation)。这些议题自我开始写作即以不同的方式延续至今,另一些议题则在之后出现在不同的研究阶段。换言之,这个练习使我对于自己思想发展中变与不变的部分,有了更清晰的图像。
虽然我大部分的学术研究均聚焦于十九及二十世纪,因此几乎难以避免地需要处理中国与西方(以及受到西方影响的日本)间的互动。持续不变的关怀是我决心进入中国内部,从中国人自己的经验重建其历史,而不是根据西方人觉得重要、自然或正常的角度。简言之,我希望能超越过去承载着沉重的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假设的中国研究取向。此一立场的早期范例是我的第一部作品《中国与基督教》。我在该书序言中明确地远离旧式中国传教史以及其“关注传教而非中国”的焦点。随着二战后中国研究的逐渐成熟,此种西方中心观取向的缺陷更加显著,而以我的另一位恩师费正清为先驱的另一种新取向,“更关注于理解及评价基督宣教活动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这也是我在第一本书所采用的研究路径。

保罗·柯文
这个起点最后成为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在《中国与基督教》一书的最后一章,我初步勾勒了下个步骤:批判地检视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取向(此一取向与费正清关系密切),它在战后数十年来深刻影响了美国学界对于十九世纪中国的论述。我写道:“现代中国研究者常过分聚焦于西方冲击与中国响应的过程,以至于忽略相反的发展:中国影响与西方反应。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发现他必须面对意想不到的挫折与敌意,并因此逐渐被转变成一位“外籍”传教士。传教士对于此一转变的觉悟(或可说是憎恨),结合了他对中国事物的根本不满……严重地限制了他对于中国环境的响应。”换言之,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取向过分简化了历史,它假设十九世纪中西互动是单向地由西方流向东方。
数年后我在一篇论文中更系统性地检讨冲击-响应取向,并尝试指出若干隐含的基本假设。其中一个内在倾向是将任何十九世纪中国的变迁,都视为西方冲击的结果。此一预设也成为19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学界研究倾向的一部分,亦即在看待中国数百年历史时,否定其出现重要内在转变的可能性。虽然我直到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时,才对此议题进行更详尽的检视,但如今回顾起来,我在十多年前撰写晚清改革者及先驱报人王韬的思想传记时,便已开始朝此方向前进。由于王韬毕生致力思考关于变迁的复杂性,我在理解他生涯的过程中自己也必须面对这些课题。在本书讨论王韬的四篇前言中,我触及了有关变迁的几个大课题,例如渐进转变与革命的关联、从内部观点评估社会变迁的优点、传统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中国传统与实际历史发展的差异、技术变迁与价值改变、十九与二十世纪中国变迁的地理文化资源等。我后来逐渐了解到虽然自己已经开始进行反思,但在该书大部分的讨论中,仍存留着过度强调西方因素作为衡量晚清中国变迁主要标准的倾向。我在本书的英文平装版序言中,指出了此一倾向的结果,尤其是对于王韬一书最后一部分的影响。
在王韬一书中已经显现的,对于包含我自己在内的西方中心取向的逐渐不满,让我在1970年代晚期开始更为广泛地批判这些倾向对于战后美国学术的塑造作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便是此工作的成果,我在前三章探讨了西方中心的偏见,指出三个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要概念架构: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取向,现代化(或传统与现代性)取向,以及帝国主义(或更为明确的帝国主义与革命)取向。并在最后一章讨论美国学界的新研究趋势,我称之为中国中心取向。此一取向出现在1970年前后,并努力地克服早期的西方中心偏见。在本书平装本再版序言中,我响应了学界同人对于中国中心取向的若干批评。在本文中我想以中国史研究的新近发展为例,讨论中国中心取向的可能限制。
中国中心取向的核心特色是研究者致力从中国自身的观点来理解中国历史,尤其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以及中国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避免源自于西方历史的期待。但此一立场并未忽视外来的影响,也不排斥(相反的是更加欢迎)将非中国的(通常来自其他学科而非历史)理论洞见及方法策略,应用于中国的现实状况。只要这些洞见与方法能够敏感于狭隘地域偏见(典型的西方中心)的危险。
直至今日,我仍未改变上述论点。我认为中国中心取向在许多中国史研究议题上,仍是适切而可行的。但另一方面,中国中心取向的优点,在某些议题上则未必如此明显。我脑中浮现的是几个新兴研究领域,它们虽然与中国史相关,却更适合从其他角度加以讨论。其中有些是属于比较历史性质或从世界史观点的提问,有些是从东亚或亚洲区域体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有些虽然处理中国历史,但其关心课题则超越了国别史,有些聚焦于中国境内非汉族群体的行动思想(与自我认知),有些则是着重关注迁移至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上述学术领域(无疑还有其他课题)均对于何谓“中国历史”的边界,乃至于何谓“中国”的定义提出疑问。不可避免的是,上述研究也因此以各自的方式对于中国中心取向的适切性提出挑战。
对中国史研究者及其他领域学者而言,近年来最为重要且具影响力的比较历史成果,是王国斌(R.Bin Wong)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作品。尤其是前者的《转变的中国》[China Transformed(1997)]及后者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2000)]两本论著,处理近两百年西方的全球优势等复杂课题。王彭两人间有显著的不同。彭专注于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而王则将视野延伸至国家形成与民众抗争。进而言之,彭提到他自己更强调“全球趋势及相互影响,并将欧洲和中国以外的区域带入讨论。”而王则持续而深入地进行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历史研究。然而两位学者间的共同点比其差异更为重要。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均赞同过去西方对于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所进行的比较都提出了错误的问题。受限于十九世纪社会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他们均以欧洲所发生的变迁轨迹为假设规范,如果诸如工业革命等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那么应要探究的问题是中国的案例出现了什么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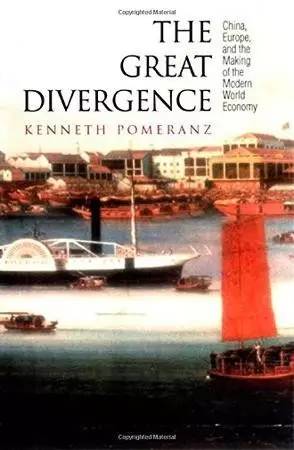
《大分流》英文版
王彭两人正面挑战上述研究,并坚持进行双向比较的必要性。王采用“对称观点”(symmetric perspectives)来描述此一过程,彭则使用“相互比较”(reciprocal comparisons)一词。两位学者在讨论历史变迁时,不再受限于欧洲中心的规范性假设。在探讨十八世纪后半叶欧洲和中国的经济状况时(彭主要讨论部分欧洲、中国、印度和日本区域),他们发现显著的类似现象。王国斌提到:“十八世纪欧洲在关键部分与同时期中国的类似处,远比十九及二十世纪的欧洲更为明显。”而彭慕兰也从较复杂的空间观点提出类似的说法。他指出十八世纪中叶“在旧世界的数个核心区域,包含中国长江区域、日本关东平原、英国与荷兰、古吉拉特等地,彼此均具有若干关键特征,和周边其他大陆及次大陆地区有所不同。例如相对开放的市场、普遍的手工业、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等”。基于此时期部分欧洲与亚洲区域在经济状况方面的共同性,王彭两人的关注焦点不再是亚洲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何种因素导致欧洲从英国开始至其他核心区域,在1800年后出现了划时代的经济变迁,但并未发生在亚洲大陆经济高度发展的区域。虽然两位学者在响应此问题时,均赞同英国的技术创新及新能源转换(煤)具有关键重要性,王国斌同时强调发展中欧洲政治经济的若干结构特征具有解放功能(如国家间的彼此竞争),而彭慕兰的解释则更为重视欧洲以外的因素,尤其是新型贸易体系及新大陆带来的意外财富与资源。
虽然王国斌曾宣称他的著作“基本上是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专书,其次才是一本关于欧洲史的作品,”而在讨论中国历史时他非常留意避免带入欧洲史的盲点。我则认为“中国”并非本书的主题,而本书的首要贡献和学术价值在于审慎地提出并说明一个崭新而更为均衡的比较历史研究取向。它并不偏重世界某一特别区域的历史发展,也因此避免我们用先验的假设来看待各区域的历史。彭慕兰的研究则较少强调比较(虽然他的研究空间范围比王国斌广阔),而更专注于欧洲与东亚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不同经济发展轨迹。虽然彭提到“当我们不再将中国从作为欧洲的假想对比解放出来时,她的发展将呈现新的风貌……而当我们看出欧洲经济和其时常比较的对象间的相似点时,对欧洲的历史也将有不同看法”,但他的首要目标是探讨现代世界经济如何出现的核心问题。彭慕兰因此和王国斌一样,虽然认真讨论中国并努力呈现其真实风貌,但其根本关心的课题则超越了中国历史研究。
要将诸如王彭等人的世界史论著(无论是比较研究或探讨趋势和影响)冠上中国中心的标志,看来是明显不恰当的。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那些将中国视为广大亚洲区域体系一环的研究。区域作为个别国家和世界之间的中级范畴,具备其自身的历史动力,也必须(如同其研究者所言)从区域中心的观点加以检视。代表学者例如滨下武志,希望我们“将东亚视为由历史过程建构的区域,具备其自身的霸权结构”。“它并不是因为欧洲列强到来才进入现代,而是由于传统中华朝贡体系的内部动力。”朝贡体系由中国创始于数世纪之前,是个包含东亚和东南亚的宽松政治结盟体系。中国及其藩属国家的关系不仅止于两国之间,更常包含了卫星朝贡国间的关系。例如越南接受寮国的朝贡,朝鲜是中国藩属但也遣送朝贡使节到日本,而琉球国王在中国清廷/日本德川时期,同时和江户及北京建立朝贡臣属关系,因此形成了复杂的区域关系网络。
根据滨下的研究,亚洲区域体系的另一个关键特质是经济。一个多层次的贸易关系网络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拓展,和朝贡体系共同运作。并与中国商人向东南亚的经济渗透以及华南劳工的移出过程密切相关。“朝贡物品和‘礼物’的关系实质上是商业买卖关系。”而商品价格“是宽松地由北京的市场价格所决定”。他指出事实上从晚明以来“整个复杂的朝贡贸易体系的基础,是由中国的物价结构所决定。而朝贡贸易区域形成一个以白银为交易媒介的完整‘白银区’。朝贡贸易作为一个体系的运作关键,是中国以外区域对于商品的巨大‘需求’,以及中国内部与外部的价格差异。”滨下赋予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要性,是他与早期费正清和其他学者讨论朝贡制度作品的明显不同之处。
虽然中国无疑是滨下区域中心观点的基础(他也常用中华中心[Sinocentric]的词汇来描绘),从前文讨论可以看出中国中心观并不适用于理解他所讨论亚洲区域体系。此点在滨下另一部分的分析中更为明显,他进一步提到海洋作为亚洲历史活动的焦点与决定因素,具有和陆地相等的重要性。虽然我们习惯将亚洲视为陆地疆域单元的组合,但它同时也可被视为从东北亚一路延伸至大洋洲的一个相互连接的海域(maritime regions)。滨下敏锐地指出,当我们采用此一海洋中心的地理观点时,将较容易理解为何亚洲各地间的政治关系数世纪以来是如此发展。“位于各个海域周边的国家、区域与城市间的邻近距离,足以彼此影响,却无法同化成一个较大的单位。在此意义下自主性成为建立一个宽松的政治整合形式,也就是所谓朝贡体系的主要条件。”

关于非汉族群体的研究亦指出了另一个中国中心观史学较无法处理的学术领域。此类研究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一群人数虽少但极为出色的历史学者,近年来为清帝国的满州性格问题注入了新活力。探讨的议题包括满人文化与民族认同的长期变迁、清代边疆的特殊性格、满人统治的多重型态及其对于清帝国经营的贡献、重要的清朝制度(尤其是八旗),以及满人对于二十世纪民族主义的影响等。这些学者常以满文资料补充中文文献,并犀利地挑战多数满人已被“中国世界秩序”吸收或同化的传统成说。如同其中一位指出的,他们的多数共识是“满州差异的重要性持续了整个清代”。而其他人则用“清代中心”和“满州中心”等词来凸显此一重要差异。他们的主要论证并非否认满人是中国历史的重要部分,而是帝制晚期的中国从满州视角而言将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从传统同化或汉化模式等汉人观点来看待满人的历史角色,将导致与从西方中心观点看待中国时相同的扭曲和偏见。
造成清代满州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朝是一个征服王朝,并在此时期将中国与中亚等地纳入其势力控制。至于其他非汉人群体如中国回民的案例,则是另一个故事。中国穆斯林课题也对于中国中心研究取向的适切性发出质疑。但由于他们数百年来的经验与满人有极大不同,研究问题的性质也有所差异。其中一个差异是中国穆斯林虽然也曾担任政府高层官员(尤其是在元朝),但并未如同满人和蒙古人那般成为统治中国的群体。另一个差别是中国穆斯林自过去以来,便持续以不同程度和方式与宗教维持联结,而回教是个非中国起源的世界性宗教。
如同杜磊(Dru Gladney)和李普曼(Jonathan Lipman)所坚持主张的:中国不同区域的穆斯林(甚至在同一个省)彼此也有许多差异。
有鉴于中国穆斯林人群的异质性,在理论上而言,虽然中国中心取向应用于新疆说突厥语的维吾尔族可能造成误导,但仍应适用于已经汉化的中国穆斯林。此一取向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将极为复杂多样的中国世界分成较小而可处理的空间单位,以便仔细探究地方差异的各种面向,包含宗教、族群及社会差异。然而结果是,即使对于说汉语的穆斯林而言,中国中心取向仍然出现问题。李普曼在讨论十九及二十世纪甘肃地方的个案时,提供了关于回民复杂性的生动分析。兰州是此时期甘肃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国主要的经济生活重心。但兰州因位于两个穆斯林空间的边缘:一个是宁夏,另一个是河州。从穆斯林的观点而言,则是边陲地区。相反的,位于兰州西南六十多英里的河州,虽然对于穆斯林而言是个主要的商业与宗教中心(在十九世纪拥有超过半数的回教人口),在所有的中国中心观点的地图上“仍被视为边陲地区的边陲”。换言之,中国中心观点的地图并未充分关注甘肃回民的社会、经济及宗教的重要面向。除此之外,它更大的缺点在于呈现出一个毫无差异的甘肃回民社会,抹杀了其成员的多样性。如李普曼清楚地指出,甘肃境内不同地区的穆斯林(在中国各地更是如此),事实上在社会及职业分布方面有广泛的差异,相对于国家则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有时彼此间会出现暴力冲突,在宗教热诚的性质和程度上更不相同。
上述满族和穆斯林的新研究作品,与近年来中国对于民族(国籍或族群)的整体学术关怀有关。由于中国边境汉人与少数民族间紧张关系的刺激,部分受到全球对于多元文化与多族群议题兴趣及关切的影响,此一学术关怀展现在有关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彝族及其他族群的著作中。就其对于透明而毫无疑问的“中国性”概念的挑战而言,它将此范畴复杂化并迫使我们继续重新思考其含义,可以理解此一研究对于中国中心式的分析并不十分友善。
假如中国中心取向无法充分处理中国境内非汉族社群的特殊观点及经验,它在处理迁出中国境外的汉人移民时也出现问题。这也是近年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议题。中国海外移民是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学者们如今才开始重新进行概念化的工作。它的主要特征来自于广泛(及先前的)中国国内迁移的模式。就迁移过程“推力”部分的焦点而言,注重地方特殊性与差异性的中国中心分析,对于理解从某一地点迁移的有利决定因素(无论是国内或海外),均具有潜在的价值。但即使在此阶段,我们也开始遇到问题。虽然在十九及二十世纪,华北及华南各地均出现地方贫困与社会动乱,但海外移民大部分源自于南方福建、广东的特定区域,而非来自中国北方。此一现象的主因是这些地方能进入若干南方贸易港口尤其是与英国殖民地香港高度发展的华人网络。用冼玉仪(Elizabeth Sinn)的用语,这些“中介地区”(in-between places)作为转运或枢纽,让人群、物品、汇款甚至死者的骨灰,可以在华南村落与全球各地之间流动。运用此种迁移的网络,成为华南部分地区家族(有时甚至是整个村庄和宗族)的首要经济策略。它也是前文所说的区域与全球体系的重要环节。
在讨论迁移过程时,中国中心取向作为唯一甚至基础理解途径的用处明显地减弱。其主要原因当然是中国与外界有着重要的连结。当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爪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秘鲁利马和普利托利亚等地定居,无论是暂时或永久,即使他们保持中国社会与历史记载的重要生活方式,他们也同时成为印度尼西亚、美国、秘鲁及南非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对于不同环境的适应不但因地方而异,更随着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孔飞力使用“历史生态”描述的此一过程,是无法用单一国家或文化的观点加以理解的。但如何理解多元地域的复杂性,只是中国中心分析的部分问题。如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有力地说明,要完整地理解华人移民,以国家为基础的观点(无论是以中国、美国、印度尼西亚为中心等),必须辅以强调移动及分布的研究,“以关注连接这些较为地方性参考基点的全球性连结、网络、活动及意识。”换言之,迁移并非只是推力和拉力的因素,也不只是移出地和迁入地,而必须被视为一种过程,包含了在稳定建构并密切连结的移民管道间持续往返的移动。正因如此,移民对于既有的国家疆界具有强大的颠覆作用。
中国中心取向的适切性在某些直接而广泛地与中国历史相关的个案中,也出现质疑。我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1997)]便是一个良好示范。我的确在本书的许多篇章里,持续努力地进入1900年春夏期间义和拳民及其他华北平原中国居民的内在世界。就此方面而言,我的研究可以被视为中国中心取向。但我同时(虽然比重较小)也有兴趣理解事件发生时在华外籍人士的思想感受及行为,并时常指出中国人与外籍人士之间的共同点。在某些重要时刻,我的研究取向是更以人为中心,而非只是中国中心(我稍后会再说明此论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如同我一直说明的,本书的主旨是探讨有关历史书写的一系列广泛议题,“以义和拳民作为此一更重大工作的仆人”此一做法与正规的历史研究非常不同。在中国研究及其他领域的作品里,作者通常都会在结论时将他们的发现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参考架构,借此强化其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历史三调》里我则是以一系列大问题为讨论起点,并且未曾放手。本书虽以义和团为延伸性的个案,但我更进一步地在结论中指出,义和团与全书探索的重大议题之间,并不存在必然与排他性的连结。世界史上许多其他故事亦可扮演同样的角色。本书的主要目标并非中国历史,而是关于历史书写的一般性课题。因此也并未特别强调中国中心的观点。
前文所讨论的研究课题,均对中国中心取向提出质疑,有些例子要求放弃使用它,但更多的情况是将它更为细致地与其他的研究取向相互结合。当四分之一世纪前我初次提出中国中心取向时,我明确地将它与研究中国的过去相连结。我急切地(从当时的观点)强调自己所进行的工作,是将其他学者已经开始使用的一套研究策略加以连结及命名,并认为这对美国的中国研究而言是个合适而值得庆幸的走向。事实上《在中国发现历史》书中章节介绍此一取向时,我使用的标题是“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只要学者选择的题目是明确地以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学术、文化与宗教)脉络为核心时,我认为中国中心取向仍是非常有用的。即使就近年来学界的新发展趋势而言,此点对于大多数中国历史作品也仍然属实。困难发生在当我们进入我在前文所讨论的各个领域,例如将中国去中心化地放在跨国性的历史过程(如海外移民、现代世界经济的出现、亚洲区域体系的演化),或者更为一般性的学术议题(如理解过去的多重方式、比较历史的研究),或者将中国从物理性空间转化为其他事物(如最近流行的去领域化等词汇),以及将中国问题化的其他方式(如中国境内非汉民族与海外华人移民的自我认知等)。
上述研究方向虽然对于狭义的中国中心取向提出质疑,但对于更为广义的中国历史研究则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其中几种具体成果如下:移除数百年来关于“中国”概念的人为障碍(包含中国人和西方人);颠覆对于中国过去的狭隘认识(由中国人及西方人一样所提倡);深化理解“中国”在不同地方及时间所代表的复杂意义;更为均衡地(而少带偏见地)比较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弱化西方长期以来将中国视为主要“他者”的认知方式,破除“东方”与“西方”式武断而误导的区分,进而能够以更具人性而非异国情调的观点,重新看待中国及其人民与文化。
我希望再次强调上述最后一个论点,因为它越发成为我自己的重要研究关怀。我特别指自己对于西方人过分夸大中西差异所抱持的怀疑,这些夸大宣称时常是(虽然不是不变地)根源于西方中心的观点。我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认真看待文化(包括我在本文后半段会讨论到的最新作品),也绝对不会否认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差异。但此同时,我相信过分强调此差异的历史研究将容易导致不幸的扭曲,即使是以某种幽默讽刺的方式加以表现。其中一种扭曲形式是文化本质论,将文化过度化约成一组其他文化无法体现的特殊价值或特征。例如对于威权主义东方与自由宽容西方的刻板印象,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精彩论证所指出的,无法提供理解印度或中国历史也拥有宽容或自由的传统,以及威权主义亦有其西方自身历史来源的可能性。然而真实的历史记录完全否定了这类传统成见。事实上“当讨论到自由与宽容时”,森指出更合理的分类方式是以观念内涵为优先而非文化或区域,“将亚里士多德和阿育王分在一组,而将柏拉图、奥古斯丁及考底利耶分为另一组”。
当历史学家去尝试理解另一个文化的人民时,常会过分注意文化间的差异。除了因此更不易理解该文化组成中复杂乃至相互矛盾的元素,以及其所经历过的长期转变过程外,也将遮盖该人民的思想行为中所反映的跨文化的内在人性特质。这些是与世界其他地区人民重迭或产生共鸣的思想与行为。我认为此种普遍人性的面向,必须与文化差异共同讨论,才能对中国的过去有更为完整立体而较不偏狭的理解。此点也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方式,让我们能穿越西方与中国历史学家以不同方式与原因,在中国及其历史周围时常留下的边界。
虽然我初次接触中西文化汇流或共振的概念,以及其所可能反映的基本人类心理倾向,是在四十多年以前出版的研究王韬的论文。我直到开始关于义和团的研究,才真正深入探讨此问题。在《历史三调》一书中,我不断利用跨文化比较,将义和拳民的思想及行动加以自然化或“人性化”。并在过程中扩大中国的“他者”范围,从西方延伸至非洲及世界其他区域。其中一个例子是我在讨论1900年春夏义和团事件高峰期间华北的谣言与集体恐慌。当时最为普遍流传的谣言,是指控外国人和华人基督徒在各村落的井里下毒污染水源。“井里下毒的指控”根据当时人说法,“几乎是无所不在”,并引发一般民众对基督徒毫无理性的狂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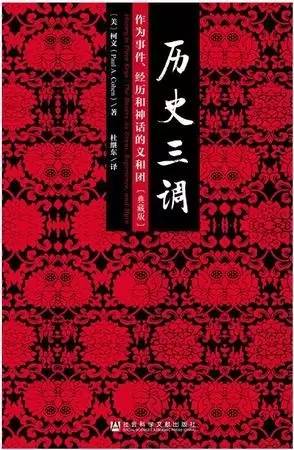
在这个例子里有趣的问题是恐慌的内容:为何是集体下毒呢?而且是特别针对公共水源下毒?如果我们接受谣言可以传达信息的说法,特别是谣言的散播提供了关于社会危机与集体恐惧的重要象征信息,那么回答上述问题的途径之一,便是尝试确认谣言恐慌与即时背景的对应关联。例如对于绑架的恐惧,在中国及许多其他社会均有长期的流传历史。社会集体关注的焦点是孩童的安全(如同kidnap一词所隐含的),孩童几乎总是被视为首要的被害者。另一方面,公共下毒的谣言则合适作为对于战争、天灾或瘟疫等危机的象征性响应,因为它们对“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具有潜在的威胁。
从其他社会的经验更可以确认上述看法。在井里下毒和类似犯罪的控诉,曾被用来指控罗马帝国的早期基督徒和中古黑死病时期(1348)的犹太人。在1832年黄热病蔓延的巴黎,曾流行着有毒粉末被散布在面包、蔬菜、牛奶及饮水的谣言。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交战各国间也散播着敌人间谍正忙着在公共供水系统下毒的谣言。在1923年9月1日东京发生大地震的几个小时之内,关于朝鲜人和社会主义分子的谣言便开始散布,说他们不但纵火还阴谋叛乱,并在井里下毒。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新闻则指控汉奸在上海的饮用水里下毒。而在1960年代后期尼日利亚内战时,关于毒害民众的谣言也在比夫拉地区蔓延。
在上述许多例子里,谣言均针对外来者(或他们安插的奸细)。以直接或影射的方式,指控他们试图消灭谣言所传布的社会。此点看来十分类似义和团事件当时中国的情况。如同指控那些挑战中国神祇权威的基督徒需为1900年春夏华北的干旱负责,关于外国人及其中国属下在华北供水系统下毒的谣言,将外来者描绘成剥夺中国人生活必需品的象征。井里下毒谣言的蔓延,因此直接唤起了当时一般民众心中最深刻的集体恐惧,也就是对死亡的畏惧。
让我重述2001年夏季关于义和团事件的演讲,来总结前文对于过度强调文化差异所产生问题的讨论。那次演讲有个与众不同(对于大部分是西方人的听众而言,有些挑衅性)的题目——《将义和拳民人性化》。我所采取的立场是文化除了作为人类社群表达其思想与行动的棱镜,也可能造成不同社群的疏离,促进刻板印象,歪曲嘲讽及制造神话的过程。有鉴于义和团在二十世纪于中国及西方所遭受的过度扭曲,我在该次演讲特别聚焦于义和拳民们与其他文化的人们,在面对类似历史挑战时所共同经历的事物。我的论证要点并非否认义和团及其文化特殊性(当然,也不会过度美化他们),而是将他们从去人性化的特殊主义中拯救出来,这类特殊主义从开始便误导并扭曲了他们的历史。
文化差异与内外二分对立的概念十分相关,两者都有许多不同的表达形式。如同前文所言,这个议题是我学术生涯的核心关怀。我在总结《在中国发现历史》平装再版的前言时,曾提到历史写作时的“局外观点”(outsiders perspective)。虽然在该书最后一章认为外部性及其某些形式较为无害,但我始终将它视为“一个问题,对历史研究而言是负担多过资产”。某些评论者不同意此观点,指出在某些情境下,局外人(如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可能反而比局内人(研究自己历史的中国学者)具有某些优势。在写作《历史三调》一书过程中,我仔细反思了对于过去的直接体验(最为重要的内部观点),以及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的事后重构(不可避免的局外者)之间的差异。我逐渐接受上述批评,承认历史学者的局外性虽然是个问题,但同时也是让我们与历史当事人有所不同的关键。此一差异让作为历史学者的我们,可以提供历史当事人所没有的认识观点及意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最近的作品《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Speaking to History:the Story of King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可以作为此一真理的最终示范。这本书讨论东周后期东南越国国王勾践的故事,如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被重新述说。它也讨论更为宽广的历史问题:为何人们在集体或个人生命的某些时刻,会特别被历史故事所吸引?这些叙事通常都是来自遥远的古代,但与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境产生密切共鸣。勾践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年轻的国王,他在惨败于主要强敌吴国后,在吴国担任三年的囚犯与奴隶。在获得吴王对他忠诚的信任后,勾践终于获准回到越国。他决心要复仇雪耻,以二十年时间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富国强兵。最后在辅佐高臣的支持下勾践发兵攻吴,吴王自杀,吴国灭亡,一雪前耻。
勾践的故事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学童而言,就如同美国青少年对亚当与夏娃或戴维和歌利亚的圣经故事一样耳熟能详。另一方面,虽然它在中国文化世界中有深远影响,对美国(非华裔)的中国近代史学者而言却十分陌生。显然易见,这个故事是一种文化知识的建构,存在于每个社会。也是每个在此社会成长受教育的成员(局内人),自幼接受灌输的文化素养。但对于局外人而言,他们对此文化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书本或成年后的短期居住或旅行经验,从未接触或注意到此类故事。由于此一特别的情境,美国(及西方的)历史学者作品中,完全忽略了勾践的故事在过去百年来中国的流传过程。
和美国学者不同,中国的学者均十分熟悉勾践的故事,也非常了解它在二十世纪的广泛流传和引用。如一位中国同事最近对我所说的:这个故事深植在“我们的内心”。但我也发现中国学者很少将勾践的故事和其本身历史间的关系,视为值得严肃探讨的课题。我推想其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均已经接受此故事与其历史间的关系为既成事实。他们从小便被灌输以古鉴今的观念,因此也直觉地从此类故事中寻求历史教训和指引,却很不容易退一步思考,客观地探究故事与历史间的重要关系,无论对中国或其他文化均是如此。
经过上述讨论,Speaking to History一书的讽刺性质现在应十分明显。没有比一本探讨中国历史故事的影响更为中国中心的作品,但此一深植于中国文化并广为中国人熟知的故事,却很少为局外人所认识。此现象可被称为中国中心特征的极致。但与此同时,对于像我一样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而言,当知道这个故事及其对二十世纪动荡中国的重要影响时,自然会从另一个层次提出更为宽广的(非中国中心观的)问题:为何一个民族会从历史故事的视角来理解当前的现实经验?
虽然历史故事(或借故事来回顾历史)在中国似乎非常普遍,但在其他社会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举出以下鲜明实例:象征犹太人民宁死不屈的牺牲精神的马萨达(Masada)神话,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数十年间广泛流传;二十世纪后期的塞尔维亚人对六百年前他们祖先在科索沃战役(the Battle of Kosovo,1389)壮烈牺牲的追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07年3月亚拉巴马州塞尔玛市(Selma,Alabama)演讲时,采用圣经式历史叙事描述美国民权运动,并视马丁•路德金等先驱人物为“摩西一代”(他们为民权运动奋斗牺牲,但并未渡河看到应许之地),而他和同辈则是承先启后“约舒亚一代”。
上述在(古代)故事与(当前)历史间的彼此回响,对历史研究而言极为重要。另一方面,它是个极为复杂的现象,深刻反映了个人、社群乃至整个民族如何置身历史记忆之中。面对历史记忆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和差异。奥巴马对美国民权运动(与他个人在其中的位置),以及圣经里从摩西到乔舒亚的传承过程的理解,与二十世纪中叶犹太民族对马萨达神话的积极关注有非常大的不同。但在这些案例中有一个持久的共通点,也就是当代人们通常从远古重述史实基础十分薄弱的事件中吸取了神秘力量。
这种非常普遍却未被充分理解的力量,值得历史学者们更加注意和关切。我在Speaking to History一书里指出勾践故事与当代中国历史的多重关联,可以作为更广阔学术讨论的起点。但如要对相关议题有更完整的理解,中国历史需要结合犹太历史、塞尔维亚史、美国史及其他各种历史来进行讨论。如同前文所指出的,中国历史研究的边界正在被翻转。而我们也面对着最后一项悖论:在二十世纪从中国中心观点深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过程中,局外人视角对于认识故事与历史关联在人类经验的普遍性与重要性而言,也许曾是必要的。但当我们达到此目的时,由于文化特殊性的重要性已降低,过去对于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区别,也很可能将不再如以往那般明确了!
本文是柯文先生为新版《在中国发现历史》所写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