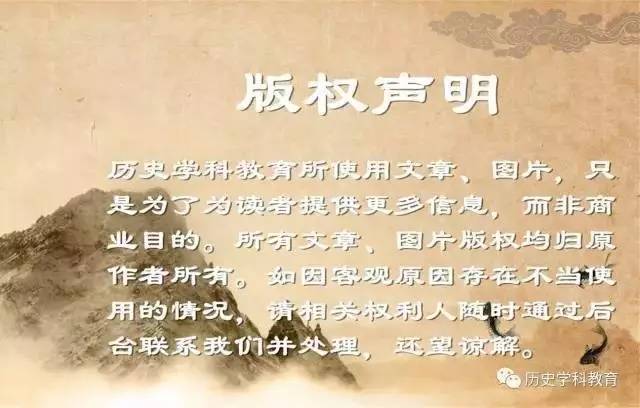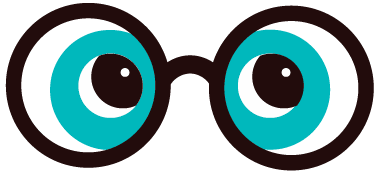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电脑技术与互联网事业的飞速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这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学术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还在日益扩大。其中与文化、学术事业直接关联的电子文献和电子文献检索,一经产生,就对延续千年的图书馆工作造成很大的挑战,不得不直面应对,做出电子资源方面的建设。对此,学术界已经多所讨论和采取了不少措施。本文不拟分析上述较为宏观的问题,仅从中国历史研究者个人运用电子文献检索和史料查阅的角度,谈谈其学术上的功能和利弊。
1
一
1
历史研究的对象,主要针对的是以往发生过的社会状况、文化情景及人物事迹,而不是正在变化着的现实与未来,因此所利用史料的范围,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圈定,有利于电子文献和互联网资源发挥出显著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由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极其兴盛,历代的积淀而形成了多种系列的史籍文献,十分方便于大型电子文献和数据库的制作,“四库全书”、“二十五史”、“四部丛刊”等等,都较早地形成了电子文本、电子数据库资源,对历史研究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觑。
凡是不直接使用纸质或其他实物材料文本,而是利用电脑查询、阅读的图书、文献、资料,可以暂且概称之为图书文献和资料的“电子资源”,对于中国历史研究而言,按其内容体系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是电子文献数据库,例如当下广泛使用的“四库全书”全文数据库、“二十五史”全文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库、“四部丛刊”数据库等,数据库多为上网使用,也可以独立安装在电脑上。其主要特点和优点是可以作“字串”的检索,所谓“字串”,是由若干字符(包括单字)联结而组成,可以是词语、概念、命题等,也可以是自行设计的文字匹配,这极大地方便了历史资料的搜集。例如在“四库全书”电子数据库检索“史学”一词,“四库全书”内所有古籍中凡有“史学”词语者会全部显示出来,即可获得历朝历代谈论史学的资料。第二是电子版的图书与文献,乃根据某种纸本的图书文献扫描或电脑输入而形成,有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多种传播途径。第三是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随机搜寻资料和信息,这样的信息即使在学术范围之内,也五花八门,缤纷多彩,未免庞杂,但可以阅读、下载很多书籍文献,复制不少文章,还有大量纸本报刊见不到的学术主张,披沙拣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历史研究由于电子资源的扩展,带来划时代的巨大变化,这表现为四个方面。
1.书籍、文献、学术信息的查阅和史料的搜集空前便捷,逐步打破以往研究资源保存在不同地区、单位和团体的严重不均衡状态,挑战史料和信息的垄断行为,使历史研究较为普及、较为公平地展开,可望促成史学界学术队伍结构和学术机制的良性演化。
2.从研究方法上冲击传统的治学方式,例如原先手抄资料卡片的方法,会渐少应用,因为检索和存储电子版原文更为便捷、可靠。纸本的专业文献目录书籍,也会被电子版逐步取代,因为这样更便于查找。在治学上,从头到尾认真阅读的专业著述将会更加集约、凝练和精要,许多史书会被列于随机检阅、抽读、选读的对象。
3.启发新的探索、新的思维,使研究成果更为多样和丰富。由于电子资源对史料的检索效率高、速度快,可以短时间完成过去阅读、摘抄方法难以承担的工作,就使研究的选题眼界大为开拓,特别是在探索长时段经济资料以及梳理某种事物、观念、语汇的历代源流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4.在当下史学界,年龄较轻的学人具有利用电子资源的较大优势,这是因为历史学的电子资源无论是在技术水平抑或覆盖范围上,都处于不断提高和扩展的进程之中,并且与电脑技术的进步、网络布局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年轻一代较早地得到电脑技术的学习和锻炼,更具有乐于接受新事物的趋向。
以上四个动向,各级学术研究的主管部门需要有清晰的了解,以便提高前瞻性,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史学研究者个人也需要认清趋势,加强相关的学习和锻炼,以免过度地落伍于时代。

二

历史学的电子资源是社会公共产品,但学者的具体运用则非常个性,每个人有不同的侧重、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体验。对于学术性电子资源运用的日益扩展,毁誉参半者有之,忧心忡忡者有之,然而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挡这一趋势的发展,我们应当积极掌握这种治学方法,更应当促进整个社会的学术性电子资源建设。
近年历史学科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可以说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电子版图书、文献,都以电子检索搜集资料和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甚至可能将电子资源作为主要依靠的对象,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手段具有极高的效率,可以节约时间和经费。这给指导教师提出一个挑战:为了审核、批阅学生的学术论文,导师必须也具有对电子资源一定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否则很难发现其中的讹舛、误读甚至可能存在的不端现象。而将这些问题阻遏于萌发之际,是非常重要的。
推而广之,对于史学界一些流行的观点,一些似成定论的见解,在互联网信息日益发展、电子资源越加丰富的条件下,也应当重新予以审视,因为学术信息的获得、史学资料的搜讨大为便捷,提供了重新探讨的有利条件。例如雷海宗先生的文章《司马迁的史学》(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6~242页),全盘否定司马迁的史学成就,虽会引起人们质疑,但文中指摘了《史记》一书的许多讹误,也可能令人觉得雷文还是有所发现。而在电子文献资源相当丰富的现在,只要稍作检索,便可识破这些指摘《史记》讹误之处,绝大多数是雷海宗先生照抄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而来,余下几条分别抄自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清顾炎武《日知录》等等,一概未注明来源(详见乔治忠:《雷海宗学术评价问题新议》,《学术研究》2014年第1期)。在缺乏电子搜索手段的过去,这种底细很难完全摸清。
雷海宗先生又在同一文章中,贬斥司马迁文笔拙劣,凡描写生动之处,都完全是抄袭了汉初陆贾的《楚汉春秋》,认为“全部《楚汉春秋》除次序的变动外,大概一字不改被收入史公的作品中”(雷海宗:《伯伦史学集》,第236页),而《楚汉春秋》早已佚失,那么在《楚汉春秋》佚失之前是否有过这种说法呢?经利用电子资源搜讨资料,可以确知自古以来绝无一人批评司马迁文笔不佳,相反,“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篇末赞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连谴责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的汉明帝,也承认“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班固:《典引·叙》,载《东汉文纪》卷一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如果司马迁真的只靠抄袭《楚汉春秋》骗取文名,汉帝与御用学者岂不予以揭露?焉能交口称赞司马迁的文才?至于说《楚汉春秋》被“一字不改”抄入《史记》,更是无稽之谈,《楚汉春秋》一些内容现在还残存于《史记》“三家注”中,检索结果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没有被《史记》全部录用。
目前有些机构,为了检验研究生学位论文与学界已有论述的“重复率”,已经利用电子技术制成专门的软件,效果明显,这在原则上也应当适于检验任何学者,若此,当能有效地净化学术风气。
笔者曾经主张,中国史学史研究,不能现成地接受其他专业提供的具体结论,而必须重新加以审视,因为史学史本来就是要审视以往史学成果及发展状况,如果糊里糊涂接受其他专业对史学问题的议论,岂不是学术失职?因此史学史研究不能再随波逐流,必须要全面疏理历史学的学术史,这在原则上,适用于历史学所有的专业研究。此种设想的可操作性,就是依托于电子学术资源的日益扩展和不断富集。当然,历史学文献、资料的电子资源,不是单单用于纠正前人研究中的讹误,重要的是能够搜集到更丰富的史料,从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一步。
当今历史研究中运用电子文献资源,已然十分普遍,相信每个学者都大受其益,各有经验和体会。这里谨将笔者近期考订《越绝书》成书年代的体验予以略述,以见证运用电子资源搜讨文献、汇集史料的便捷和高效。关于《越绝书》成书年代,学界见解分歧,争议不休,笔者在修辑《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中尚未完全解决,该书稿上交后和将要出版之际,才予以深入探索。学术界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如李步嘉的《越绝书研究》、《越绝书校释》,乐祖谟点校的《越绝书》,周生春的《吴越春秋辑校汇考》等等,与大量研讨《越绝书》及相关问题的论文,几天之内就从互联网上下载齐备。研究和撰文进程中,又随时利用电子资源检索史料、查阅文献,相当方便。在《越绝书》最后一篇《篇叙外传记》(相当于“后序”)中,叙述此书最后主持人吴平“年加申酉,怀道而终”,又把吴平临终修成《越绝书》与孔子获麟加以比拟和联系,在《越绝书》的另外一篇关于大禹之死的叙述中,也使用“年加申酉”词句,这样,破解“年加申酉”究竟是哪两年,就成为考证《越绝书》成书年代的关键。于是,通过电子信息的搜索和电子文献的查阅,了解了东汉干支纪年方法发展的轮廓,用同样方法也研习了谶纬之说中干支与五行的对应关系,更从电子文献史料检索得知:按照东汉当时历法,传说的孔子获麟和大禹自知将要病死的年份,都在庚申年。这样相互印证,遂得出结论:吴平是庚申年卧病,次年即辛酉年去世,《越绝书》基本完成于东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或延光元年(122年)(详见乔治忠:《〈越绝书〉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的重新考辨》,《学术月刊》2013年第11期)。倘若没有电子版图书、电子文献、互联网的搜讨及下载文献的资源,这样的论文大概是写不出来的,尤其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历史研究中电子资源的强大功能和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于掌握丰富的史料,因而历史学无疑是需求书籍、文献较多的学术门类,电子资源以其使用快捷、便利的优势而造福于史学,而学者个人必须自觉、主动地紧跟形势,调整学习和研究的方法与布局,开发和建设适合于自己治学方向的电子资源储备,其中最基础的工作是:
1.设立自备的个人电子图书馆,将可以下载和存入电脑的电子版专业图书、论文、资料、信息,包括可以独立于网络之外的可检索数据库(如“四库全书”全文数据库)在内,皆在电脑中内予以安装、储存,可以随时检索和查阅,这要比自家藏有纸本书籍更为方便。另外,有些网站如360doc,也具有建立网上个人图书馆的设置。
2.尽可能获得网络电子资源的检索使用权,例如当下的中国知网、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读秀网等等,均具有很好的史料文献检索功能。此类网络资源的建设,仍在持续地扩大发展之中。
3.随时扩充个人电子图书馆,师生、学友亦可互通有无、互通信息,加强协作。如果历史研究者能够在电脑之前,通过多种搜索引擎获得极大范围和极长时段的学术信息,可以如意地查阅多种学术典籍和学术论文,真所谓“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那么整个史学界的学术研究成果,将跨入高速发展的新通道。
三
学术性电子资源虽然具有利用便捷的优点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不能改变学术研究的本质,它仍然仅仅提供研究的资料基础,史学成就的取得还是依赖史学界诸多学者的思考、探索和相互讨论。在史学电子资源之中,扫描版的电子图书和文献来源于纸本文献,具有镜像的性质,只可阅读而不能检索,实质与纸本图书无异。而电子版“四库全书”、“中国基本古籍库”、“四部丛刊”、“中国知网”、“读秀”网站等等,既具备与原书相同的镜像,也能够检索。再一种就是重新打字或转换而形成的电子版文献,如word文件,互联网上检索时常常出现,其中时有错码、讹误,也会有不良的信息,务须警惕。对电子资源利用表示有所忧虑者,基本是针对电脑检索而言。
李根蟠先生认为:“不管电脑检索如何方便,它代替不了读书……在信息时代,认真读书仍然是做学问最重要的基础。”李先生并不贬低电脑检索的作用,但提出了应当注意的几个前提条件:1.对检索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要具备必要的知识;2.对检索的文献要有必要的了解;3.利用多种不同的匹配进行检索,既可以扩大材料来源,又可以防止片面性;4.电脑录入难免有差错,需要核对原文,有时还要进行校勘;5.对检索得到的材料,应当看它的上下文,防止断章取义”(李根蟠:《历史学习与研究方法漫谈》,《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这些建议是十分正确的,但还不能完全囊括史料检索方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一,学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电子资源虽然迅速地扩展,但迄今仍有许多历史文献、宝贵资料未被融入,许多善本书籍、稀见期刊以及史料价值极高的档案文献,依然游离于电子资源之外,短时期也无法改变现状。因此,历史研究不能单单依靠电子资源,特别是不能因为电子资源的便于利用,养成懒于寻求其他各种文献的作风。
第二,使用电脑检索史料,往往带有“欲取所需”的预设目标,即主观上早已形成观点而急切搜寻根据。因此一旦有所“发现”,容易导致不加辨析,仓促间即曲解引用。例如一篇题为《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长文,梳理国外“新清史派”的学术观点和国内学界的反应,资料丰富,条理清晰,但为了批评“新清史”观点,引用《礼记·王制》史料:“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接着就发挥了一大段错误的阐释,甚至曲解中国古代的正统论观念。查《礼记·王制》的原文,乃是“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7页)。意思是,中国与戎夷乃至五方之民,都是各有不同禀性的,不可以强行转变,显然带有“华夷”之分的因素。而该文砍去“不可推移”四字,又曲解“皆有性也”语意,即把“皆有性”理解为现代的词语“共同性”,随之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误解(李爱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这种谬误,即源于先有主观意念,继而用电脑检索”四库全书”,并且片断地截取语句、曲解其义。
葛剑雄等《历史学是什么》一书引《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认为这是将“历”“史”两字连用“现在发现最早的例子”(葛剑雄、周筱贇:《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这也是完全错误的,错在标点断句,正确的标点应当是“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这里的“历”字作动词用,“史籍”才是一个名词,把“籍”字拆为下属,成了“籍采奇异”,则扞格不通,不成语句。“历史籍”,意思就是“经历过阅读各种史书”,这里根本不属于“历”“史”两字的连用。
应当说明,带有预设目标搜寻史料而造成曲解,不光出现于电脑检索,上述葛剑雄等之书可能是因为检索无标点的“四库全书”电子版,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做了错误的标点,也可能是受了中华书局本《三国志》错误标点的误导。但运用电子检索方法查找资料,产生此类错误的几率很大,学者要特别引起注意。
由于历史学电子资源的丰富化,还要设法防止青年学子不认真读书,仅以几种电子文本剪切拼接来应付课程作业的现象,以这种手段拼接的东西,他自己也未曾逐句阅读,只是大致扫上一眼随即粘贴而已,这种“取巧”习惯一旦养成,对当事学生就贻害无穷。因此,笔者在大学主讲《史学概论》课程时,布置书面作业一律不收打印本,要求手写,这样即使是拼抄而成,也等于经过了阅读,达到了课程作业的教学目的。
总而言之,历史学电子资源的建设和扩展,对于史学发展是利大弊小的好事,兴其大利同时除其小弊,并不存在多大困难,关键还在于理念问题。如果将之视为一项类似图书馆建设的公益事业,很多矛盾就会比较容易地解决,很多缺陷也较为容易弥补,这是史学界和历史研究者的热切期待。
(本文摘录自乔志忠:《历史研究电子资源运用的兴利除弊》,《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编辑:赵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