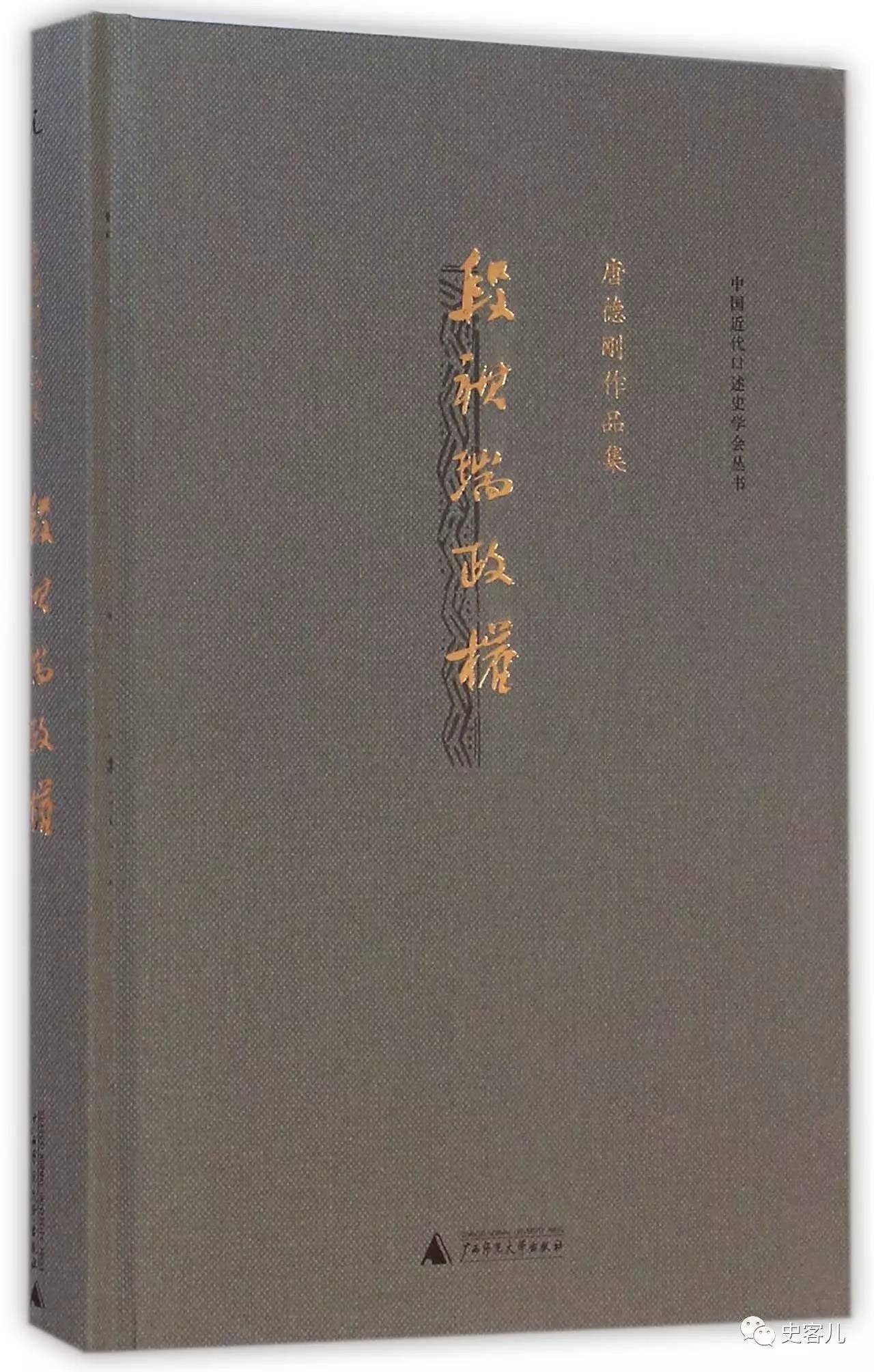● 原创投稿请至:historymook@sina.com
民国时代最上层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狱之间的边缘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个波涛翻滚的转型期。前型(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国制度)已毁;后型(今后两千年的民主制度)未奠。他们一般都是忽前忽后,不知所适地在两型之间走钢索桥。上有光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阴森险恶的万丈深渊,一步踏错,或一念之差,便会坠入谷底,而粉身碎骨。他们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索桥被他们弄断,全民族也随之滑坡,尸填沟壑,彼岸无期。
这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袁世凯和汪精卫了。汪氏当年如不因误听他那心际狭小而又生性泼辣的老婆之言,在一念之差中,当了汉奸,抗战后在蒋公弄得捉襟见肘、无路可走之时,就是“汪先生”的天下了。哪还轮到胡适之、李宗仁来做总统呢?
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其第一个“千古功臣”,绝不是张学良;张也向不以此自居。他甚或公开地说是他当年犯了错误,虽然他并不改悔。少帅就曾向笔者说过,他是以部下身份,阴谋反对长官,他自己的部下,如果也以同样阴谋反对他,他早就把这人枪毙了。换言之,他如果是蒋介石,他早就把他自己枪毙了。所以他对蒋之关他五十年,毫无怨言。少帅近一百岁了,据说头脑还很清楚。此语可复按也。中共的“千古功臣”,更不是日本军阀,而是当年内部倾轧无已时的国民党本身啊。国民党自己胡搞一通,才搞出个共产党来,哪能乱怪他人呢?
是谁搞垮了袁世凯
再翻翻历史,回头看看袁世凯:袁氏在民国二年(1913),镇压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国民党的三藩之后,是何等声势?乘此声势,他就应该虚怀若谷,好好地为国为民,做点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图,却要起邪心,做皇帝。结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钢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试问老袁为何失败,而失败得那么惨?他是被风流小将蔡锷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凯就因一念之差,而为全民所弃也。悲夫!
我们要知道,袁世凯在称帝之前,中华民国原是个统一的国家啊。中央政府也是个可以驾驭全国的政府啊。袁大总统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声望,是远在孙前总统之上,至少不在当时的中山之下。连蔡锷将军当时对所谓“党人”也颇感不耐。笔者在《袁氏当国》中就提过,二次革命期间,蔡锷(时为云南都督)就曾发过拥护中央、痛诋李烈钧造反的通电。当时又有谁能够逆料,三年之后,蔡李二人又联袂率领护国一、二两军,北伐讨袁。这又是谁之过呢?千不是,万不是的是,袁世凯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儿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来。
这一失足,他自己遗臭万年不打紧,却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几乎也被拖到万劫不复的绝境。这纯粹是个历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凯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来的嘛,是啥鸟“历史的必然”呢?丘吉尔在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痛定思痛,就曾在他的二次大战回忆录里面,举出过好些例证,来说明“偶然”怎样改变了历史的方向。
宏观有其必然,微观难免反复
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曾反复地解说过,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制向民治转型,众星拱北,万水东流,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大趋势,是个历史的“必然”。今后两千年,至少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是个“民治”的中国,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扭转的。
可是,从微观的史学法则来观察,则这条通向太平之洋的长江大河,每个阶段都是反复无常的、捉摸不定的。“共和不如帝制”;“选举我是绝对不相信的”;“民主专政至少再搞二十年”…‥还有举不尽的语录,和不够资格叫语录的语录呢。但是这些“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小阶段现象,却改变不了“万水东流”,或“权力滑坡、独裁专制、逐代递减”的大趋势。看不清这一“历史的客观实在”的政客,必然就会在时代的潮流上落伍,终于被历史斗垮、斗臭。袁世凯的悲剧,就是他的时代背景,和知识条件,使他无法看清这个大潮流的总方向,而误走回头路的结果。
吾人在世纪之末的观光客,站在巫山十二峰之巅,俯视三峡之中千帆齐下,大小船夫、袁皇帝、蒋总统、毛主席,乃至最近以香槟浇头的小马哥,强颜欢笑的阿扁哥……或沉或浮,乱成一片,千里江陵一漩涡,看得好不清楚。但是身在船上的操舵者,面对削壁险滩,波翻浪滚,生命交关,何由得见呢?他们自己并不清楚的故事,搞历史的人却不能忽略。一个一个的慢慢来交代,现在还是先谈谈袁皇帝的后遗症:
从较好制度、可行制度到破产制度
袁世凯在身败名裂、忧愤暴卒之后,他身后留下的烂摊子,无人能够收拾,其后遗症至今未了,我民族可就跟着吃苦了。
笔者不学,曾在不同的拙著里,一再说过:我们那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帝国文官制,不是个“最好的制度”(bestsystem),但是它和与它同时的其他文化相比,它却是个“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至少是个“可行的制度”(functional system),所以它才能延长至两千年之久,而没有消灭。
这个可行的制度,可行在何处呢?再三言两语交代一下。我国自秦皇汉武以后,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交互为用,使我们的“政治社会结构”(socio-political structure)走进了一个“国家强于社会”(statestronger than society)的特有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大的问题,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维持长期稳定的问题。而长期稳定的关键则系于中央政府的接班制,也就是继承制。解决这个问题,智慧加机运,我们的祖先选择了“帝王传子制”,它能够一传至十代以上而不出大纰漏。这是在历史上打破金氏纪录的政治制度,为其他任何文化所无也。
汉初诸吕之乱时,顾命诸大臣,咬定了一个“非刘不王”的原则,并声明“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试问当时诸大臣对刘氏真是如此效忠?非也。朋友,他们都是一批了不起、有远见的政治家也。他们为的是奠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为万民造福也。我国古代本有所谓“传贤”、“传子”的两个传统。但是他们知道传贤,牛皮而已。传子才是个“可行的制度”,可以加以不断地改进也……在古代史上能和中国平起平坐的只有个罗马帝国了。罗马帝国就是在这方面败下阵去的。罗马帝国晚年出了三十个皇帝,就有二十九个被杀掉。朋友,将货比货,你能说我们中华帝国所行的不是个“较好的制度”?
地域庞大、人口众多的大帝国,第二个大问题,便是闹分裂,搞藩镇跋扈,军阀盘踞。我国最早的帝国政治家,对此也有最适当的安排,能防患于未然,化之于无形。为此,除掉短期的唐末之外,汉宋明清一传数百年,都未发生太大的问题。你看近在眼前的晚清七十年,动乱若斯,有没有军阀横行呢?你说人家是封建落伍,三座大山。
最后,大帝国里的草根老百姓,总得有个和平安定,善有可褒,恶有可告,安身立命,有保障,有公平的社区生活。这一点在我们传统帝国里的正常状态之下,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当中西两文化在16世纪、17世纪初次接触时,康熙、乾隆的中国,未必就不如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法国。双方是各有短长也。不幸在19世纪之末,在双方较劲之下,我们败下阵来,破了产,社会文化、政经制度,就被迫转型了。在转型期中,新制尚未奠立,旧制已玉石俱焚了。凡事没个标准可循,旧社会出身的政客(如袁世凯)就晕头转向,莫知所适,不得已就只有乞灵祖宗,反动回头;革命阵营出身的政客,就食洋不化,自以为是,而胡作非为了。
袁的烂摊子变军阀温床
袁所留下的后遗症便是全国皆兵,军阀横行,民无噍类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并没有什么军阀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军阀遍地呢?这就是转型期的悲剧了。转型期中,新兴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至少要两百年的时光,庶几有望),而旧的制度则可毁之于一旦。在新旧交替的真空期,就民无噍类矣。
笔者不学,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这么个转型中期。幼年所受的,也就是这么个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转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个不新不旧的初生之犊,对所见所闻的感染,如军阀横行、国共党争,也写了些大胆的假设之文。认为当权者除旧太过,布新不足。今日重写《袁氏当国》,每忆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无道理,有时甚至自惭老来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锐敏。所恨少年之作,历经国难家难,十九皆毁,近偶自昔年报刊中,发现若干旧作,试重读之,自觉尚不无可用之处。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报》,检出一篇青年期旧作,便自觉其颇能解释袁世凯所留下的烂摊子,何以终于变成了民国时代军阀的温床,其祸至今未已?无他,除旧太过,而布新未足也。乃将旧篇自残报中复印一份,复刊之为拙篇之“附录”,以乞教于方家也。
1998年12月18日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七十四卷第一期
【摘选自唐德刚《段祺瑞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 “理想国”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