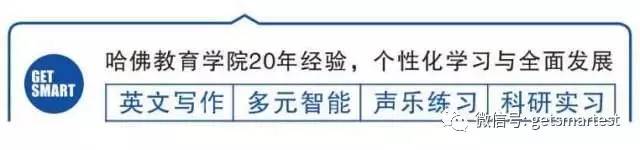

学习,是终身的奋斗。因此在一生中,书,不断改变着我们的价值观。就话题“学生时代最受影响的一本书”,哈佛校报采访了几位哈佛教师。
哲学高级讲师雪莉·陈(Cheryl Chen)
“我祖母在二战时期离开中国,来到了美国。她的三个孩子,包括我爸爸,都在这里出生。祖母与她的孩子大多用英文交流,这导致了到我这一代,接触中文的机会太少了。因此,我能在大一时学习“基础汉语”,祖母尤其开心。这门课要求我们购买一本《简明英汉汉英双解词典》(Concise English-Chine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科维, A.P. Cowie 与伊维森, A. Evison,1986年版)。当时的课本已经被我丢了,可词典却一直还在。它的长宽近似一部手机,只不过厚多了也重多了。捧起它,总能让我有一种奇妙的幸福感。它的红封皮是上蜡的帆布材质。全书1100页,每一页都像人们曾经的国际信件用纸一样薄,且印字不可思议地小。
“大三时我去中国交换过一学期。在那时,我走到哪儿都带着这部小字典。它曾陪我拜见中国西部遥远西藏的佛教圣地,也曾一同沉睡在内蒙蒙古包;它曾陪我探索桂林溶洞的绮丽,也曾一同见证长江三峡的壮美;它曾陪我坐在四川大佛雕像的脚指头上,也曾一同在拥挤缓慢的火车里消磨时光。
我宁愿丢了我的护照,也不愿丢了它。”
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国际科学教授威廉·克拉克(William C. Clark);
国家政策与人类发展教授哈维·布鲁克斯(Harvey Brooks)
在我大学时期,斯图尔特·尤德尔(Stewart Udall)的《1976:明天的议程》(1976: Agenda for Tomorrow)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从那时候起,每当我为人类间,或其对环境无休止的迫害感到失望时,它提醒我人性光辉尚存。它让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好。
“当时我在耶鲁上大二,那是我们这代最糟糕的一年。我们的城市喧声四起,我们的领袖遭到谋杀,我们的人口爆炸增长,可我们的学校无动于衷。
那年,尤德尔的书出版了。
尤德尔描绘了一个开阔的,充满人性的理想世界。对我来说,为追求那样美好的世界而奋斗,是尤德尔为我绘制的宏图。这本书号召每个人结合科学知识与政治理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当尤德尔在第二年以访问教授的身份现身耶鲁的林业学院时,我凭借着对这本书的热忱挤进了他的讨论会。这本《1976:明天的议程》充斥着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与人性内涵,是我职业生涯最好的指路明灯。”
生物学教授布莱恩·法瑞(Brian D.Farrell);
拉丁美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
“我钟爱的有 厄斯特·马尔(Ernst Mayr) 的《人口,物种与进化》(Populations, Species, and Evolution),约翰·威廉(George C. William)的《适应与天择》(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以及史蒂芬·詹·古德(Stephen Jay Gould)的文章。”
“读他们的书之前,我是无法理解宏观进化与微观进化是如何互相联系影响的。在读书中,我逐渐意识到,生物学的知识与生活中的现象紧密相连。一个学者,只有了解到其他学科对其研究领域的影响才能算得上学而有术。教条式的沙文主义等错误偏见只能反映无知。在大学时期,我发现了艺术与科学的共通性,并越来越确信这一点。我们对各个学科整体的认知水平在上升,因为学科间的界限已逐渐模糊——新的想法与新兴技术使学科使之彼此相融。
社会学教授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 与约翰·克莱斯(John Cowles)
“大概是阿尔伯特·卡姆斯 (Albert Camus) 的《西西弗的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吧。我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是读大学之前。从图书馆书架上拿下它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本神话书,后来发现是哲学的专著,翻看没几页就爱上了它。当然,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涵义。因此我将它带到大学,一遍又一遍反复地读,直到慢慢吸收,直到完全读懂。这实在是对我影响至深。
“我的第一本书是小说《西西弗的孩子们》(The Children of Sisyphus)。这本书描绘了住在金斯顿棚屋里极端贫困人民的生活。最触动我心的是赤贫中的人们对其生存意义的寻找,这也是作者卡姆斯最想要读者思考的。除了精神上的绝望以外,连最基础的生存条件也很难满足,一个人的生存意义在哪里?他该如何求生?那些生活在粪堆边的人,那些靠城市的垃圾过火的人,他们该怎么找寻人生的意义?
“要我探寻生命意义’的声音久久在我心中回响,从未停止。从牙买加搬去英国,从这本书到他的其他作品,我始终带着这个问题行走着,思考着。在很多个层面上讲,他的思考与主张没有让我止步,倒是为我的思想探索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后来,我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属于我自己的探索,但他永远是我最初的哲学导师,那时最好的引路人。
本文编译自news.harvard.edu。

尊敬的畅言客户,您好。您所使用的网站评论功能已广告作弊被限制使用,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电话400-780-9680。